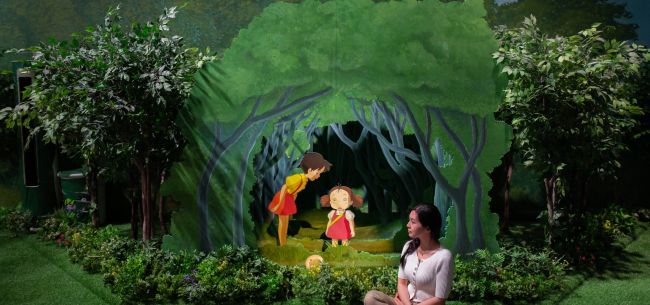
(图片来源:IC Photo)
吕利/文
集体主义日本对个人主义美国一说常见于各种商业评论,但在动画这一日美各有所长的领域,两国业界的表现恰与这一传统印象相反。美国动画的品牌价值往往凝结在工作室与IP名下,大部分观众在观看《玩具总动员》《机器人瓦力》时很难对导演的名字或作风留下记忆。与此相对,今天即便不甚熟悉日本动画的观众也知道《攻壳机动队》与押井守、《盗梦侦探》与今敏的对应关系。一些热忱的日本动画爱好者将上述现象为“卡通”(cartoon)与“动画”(ani-me)之间的关键区别,认为后者更有“深度”,而前者只是传统的儿童娱乐,但日美动画真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制作模式上。
在美国,华特·迪士尼在美国开创了以工作室为核心的制作模式,导演、动画师等主创人员在制片人统筹协调下形成均质可控的美术与表达风格,共同产出能够取悦尽可能多的观众的商业作品。相比之下,起步较晚的日本动画业更强调特定主力人才的带头作用,具有突出能力与个性的创作者可以享受更大空间。在产业规模上远逊于美国同行的日本动画业之所以能在这场大卫对歌利亚的较量中给人留下可圈可点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作者主义”传统。
如果说美国动画业的工业化模式肇始于天才制片人华特·迪士尼,由手冢治虫等人从1960年代在日本开启的作者主义路线则以动画导演宫崎骏为集大成。在当代日本乃至世界电影界,宫崎骏的地位毋庸赘言。舆论印象中的宫崎骏是定言令式般的商业品牌,一场活着的文化事件,而作为动画导演,宫崎骏的专业能力更令人高山仰止。宫崎骏在1960年代加入东映动画,成为主力动画师之一,在积累了丰富的一线制作经验后,于1978年初执导筒,主持制作了电视动画《未来少年柯南》,其间一手包办了剧情大纲、角色设计、分镜绘制与大部分动画检查,展露出空前的精力与全面的才能。此后,从1979年开始执导剧场动画的宫崎骏延续了这种事必躬亲的风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自己的导演作品施加了巨细靡遗的把控,令与他颇有交情的押井守称他为制作现场的“拿破仑”。
除了拥有将个人构思忠实投射到作品中的天才能力,作为动画导演的宫崎骏也确实是一个不惮于表达自我主张的创作者。在80年代的几部动画长片中,宫崎骏的作者性已经表露无遗:主人公通常为具有独立动机的少女或精力无比旺盛的少年,因关乎人类存亡的危机或单纯的搬家而开始冒险。自然世界总蕴藏着友善的超现实能力,可以在剧情的重要时刻(以在观众看来不那么有说服力的方式)为主人公化解关键冲突。国家总是以近代化暴力机关的面貌登场,其军事力量的灭亡往往为剧情的高潮拉开序幕。故事中真正的坏人极少,大部分配角内心缺乏恶意,一些最有活力且最善良的角色往往是老人;几乎所有人都按照一定的道德观行动。在因《千与千寻》赢得广泛的国际关注后,宫崎骏作品引发的讨论更是从偏向技术与审美的“作者性”进入了更偏文本的“思想性”层面:他的动画似乎寄托着一种融合了环境主义、女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个人“哲学”,这些主张不但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也体现在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日本修宪、《查理周刊》事件等问题上采访到的只言片语中。
然而,成为日本动画界的金字塔,并不意味着动画创作就是宫崎骏创作活动的一切。对宫崎骏人生经历的回顾时常强调他在青少年时代因观看《白蛇传》与苏联动画《冰雪女王》而立志制作动画,却很少提及漫画与儿童绘本对宫崎骏的影响。在加入东映动画以前,就读于学习院大学的宫崎骏曾加入该校儿童文化研究会,尝试过以儿童文学之名漫画创作;从事动画工作后,宫崎骏曾以“秋津三朗”的笔名在1969~1970年连载了漫画《沙漠之民》,又在1983年完成了绘本《修那之旅》。成为动画长片导演后,宫崎骏也曾创作多部军事题材短篇漫画,《红猪》与《起风了》两部影片的雏形即在其中。
作为漫画家,宫崎骏的代表作非《风之谷》莫属。1981年,宫崎骏经日后的合作伙伴铃木敏夫介绍,向有意进入动画市场的德间书店高层提出了制作剧场动画《风之谷》的方案,但被以没有原作漫画、缺乏商业保证为由拒绝。因此,宫崎骏从1982年2月开始在德间书店旗下刊物连载漫画版《风之谷》,并于1984年将相当于单行本前两卷的内容改编为时长两小时的动画长片。在此之后,虽因导演事务缠身时有休刊,宫崎骏仍将《风之谷》漫画的创作坚持下去,直至1994年正式完结,全篇幅相当于动画版剧情的三倍。
虽然此生只创作过这一部长篇漫画,《风之谷》单行本七卷逾千万册的销量和持续至今的文化影响力仍足以奠定宫崎骏在日本漫画史上的地位。2019年,漫画版《风之谷》被改编为歌舞伎,就在当年年底,日本出版界一月之内先后迎来了两本以《风之谷》为主题的思想评论著作,其一为社会伦理学者稻叶振一郎的《娜乌西卡解读·增补版》,其二为民俗学者赤坂宪雄的《娜乌西卡考——风之谷启示录》。即便以宫崎骏之盛名,一部漫画在完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能受此待遇,仍不可谓不奢侈。
1984年上映的动画《风之谷》是宫崎骏执导的第一部原创动画长片,也是“宫崎骏式”风格的集大成之作。在现代文明灭亡后,由有毒黏菌与巨型昆虫组成的新生态系统“腐海”主宰了生物圈,将人类逼至陆地边缘。军事大国多鲁美奇亚入侵小国培吉特,从其境内夺走一千年前消灭旧人类文明的生物武器“巨神兵”,试图以此烧平腐海、开拓生存空间,培吉特遗民则故意惹怒腐海虫群,试图诱其冲击多鲁美奇亚军队,报亡国之仇。沦为战场的农业酋邦“风之谷”酋长之女娜乌西卡历经冒险,发现腐海并非自然的恶意,而是将被人类污染的旧世界还原成清净世界的良性机制,最终牺牲自己平息了虫群的怒气,以此换来虫群的谅解与祝福,在经历了弥赛亚式的复活后调停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
稻叶振一郎的《娜乌西卡解读》脱胎于他1994年12月发表在《季刊窗》上的长文。作为对当年早些时候完结的漫画《风之谷》的回应,稻叶振一郎从乌托邦主义的角度指出了《风之谷》漫画版与动画版间的思想色差。动画版《风之谷》讲述了一个从乌托邦出发、又归于乌托邦的故事:在工业文明崩溃后,于有毒的腐海边缘艰难求生的农业社会风之谷没有政治权力与暴力,仅凭简单的风力与灌溉设备维持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以强大军事力量挑起战争,甚至企图焚烧腐海的多鲁美奇亚军队虽然破坏了这一理想状态,但随着剧情高潮部分的核心冲突因娜乌西卡的死与复活而化解,侵略者不得不撤离,在腐海的“福音”庇护下,风之谷又被还原到了之前那种和谐永续的状态。
与此相对,漫画版《风之谷》讲述的是一个不但没有从乌托邦出发,反而在结局中否定了一切乌托邦存在,在核心思想上几乎与动画版截然相反的故事。在动画中,腐海的真相暗示着和平永续的生活终将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终将得到解决。但在漫画中,腐海寄托的含义恰恰相反:被腐海完全净化后的世界无法生长任何动植物,在当前世界里生活的人类只要呼吸一口“清澈但强烈”的未来空气就会吐血死亡。随着腐海的本质在漫画版结尾部分得到澄清,这个在电影版中代表大自然良善力量的意象反成了人类文明技术的最高“杰作”:以不符合演化规律的速度突然蔓延到整个生物圈,不断增殖、净化并自我毁灭的腐海并非自然产物,而是少数古代人(即现代人)的世界重启计划的一环。在用几千年时间消灭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争斗的一切痕迹后,被封存的人类胚胎将在毫无环境污染与不必要的技术,只有农业、风车、动物、音乐与艺术的理想环境中发育、生活。结果,在为充满敌意的世界寻找解决方案的冒险之路尽头,娜乌西卡反而决定用暴力摧毁含有旧人类胚胎的改造计划中枢,把《风之谷》世界的未来留给了似乎注定走向灭亡的现有生物界。
如果说动画版《风之谷》只是以“风之谷”为喻体,向现实世界(即在动画版《风之谷》开场的寓言中已经灭亡的现代观众)宣讲某种生态乌托邦的可贵性与可能性,漫画版《风之谷》中的那个虚构世界不但脱离了工具属性,呈现出类似托尔金所谓“次等世界”的自主生命迹象,还直接质疑了动画版中表达的乌托邦思想本身。漫画版中的“风之谷”酋邦并非遗世独立的农业社群,而是时刻面临少子化、慢性病与腐海污染威胁,必须为多鲁美奇亚提供军役才能换取和平的脆弱小社会;与动画版相比,“乌托邦理想能否保全自己”的问题在漫画版中更为鲜明。而如果一个生态乌托邦的构想解决了现实的问题,它是否也彻底倒向了选民主义,它的践行是否也无法离开彻底的计划性?对于乌托邦主义的这一倾向,宫崎骏在结局表达了略显唐突、但发人深省的拒绝。
在稻叶振一郎看来,宫崎骏的结论与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的观点颇为相近,这一解读或许会令抱有“社会主义者宫崎骏”印象的读者产生违和感。稻叶认为,在漫画版《风之谷》结局中,娜乌西卡拒绝了一种全然计划的、不承认对良好生活之自主探索的“帝国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以拥抱一个包容多种乌托邦之可能性的“元乌托邦”。它只能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在无尽旅途与无尽苦难的煎熬下偶然生成的和解与共生中,无法获得固定的形态,也不能成为历史的终结者。
与在更广泛意义上把宫崎骏作为思想者对待的稻叶振一郎相比,赤坂宪雄对《风之谷》的评价更重视其创作过程背后的知识考古学背景。出于日本左翼民俗学对天皇制与政治权力来源的传统关注,赤坂注意到了宫崎骏在《风之谷》中对“风之谷”这一前国家社会的描写与他之前的绘本、漫画作品间的关联。与专注于构筑一个完备的次等世界的漫画版相比,宫崎骏在动画版《风之谷》去除了腐海背后的复杂矛盾,淡化了风之谷居民正走向慢性死亡的惨淡背景,转而着重刻画了以一群可爱的老人为首的风之谷居民如何伺机推翻多鲁美奇亚人的军事统治。这一改编情节的分量在动画版中几与娜乌西卡本人的冒险戏份相当,其内容则几乎完全脱胎自宫崎骏讲述中亚小民族对抗游牧帝国侵略的早期漫画作品《沙漠之民》。
用“小国抗霸”这一更具张力也更为驾轻就熟的主题填补动画改编留下的空白,揭示了作为创作者的宫崎骏与作为动画导演的宫崎骏之间耐人寻味的矛盾关系。如果不在漫画中(半无意识地)思考乌托邦思想面临的种种难题,宫崎骏也无法在动画中勾勒出一个在充满恶意的世界里生动而可欲的“风之谷”意象;然而,受制于工期、商业考量以及动画这一体裁的基本属性,作为动画导演的宫崎骏又不得不把一种已在自己脑海中被全面拷问、却在感情上难以割舍的单纯的乌托邦主义当作编排情节时最经济的选择。赤坂宪雄将漫画家宫崎骏构筑《风之谷》世界观与故事的手法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中的“复调性”(这也与稻叶振一郎的乌托邦论相呼应——有着多种价值观的世界必然是一种确定的乌托邦主义无法容纳的),但在动画版的改编中,只需与漫画内容稍加参照,观者便不难看出宫崎骏在制作动画时对自我表达的明确节制。
通过将复调性的世界构造与单线条的、以明快的情绪为动力的冒险戏剧截然区分,80年代的宫崎骏产出了完成度与商业回报比之前更高的作品。但在他本人看来,这种“盆栽”式的成果未尝不是一种表达上的缺憾。或许正因如此,在今天若以1994年《风之谷》完结为分界点回顾宫崎骏的作品便不难发现,从1997年上映的《幽灵公主》开始,宫崎骏作品的道德色彩变得更为暧昧了。《幽灵公主》中,在室町时代的日本大肆破坏原始森林的炼铁城镇本身染上了现代企业与宫崎骏早期作品中无政府工团意象的色彩,成为麻风病人、女性等受迫害人群的公社;在2001年上映的《千与千寻》中,光怪陆离的澡堂“油屋”既是半奴隶制雇佣劳动与异化的隐喻,也与女主人公在社会意义上的成长密不可分。随着《风之谷》的故事走向终结,曾被宫崎骏小心排除在动画这一媒介之外的那种令他在漫画中无法割舍的复调性终于渗透到了他的主业当中;拜这一变化所赐,宫崎骏作品原本畅快的反现实基调中也加入了一抹更接近现实的颜色。
不过,把复杂而多歧的虚构世界删减成在时间与逻辑上有限的动画电影固然是一种表达的缺憾,把两种看似完全相悖的创作思路糅合在一起也未尝不是如此。虽然在思想性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宫崎骏自《幽灵公主》以来的作品在叙事的完成度上时常不尽人意。某种意义上,越来越复杂的构思令宫崎骏作为叙事家的造诣在21世纪遇到了瓶颈;但正是在这一瓶颈的挤压下,他的创作冲动才能像永动机一样不懈燃烧。由此看来,那个永远在路上、永远不会被现实追上的乌托邦或许不只代表了宫崎骏对乌托邦主义情结的扬弃,也是对这位名副其实的巨匠半个世纪创作生涯的一种隐喻。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