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2 |

《你好,忧愁》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余中先、谭立德、金龙格/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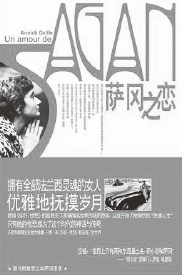
《萨冈之恋》
热尔/ 著
黄荭/译
新星出版社
2010年1月
经济观察报 增刊 黄荭/文 “1954年,她带着一部单薄的小说《你好,忧愁》走向世人,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丑闻。而在写出了众多轻率的文字、经历了同样轻率的一生之后,她的离去却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这是弗朗索瓦兹·萨冈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在法国南方洛特省的卡雅克,女作家故乡的家族墓地里,萨冈和她的前夫、她儿子的父亲鲍勃·韦斯特霍夫(Bob Westhoff)葬在一起,还有另一个人——佩姬·罗什(Peggy Roche),曾经陪伴萨冈走过大半辈子、有埃及女王纳费尔提蒂一样的高鼻子和冷峻面容的美女模特和时装设计师——墓碑上没有她的名字。或许这就是萨冈“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和世界无关。
而作为流行作家,萨冈已然是大众语汇中一个点击率很高的词条,二十世纪的一个出版现象,一个问题people,一个用速度、用酒精、用毒品、用赌博、用令她“倾倒”的爱情去挑逗“生命之轻”的时代标签:心不在焉的享乐、放纵,脚注是有点残酷的青春,仿佛一首宋朝小令的吊诡,上半阙东风沉醉,下半阙“酒已都醒,如何消夜久?”
“十八岁”——弗朗索瓦兹·夸雷小姐在手稿的背面特别标明。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几年后她对闺中密友弗洛朗丝·马尔罗坦诚,她当初这么做只是出于一个稚气的考虑,出版商或许会想:“她还年轻,写得不好也情有可原……”
《你好,忧愁》于1954年3月15日出版,在夏天到来之前,印数已达到五万册,萨冈已经“声名在外”。慧眼识珠的其实并非只有勒内·朱利亚一人。
1954年1月6日,萨冈把手稿亲自交到位于拉丁区大学街的朱利亚(Julliard)出版社,同时也去了附近的布隆(Plon)出版社和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布隆和伽利玛最后都同意出版,只是为时已晚。朱利亚在看完手稿的当晚就给天才少女发了电报,约她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面议。只是夸雷小姐有赖床的喜好,醒来发现已经迟了,于是改约下午五点。
朱利亚一下子就被这个一头短发、纤细、透着古灵精怪的小姑娘迷住了,尤其是当她有点腼腆、有点结巴地说出一些直截了当、玩世不恭的话的时候。她跟他要了两万五千法郎的稿费,朱利亚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她立刻拿着这笔钱跑去买了一辆“捷豹”跑车。她曾经问过父亲得到一大笔稿费该怎么办,皮埃尔·夸雷十分干脆地回答她:“在你这个年纪,这太危险了,花掉它!”
挥霍也是一种抵抗,抵抗被金钱、被循规蹈矩的生活腐蚀,就像飙车会给人一种飞翔的假象,它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忧伤、一种孤独、一种遗忘。
“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让我认识到那没什么意义。”太早、太快、太容易得到的一切都显得虚幻和可疑。“一月后,一年后”,或许曾经的“某个微笑”就已经变成了镜花水月,渗到灵魂里就是莽撞的青春磕着碰着的一块“淤青”(bleu)。
美国《纽约客》的记者亚当·戈普尼克称《你好,忧愁》是欧洲版的《麦田守望者》,萨冈和J.D.塞林格一样,代表了一个时代(“垮掉的”、“颓废的”)的青春。莫里亚克说她是“一个迷人的小魔鬼”,邪恶又天真,温柔又残忍,以最简洁的文笔把握了青春生活的一切。走进浪漫主义死胡同的缪塞坦言:“我们并非热衷于作恶,而只是放弃行善;我们不是悲观失望,而只是麻木不仁。”二十世纪的“洛丽塔”也许会带着厌倦、冷漠又好奇的神情承认:“我们也是世纪儿,只是我们不要忏悔。”
1957年,萨冈的第三部小说《一月后,一年后》出版,艾田蒲“指出了两种时代病:可口可乐与弗朗索瓦兹·萨冈”。
| 1 | 2 |


 聚友网
聚友网 开心网
开心网 人人网
人人网 新浪微博网
新浪微博网 豆瓣网
豆瓣网 转发本文
转发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