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在卡儿斯与法兰克福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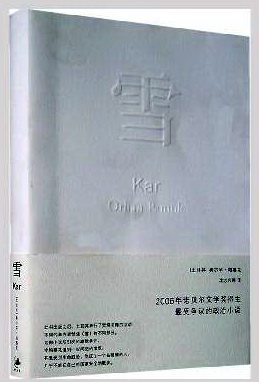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邓金明 雪并不必然象征着神圣、纯洁、安宁,它也预示着令人窒息的恐怖、灭亡、死寂。雪的含义,有时,要看它落在什么地方了。雪,落在奥尔罕·帕慕克的土耳其,落在东西方之间,就注定了它六角形的晶体对称结构所引发的神秘与错综:轻盈与沉重,个体与族群,诗学与政治,记忆与现实,安宁与不安,幸福与灾难……
一个名叫卡(Ka)的诗人被一场雪(土耳其语为Kar)困在一座叫卡尔斯 (Kars)的土耳其 “边境城市”。与其说这是帕慕克小小的文字游戏,不如说是他以一个同样荒诞的政治故事在向卡夫卡致敬。《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始终无法走进城堡,而在《雪》中,诗人卡的命运却是困在卡尔斯这座政治“城堡”中无法摆脱出来。正如小说作者介绍的那样,“卡是土耳其人,与卡夫卡并无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文学上的。卡的真名是KerimAlakusoglu,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喜欢这个名字的缩写。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他第一次去了法兰克福。他并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诗人,其一生是诗歌的一生。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了进去。”
一个诗人和一场大雪中的政治运动遭遇,诗人的多愁善感与政治的铁血遭遇,问题不在于其间多么的荒谬不经,而在于作者帕慕克执意要把这种荒谬变为可信的现实。于是我们看到了弥漫在《雪》中的梦游一般的不安感,令人发疯的恐惧中的玩笑;看到了在剧院上演、在电视直播的布莱希特式的戏剧如何与和政治杀戮交织在一起、艺术和现实彼此纠葛的噩梦;看到了那个叫卡的诗人在暗杀与审讯、逮捕与恐吓、政变与清洗中完成一首又一首诗篇的可笑又可怕的荒唐景象。
《雪》让我很震惊。有时候让我在恐惧和大笑之间不知所措。它奇怪地复苏了我,一个七○年中后期生人不曾有过的政治感。当然,这种感觉不是记忆而是幻想。当我们把所有的政治因素(口号、声明、政策、运动、密谋、审讯、交易、暗杀……)完全堆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合逻辑的就变成了不合逻辑的,政治于是就成了笑话,成了艺术。《雪》当中写到一场发生在剧院里的政治枪杀。帕慕克以一种夸张然而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笔调,一一罗列了军人对观众射击时,子弹各射中了什么。其令人骇笑之处,我只有在读到王小波的《2010》中描写的华丽的“鞭刑”时,才曾经体会到过。帕慕克令人惊奇地在现实的残酷和艺术的轻松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他执意让一个诗人的单纯 (他在面对雪和自己的情人时完全像个孩子!)直面一场政治迷局的错综复杂;让一个久未写诗的诗人身陷政治的血雨腥风中时突然诗性大发,文思泉涌;让轻盈的艺术和坚硬的现实并驾齐驱——但是,这不是天真!也许,帕慕克想暗示的只是,诗,并不是政治的反面、反题,诗和政治并不是对峙的,恰恰相反,诗和政治拥有某种同质的秘密之花。这并不是说诗有时候是血腥的,政治有时候是浪漫的 (比如我们津津乐道的那种某个伟人的政治美学),而是说,政治本质上就是和诗一样混乱的、未知的、神秘的、羞怯的、善变的,问题在于你是否放大了某个局部、片断、对白、举止,大到整个现实逻辑失效。
《雪》,最容易让人觉得有一种舞台剧的表演感。这真的是现实吗?问题是,什么是现实?我们会发现没有现实。小说中,卡尔斯城的小报记者两次先发表对事件的报道,后有事件的发生;小城民众观看电视直播的剧院的政变,还以为是剧情的安排。诸如此类,并不是帕慕克在玩什么鲍德里亚的“仿真的游戏”,而是因为戏剧性根本就内植于政治现实之中。正如戈培尔那句有名的叫嚣,“我一听到‘文化’这个词,就想掏枪!”这与其说是政治的野蛮,不如说是政治的浪漫。
政治会变轻,正如雪也会产生致命的重量。谁都知道,雪,不仅仅是诗歌抒发的轻盈之物,有时候也是生命杀伐的“白灾”。“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但是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暇的感觉。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政治、宗教、民族、国家,就像雪营造的圣境一样,会使个体产生皈依的迷梦,但是一旦个体苏醒,它就会成为一种难以挣脱的束缚。也就是说,身陷集体情感、信仰、主义之中,个体会觉得无比安宁、轻盈和幸福,可一旦你想摆脱它,它就会像暴风雪一样暴虐、像雪崩一样沉重无比,甚至成为打压的致命力量。这恐怕是帕慕克以“雪”命名这样一部政治小说的真正用意所在吧。
- 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 | 2008-07-15
-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 2008-07-03
-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 2008-07-01
- 十宅论 | 2008-06-25
- 用“常识”揭示行业本质 | 2008-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