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1)
| 1 |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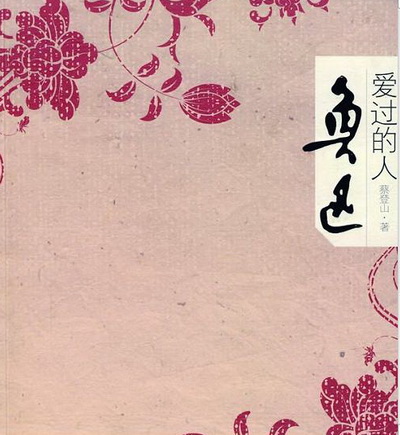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张耀杰 蔡登山先生是和我一起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文章的文友,我在《传记文学》陆续读过他许多人物传记,印象中颇有周作人美文小品的神韵和质感。只是他研究鲁迅的文章,此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当他的新著《鲁迅爱过的人》摆在面前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出乎意料之外。在接下来的文本阅读中,我一方面为作者所发掘出来的别开生面的历史文献眼前一亮;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对鲁迅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的人性底蕴和性情表现,平添了几分亲切之感。
美好爱情与事实重婚
按照作者的解释,所谓“鲁迅爱过的人”,采取的是广义的标准,包括爱情、亲情、友情及师生之情,甚至奉母命成婚的“无爱”之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由成舍我主办的北京 《世界日报》于第二天刊登《周夫人述悲怀》,其中介绍说:“鲁迅除有爱人许景宋女士及一子,随同在沪外,北平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尚有八十余岁老母,及妻朱女士。”
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许广平收到丧电,当即汇去一百万法币的丧葬费用。一年后,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从而成为第一个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为朱安留下真名实姓的人。
在第一章 《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鲁迅与朱安》中,作者一方面通过文献资料的充分挖掘,证明鲁迅在与许广平同居生子之前,并没有与原配妻子朱安正式履行离婚手续;一方面又碍于道德评判与法律认证的难以区分,自相矛盾地回避和否认了鲁迅已经构成的法律意义上的事实重婚。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美好爱情,以及与朱安之间的 “无爱”之情,作者在第二章 《十年携手共艰危——鲁迅与许广平》中写道:“可怜的朱安,她终究是无法爬到墙顶的,因为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需要慰藉,种种重大的精神创痛需要理解,需要温柔的舐舔,这都不是她所能胜任的,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
到了第四章 《最是伤心忆往事——周海婴的回望鲁迅家族》中,作者谈到1951年5月北京市法院所受理的羽太芳子对周建人的离婚诉讼,其中写道:“一九一二年秋周信子将其妹周芳子由日本招来中国,住于浙江绍兴被告家中;后因周信子与周树人说合,由被告之母主持,于一九一四年原告与被告结婚;婚后以语言陋阂,感情不够融洽。”接着这段话,作者引述了周海婴的说法:“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
为了替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与王蕴如的重婚事实进行道德辩护,作者又抄录了前辈学者姚锡佩女士批评周作人的议论:“可见他在对待其兄弟的婚变上,是何等的不宽容,是何等的有违人情物理,是何等的不论自然和事功!……他偏执于个人的情感,一味站在不愿离婚的一边,竟成了旧道德的代言人。”
稍微明白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鲁迅、周作人、胡适、陶孟和等人当年所坚决反对的,是男人可以自由纳妾却偏偏要求女性节烈的既不公正也不人道的“旧道德”,却从来不包括周作人一贯信守的为尊重弱势女子而反对事实重婚的并不老旧的“旧道德”。对于鲁迅和周建人在没有正式履行离婚手续之前,就与第三者非法同居的重婚事实,一名严谨理性的现代学者尽管可以不从道德意义上做出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甚至可以在以人为本的人性层面上予以充分的宽容及美好的礼赞,却不可以从现代法律的意义上一笔抹杀已经存在的事实重婚,更不可以把依法维护合法婚姻的周作人,斥之为“逼迫”和“旧道德的代言人”。无论人类社会如何进步,非法重婚都只能是被宽容的对象而不是被高调弘扬的一种美德。
| 1 | 2 |
-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 2008-07-03
-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 2008-07-01
- 十宅论 | 2008-06-25
- 用“常识”揭示行业本质 | 2008-06-24
- 价值投资理论新解 | 2008-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