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去了舞会,那就要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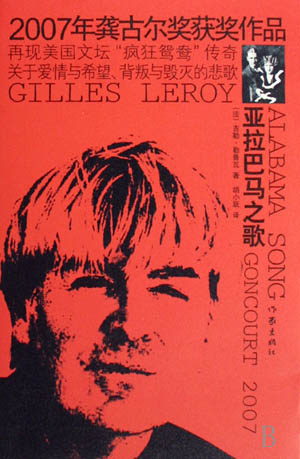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三位丈夫多多少少都有些同性恋的倾向,或者至少不那么男性化,而三位太太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她们的强悍之处,她们是泽尔达·菲茨杰拉德,来自南方的贵族后裔;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作家、演员;英格丽·卡文,歌唱家,她没有冠以夫姓,第一任丈夫是著名的法斯宾德。
我们从三本书中读三个女人的故事,其中只有《新娘日记》是真实的,但又是片面的、私人的,《英格丽·卡文》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为她写的一曲诙谐散漫的情歌,而《亚拉巴马之歌》的作者显然跳过了历史上更多人对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评价,在书中她不再是个单纯的疯子,而是个有才华亦有感情的女人。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亚拉巴马之歌
吉勒·德鲁瓦常常被误认为是用法语写作的美国作家,大概因为他谈美国文学多过法国文学,连这部获得2007年龚古尔文学奖的《亚拉巴马之歌》也是选择了美国文坛上曾经最耀眼也引发无数丑闻和争议的夫妻,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泽尔达。
司各特的朋友们都痛恨泽尔达,而传记作者们采访的往往正是这些人,也相信了他们对泽尔达的说法,德鲁瓦说。他想要恢复一种平衡,却不是用公正重现历史的方法。他写了一部以泽尔达口气叙述的小说,小说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真实的,斯人已逝,记忆早已模糊不清,而小说的功效也不是讨论谁是谁非。德鲁瓦年轻时代便着迷于这对传奇夫妇,先是想成为司各特那样的伟大作家,后来则更倾向于最后死于疯人院的泽尔达,她更疯狂、更矛盾,内心更不为人所知。她既掀起裙子在酒吧的桌子上跳舞,同时也写作,她是引人侧目的“南方美女”,法官的女儿,贵族的后代。在南方,“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简直配不上她,人人都认为她降低了身份,况且那时的司各特只是个漂亮整洁且善跳舞的小军官。
这是一个讨巧的选择,故事被人讲了千万遍,却从来没人选择从泽尔达的角度来说;况且对她内心经历过的波澜并无太多文本可做参照,作者大可随意发挥。她的“通奸罪行”,她被送进疯人院的经历,都足够戏剧化,一个“疯子”的谵妄,正可以成为小说家发挥的出口。不过德鲁瓦显然宁愿相信她并未疯狂,只是在丈夫的嫉妒心和世俗的不容下才被送进了疯人院,而那些可怕的治疗只不过是迫害的物理手段,不见得比那些隐形的杀手更可怕。在德鲁瓦笔下,司各特在才思枯竭,生活落魄到无以为生之时居然偷窃妻子的写作,或许仅仅是换来维持几个月生活的收入。她被送进了疯人院,其实从他把她从她的法国情人那里拉回来时,两个人的矛盾已经被推到了危险的极端。泽尔达最终死于疯人院的一场大火,那时司各特已经在酒精和捉襟见肘的生活中死去,他是她的爱人也是敌人,死亡却让她几近崩溃。
从另外一条线来看,有评论曾说《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小说中最接近于自传的一本,这个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故事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个人的生活,发生在出身寒微但英俊、才华出众的美国青年和因同父亲乱伦而患上了精神病的富家小姐间的故事。那个叫做尼科儿的女子难免让人疑心起来,菲兹杰拉德是否是照着妻子造出了这样一个人物——美丽、疯狂、出身高贵。“一个天生的理想家,一个被损害的牧师,由于种种原因,信奉了上层资产阶级的理想。他到了上层社会之后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才能,开始喝酒沦落。其背景正是有闲阶级处于最有光彩、最有魅力的时候。”这背景便是美国历史上的 “爵士时代”——《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可以找到对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描绘,司各特和泽尔达正来自那个年代,他自己就是那个天生的理想家和被损害的牧师,才华和最好的时光消耗在了对妻子的爱和责任,以及在并不属于自己的上流社会中的疲于奔命中。
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新娘日记
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有时的确令人生厌,如果她再不停止一遍遍地重复她少女般的外貌引起的惊叹和赞美,人们如何把她错认为是她那位著名的丈夫的女儿,她怎样一次次地在大街上被搭讪和尾随。吸引你的是什么?1950、60年代巴黎作家圈子里的逸闻八卦?“大人物”们的恩怨纠纷?还是想要窥探写出了《图像》和《女人的盛典》的让(娜)·德·贝格究竟是何许人?这本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1957年-1962年的日记的确有此功效 。
《新娘日记》在中国的出版恰巧在阿兰·罗伯-格里耶刚刚去世之后,法文版早在2004年就已经发行,选择在他仍在世之时发表日记是罗伯-格里耶的意思,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妻子这本日记的存在,据说连卡特琳娜自己也把这本写在小学生笔记本上的日记忘了个干净,只是为了丈夫的传记的缘故才又重新找了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是卡特琳娜为丈夫所写的一本“自传”,她从来没有回避站在这样一个有名而且聪明的丈夫身边带给她的满足感和自豪,即便她自己也是一位作家,并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如同对5年时间内生活的一次再现,日记由二人的新婚旅行开始,“这是一次真正的电影或小说里的新婚之旅”,自称有着“小姑娘外貌和邪恶本能”的卡特琳娜和比她年长8岁的丈夫开始了新的一种关系——婚姻。
很多人认为日记里记录的罗伯-格里耶、卡特琳娜和午夜出版社所有人热罗姆·兰东的三角和虐恋的关系对已经过世的兰东的形象有损,不过罗伯-格里耶认为这些内容更多和文学有关,而不是单纯的“八卦”。而“情色”(ero-tique)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注意,是情色而非“性”(sexuelle),这对于卡特琳娜本人的两本书来说更是主题——《图像》以让·德·贝格的名字发表,让人误以为出自男人之笔,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正是位男子,这就更加地混淆视听。法语中Image包含着多重的意思,图像、影像,还是镜像?如同她丈夫的书名一样难以准确翻译,中文版的编辑陈侗在编后记里也写到这点,《图像》里性爱“奇怪的两面性”也对应了Image这个词的多义性,书中的克莱尔既在一个年轻女子安娜面前扮演着残忍又冷静的“女主人”角色,让叙述者觉得难以接近,但在小说的末尾处她又成为让的“奴隶”,在被蹂躏和被侮辱中得到快感。《女人的盛典》则是以让娜·德·贝格的名字出版,这次叙述的口吻也变成了女人,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王”在镜子前面反复演习 “塞巴斯蒂安受虐”的戏码。
在《新娘日记》里也可以读到这两本化名出版的书带给她的快乐,笔名就是面具——别人在她面前谈起这两本书时,她完全可以装作没事人一样。现实生活中,在罗伯-格里耶家的公寓里,卡特琳娜换上紧身带、玫瑰色裙子和黑长袜,阿兰命令她在热罗姆面前脱去外衣,热罗姆在裙子底下抚摸她,阿兰则走到她的座椅旁边抓住了她的手,同时掰开她的嘴,忽然阿兰松开了卡特琳娜的手并给了她一个耳光,宣告了这段插曲的终结。这仅仅是一个片断,在整本日记里,还可以读到很多卡特琳娜的“冒险”活动,那些脱衣舞表演——尤其是在日本看到的“上乘”的脱衣舞表演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布洛涅森林里同陌生人的奇异“接触”,她对女朋友米歇尔的爱情等等。她显然也阅读了很多乔治·巴塔耶(《色情史》)这位“色情狂”的言论。而阿兰则扮演着积极的参与和鼓动者的角色,他自己的“不正常”、“身体上的欠缺”没有让他变成一个禁锢者,他更愿意亲自为妻子挑选一位情人,而热罗姆是他最好的朋友,“阿兰希望在他回来后我能做得更温柔,更温柔地迎接他的虐待,满足他的虐恋欲望,他没有对我隐瞒这一点,他期望能跟热罗姆一起分享他的愉悦。”
在2004年《新娘日记》出版时,卡特琳娜写给彼时自己的“给新娘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读到:“新娘”和在她看来约定俗成的一切东西唱反调,评价《广岛之恋》太过知识分子气,夸大司汤达的作用,让自己令人侧目,对那些胆敢动阿兰一根头发的人毫不温柔,甚至责备兰东是一个指望不了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表达了她的负罪感,甚至有时公开表示了遗憾。”25年过后,卡特琳娜也终于可以对“新娘”说:你不会感到烦闷,不会空虚,你收获了自信,从屈从者变成了支配者,和你担心的正相反,你会平静地老去,甚至对此浑然不觉。
她叫英格丽·卡文
就像很多人所说,让-雅克·舒尔是个懒鬼,这个67岁的作家到现在只写过三本书,除去在2000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英格丽·卡文》,另外两本都要追溯到25年以前。
把时间往回拉到1971年,英格丽·卡文,赖纳·法斯宾德的新娘,一个危险的同性恋者的新娘,一个被称为“电影神童”的人的新娘,这是个奇怪的婚姻,并且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一年之后告终,虽然人人都在说,英格丽·卡文是法斯宾德此生最敬重和喜爱的女人——因为她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反抗他的勇气,但是这也没有妨碍他对她进行折磨。有一年法斯宾德带着大队人马在波库拍片,有一天他怂恿所有工作人员跳进游泳池裸泳,那时他正在紧锣密鼓地追求新同性恋人萨林。在法斯宾德的指示下,两个男孩架住了卡文,而萨林手持一把刀去割卡文的长发,“事件发生后,英格丽不得不在头发秃了一块、脖子与手臂上满是菜刀伤痕的惨状之下四处抛头露面。”在罗马的太子花园酒店,她不过哼了两句流行歌曲 “您只要把小舌状的东西放进开罐器的开口,然后把那个小东西往上旋”,他就气急败坏地把电视机朝她的脑袋扔过去,结果只砸到了他自己的脚。
夏尔真正的名字叫作让-雅克·舒尔,正是那个懒鬼作家,他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夏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顺耳,只是个偶然的选择,为什么不呢?“夏尔”可以是改变的开始,一个小把戏,他害怕彻底的改变,就像他没有勇气尝试毒品,赖纳是死于毒品的。于是他半真半假地成了夏尔,他打定主意要讲一个他眼里的美丽德国女人,以及她同她的德国前夫之间的爱,多么古怪,好像他自己不是个重要人物似的,好像他仅仅满足于从某个角度观看他的英格丽,她的侧脸,她的碎发,他四处跟踪她,像个密探。
她实在太值得一写了,以至于夏尔执意要从她的童年开始写起:1943年平安夜,北海之滨。小女孩穿着西伯利亚兔皮大衣,酒红色天鹅绒连衣裙,她开始用梦幻般的嗓音唱《平安夜,圣善夜》,在“元首”的照片底下唱给那些士兵听,那是她的第一次登台。好像他从那时候就认识她了一样,那不过是她后来讲给他听的——她居住的小城在战争里被毁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她的皮肤,可怕的变态性反应,她皮开肉绽,裹在纱布堆里像个干尸,可她有副金嗓子,她可以唱歌。她一直在唱歌,她是偶像,她站在舞台上,“像斗牛士一样沉着冷静、像僧人一样轻松专注、像妓院老鸨一样充满活力”。而赖纳是个暴君,他折磨身边每一个人,他让他的演员精神崩溃,羞辱他们,让他们哭泣,他一个接一个地换同性恋人,给他们钱、角色、毒瘾、死亡……他们都倾心于他,等着他来虐待,英格丽反抗了,他对她说:别走……别走。在法斯宾德的传记里,英格丽淹没在一堆名字里,爱玛、考夫曼、阿敏……可是对夏尔来说,她是他的主角,“美得要死”的德国女人。
“这条裙子是伊夫·圣·罗兰在她身上剪裁的,那是在蒙天大道五号……”这个故事英格丽一生讲过无数次了,伊夫·圣·罗兰,时装大师,有着普鲁士人的那种优雅,他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地测量着她的身体,他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肩胛的间距,膝盖的间距,“各种神秘的间距”,这让她觉得她身体的每一寸都那么宝贵,就像女王一样,歌唱女王和她的时装王子,而她,正要赶赴巴黎,在让·科克托的一部片子里饰演“女王”,那可是让·科克托啊,他真是代表了巴黎优雅精神的全部精髓。
夏尔也许是个撒谎精,但这毕竟是一本好看的小说,还和龚古尔扯上了关系。现在,英格丽·卡文和让-雅克·舒尔还活着,但是书中大部分人已经消失了,赖纳·法斯宾德、让·柯克托等,甚至曾经王子般的伊夫·圣·罗兰也于不久前去世,他们的华丽年代早已终结。
- “既然去了舞会,那就要跳舞” | 2008-07-04
- 草场地在跳舞:在舞者与非舞者之间 | 2008-05-22
- 草场地在跳舞:在舞者与非舞者之间 | 2008-05-09
- 别让孩子带着镣铐去跳舞 | 2007-06-04
- 会跳舞的建筑 世界十大古怪建筑 | 2007-0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