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4-08-26 16:27

![]()

在当代中国,讨论农业问题总是离不开城市化,因为人们似是而非地认为,所谓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这样的思路走到今天,已经使得乡村与城市、农业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土地撂荒,村宅凋谢,老年返乡则无乡可返。这一切,都在于受“二元经济论”的影响太深以及对城市化的误解,源于一些地方理解的城市化就是“盖房子赶农民进城”。
重读西奥多·W.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我们会发现这部发表于1964年的学术专著,说的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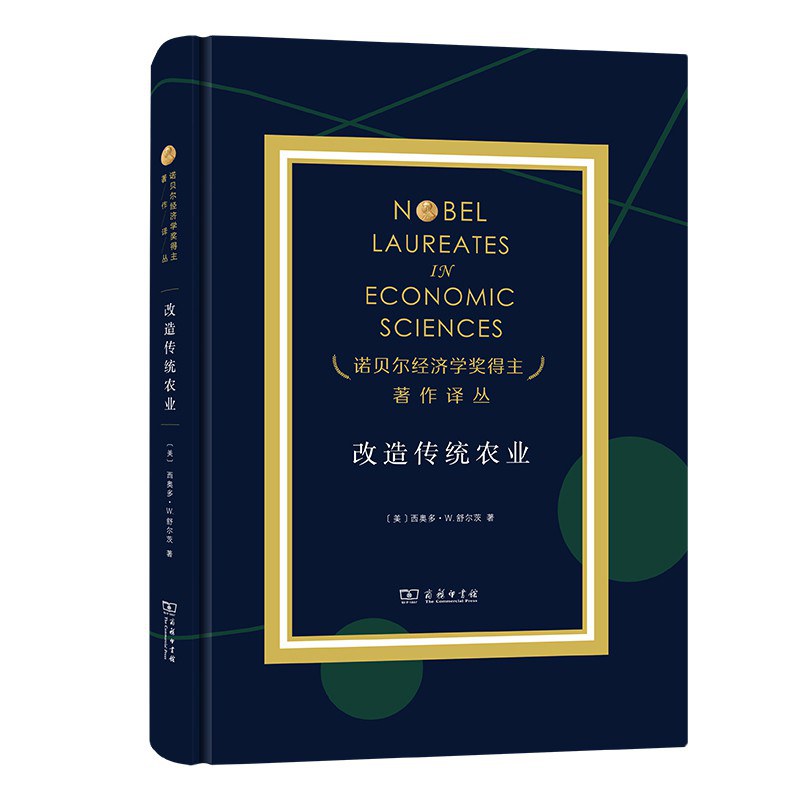
《改造传统农业》
[美] 西奥多·W.舒尔茨 | 著
梁小民| 译
商务印书馆
2021年3月
一、重读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关键是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W.舒尔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人力资本问题,然后把农业问题和人力资本结合起来研究,完成了“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于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的研究著述甚丰,《改造传统农业》是其杰出代表。《改造传统农业》这本著作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思想,其核心是:农业同样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加强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这里所讲的传统农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世世代代凭经验生产、几乎没有农业技术提升且相对封闭的农业。这完全不同于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认为,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舒尔茨认为,在给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了最佳配置,且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例如,农民种植的谷物的组合、耕种次数、农作时间、工具、役畜与农机设备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是给定技术条件下的最佳组合,不存在生产要素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即使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找不出传统农业中的资源配置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些生产要素是由传统要素组成的,农业的技术含量没有提高,是一个低层次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贫困”。但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资源已经得到了最佳配置,如果农业劳动力流失,就会造成产量下降。为此舒尔茨举了两个例子:秘鲁一个地方为了修一条公路,从附近农村抽走了一些劳动力,农业产出立即下降了。巴西的一个城市,因城市建设也从附近农村吸收了工人,农业产出也下降了。我国目前也因土地和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
舒尔茨认为,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列举了大量案例。例如,西欧虽然资源贫瘠,却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了农业生产。印度的土地灌溉面积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日本每英亩土地的产出却是印度的8倍。美国农业生产也很成功,大量出口并一度出现了产品过剩,政府甚至提出了减产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1961年间,美国耕地大约减少了10%,农业产量仍增加了50%。此外还有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其农业发展成就更是惊人,农业技术相当发达。
舒尔茨以生动的案例告诉人们,不能忽视农业,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古典、亮丽、永存的产业。一旦农业被忽视,整个经济结构就要失衡。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加强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如何改造传统农业呢?在舒尔茨看来,关键在于打破农业的封闭体系,使农业能够得到最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农业的现代化既包括对土地、种子、机器、耕种方式的改造,也包括农民的主观意愿、需求以及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农民必须是素质和能力提升了的新型农民。一句话,要用新质生产力装备和改造传统农业。
在考察了美国、西欧等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后,舒尔茨认为,传统的资本概念是有缺陷的,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和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于是他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本的概念。

《论人力资本投资》
[美] 西奥多·W.舒尔茨 | 著
吴珠华 等 |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年
舒尔茨所讲的人力资本,大致包括以下5个特质:
(1)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和熟练程度,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素质。
(2)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的投资形成的资本,例如对教育和健康的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和健康是生产型的资本。
(3)人力资本像一切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得到回报。
(4)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人的“时间价值”会提高,而且是一种必然趋势。
(5)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企业家型的人力资本。
根据以上分析,为了改造传统农业,必须投资农民的教育,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以期用更高层次的技术和装备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深刻地写道:“本书研究的中心论点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农业要素的供给者是在农业试验站工作的研究人员。农民的作用是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接受这些要素。然而,典型的情况是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寻求这些新要素。持续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舒尔茨不赞成“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舒尔茨认为,有一个广为流行的成见,即“把经济增长完全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在许多欠发达国家,这些看法形成了经济政策,于是所有的投资都向城市倾斜,认为农业不仅可以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还可以提供劳动力。这样的政策在扼止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扼止了经济的发展。
舒尔茨对压抑地租、压抑农产品价格,维持农业生产资料高价的政策也持批评态度。他指出:“一旦地租受到压抑,就会用各种特定的措施来占有土地及附属物的价值。现在已知的措施有:强制按某种名义价格交售农产品,按低的价格把农产品卖给国家,以各种名义对集体农场征税。此外,早期对机器和拖拉机站的服务实行高垄断价格也可以作为这种措施之一”。
一系列的压抑农业的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的效率。在我国,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资料每每随行就市上涨,一方面是每遇粮价菜价上涨,有关部门就出手干预。这种干预在扭曲市场价格的同时,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生产积极性。
二、误读刘易斯,并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舒尔茨提供了丰富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倒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建立其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因此,很有必要把二者加以对照分析。
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现代部门,主要是市场化的现代工业部门;另一元是传统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是封闭而低效的,甚至存在着“零值”,拥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只要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能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所谓的发展,就是通过发展现代部门——通常被理解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然,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应当反哺农业。
我国的一些学者,把这种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的模式叫做劳动力“红利”。然而,当我们按照“偏袒工业、轻视农业”的模式,高歌猛进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其实,舒尔茨并不认为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早年的马尔萨斯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工资铁率会把人口调整得恰到好处。
一旦城市化成为时髦的口号,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百般推崇和矢志不移地推动,同时伴随着对农业农村的空前轻视。不要说对农村的投资减少,就连农村的资源如劳动力和资本也被虹吸到了城市。所以,一方面是城市大规模地扩张,有的地方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下,摊大饼式地扩张,大量盖房子、引进人口。另一方面则是乡村的消失和“自卑”,享受不到公共设施投入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城乡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各种机会都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重点高校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产生了空前的城乡失衡。
于是,本来是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今形成了严重的城市失业。刘易斯本人后来在196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由于人为地城市化,加大了城乡差距,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后形成了城市失业。原因在于:
(1)城市居民的工资与农民收入的差距极大地扩大了。
(2)乡村教育加速发展,使得年轻人进城的势头更加迅猛。
(3)发展机会和福利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也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
在我国一些地方,基于“土地财政”的“圈地”,也使得农民进城很有积极性,相当多数的农民成了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当农民不打工要返乡了,却也无乡可返,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农村也存在着诸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
我们曾经靠着农业支援工业,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后果是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因而改革开放先从农村开始。现在,我们却又经常采取控制农产品价格的办法保证GDP的稳定。
受“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认为发展就是所谓的“城市化”,所有的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其实有两种城市化路径,一种是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化,外来人口有就业,城市有人气。一种是把城市化理解为城市扩张,结果是让农民进城,把农民变成移民。
其实,我们对刘易斯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刘易斯同样强调:“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为何总是同时进行。抑制了农村的购买力,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外需。外需受到影响时,经济发展就比较窘迫了。
农产品相当于经济学中所讲的“穷人产品”。所谓“穷人产品”,即在预期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人们会减少相对意义上的奢侈品,把有限的收入用于保证基本生存。农产品就具有穷人产品的特性,即使收入再紧张,人们也会把减少了的收入,用来购买基本的生存资料。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忽视农业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是拉大了农业国际间的差距。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国家现代化水平低,农村购买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国际市场。
三、重视农业并重新思考城市化
忽视农业,偏袒城市,并不遗余力地推进城市化的实践后果,已带来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使我们不能不回到舒尔茨的思路:重视农业,并重新思考城市化。
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国历史上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的主体产业,艰难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建国以后,我国工业化及其发展是通过农业支援工业的模式,具体地讲,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把一部分农业收入无偿地转移给工业。这种模式使本来脆弱的农业越发脆弱。
发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得到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在给定的条件下城市的回报高于农村,各种资源在价格机制作用下都流向了城市,打破了对农业具有保护意义的相对封闭的均衡。
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说明,我们不仅要改造传统农业,而且要重新认识所谓城市化的发展战略。
1、没有精壮劳动力的农村,不可能解决农业问题。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理论上说明,把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向农村,比投向城市更有效益。一位名叫麦克的美国学者指出,将城市的光芒照耀农村,也许比诱惑农民进城的好处要大得多。他说,正如马歇尔著名的推论,城市经济没有新的劳动加入的均衡水平,是由于“农村供给的冲击”与“城市需求的拉动”相等。换言之,只要农业的收入有所提高,哪怕依然比城市稍低一些,由于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综合效应”,农民也会选择留在农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但仅仅让农民留在农村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民的素质,提升农业的技术含量。布鲁斯·F·约翰斯顿在《农业发展战略的设计原理》中指出,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绿色革命带进来的技术突破,证明了强调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是正确的作法。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显示,基于现代科学知识和实验方法的技术创新,使得农业领域中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业有可能走上一条扩张发展之路。这种战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与生产效能越来越高的技术相关联。就是说,要用一切发达的技术装备改造农业,使农业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2、加强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投资。
我国的农业欠账太多,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仅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现在经济发展了,理所当然地应当反哺农村。大力建设农村的公共设施,包括交通、医疗、社保、教育设施以及对农村电网、水利设施的支持力度。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仅包括初、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还应当包括对农民的素质教育,即一系列农业新技术的培训。
3、通过对农业组织形式的改造,让千千万万的农民步入市场经济。
中国农业不仅有技术创新的问题,还有组织形式创新的问题。组织形式的创新就是通过合适的形式引导农民步入市场经济,这方面中国农民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
(1)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农民往往缺少冒险精神。
(2)市场经济需要对市场需求、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的了解,然而农民却处于信息缺失状态,特别是对市场走势的把握。
(3)市场经济下各种产业都需要最低限度的货币投入,个体农民难以拥有足够规模的资金。
(4)农村企业家人才是稀缺的。
克服以上的不足,引导农民步入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是把公司作为中介,一头联系着市场、信息、技术乃至资金,一头联系着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民,可以发挥企业家的功能,通过给农民提供市场需求、技术指导、乃至小额资金的帮助,以契约的形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组织起来。从实践来看,这一模式的效果是显著的。这一模式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处于龙头的公司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4、加强小城镇建设。
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很不经济。刘易斯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反思性地指出,基于对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人们总想把所有工厂都建在一个或两个大城市里。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查证明,一个城市在人口规模达到30万前,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他强调,相当经济的办法是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学校、医院以及其它能够吸引居民的设施。当最近的城镇在30公里之内,又有良好的道路时,人们将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路途遥远的中心城市。我们应当换一种思路:把农村建成小城镇,既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还能减轻一系列城市的社会问题,这可能是中国农业问题和城市化的真正必由之路。
5、不要干预和压抑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的价格一上涨就用行政手段干预,在扭曲价格的同时也就抑制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可以换一种思路,不是频繁地干预农产品价格,而是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给城市中低收入者以补贴的办法,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