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军/文 日本与德国同为二战的策源地和战败国,但是两国战后反思的进程和程度非常不同。德国基本上彻底清算了纳粹遗毒,实现了国际和解,开创了社会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新德国”。但是日本政府的战后反思,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右翼势力等因素的制约,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状态,不时在东亚引起波澜。
我们结合国际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德日二战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进行一下探讨。
一
1946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罪责问题》一著中,对于德国人战争责任所做的四个层面——法律(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灵魂)罪责——的区分,为我们理解和评估战后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罪责的反思,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伦理分析框架。
德国在二战后的战争罪责反思,基本体现了对“四重罪责”的深度反思和接受。在法律(刑事)罪责方面,德国通过纽伦堡审判、法兰克福审判等方式,追究了纳粹战犯的法律责任。在政治责任上,德国政府接受了对纳粹暴行的责任,对国际社会进行了公开道歉,还通过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家属等行动承担后果。在道德责任方面,德国社会广泛开展了对纳粹历史的教育和反省,强调每个公民对历史的认知和道德判断的重要性。在形而上学(灵魂)责任,德国通过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和系统的中小学教育项目,促进了国民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思,强化了抵抗不正义的全球责任感。
相比之下,日本对于二战罪责的反思,在四个层面上都显得不足。在刑事责任方面,虽然东京审判追究了部分战犯的责任,但日本国内对东京审判的接受程度,始终存在争议。在政治责任层面,日本政府虽然发表了多次道歉声明,但一直饱受邻国的质疑,这些被侵害的邻国认为日本没有充分承认其侵略行为和暴行。道德责任方面,虽然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对侵略战争的叙述,但对于战争责任和暴行的反省并不深入,且一直存在教科书审定和历史教育上的争议。在形而上学责任方面,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受害者的纪念和对全人类不正义行为的反省,相比德国显得较为有限,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反应也更加保守。
可以说,从雅斯贝斯的“责任概念”来看,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处理二战罪责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德国通过全面接受和反思四种责任,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深刻自我批评和道德重建;日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责任,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显著不足,尤其在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公开和深入讨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二
德国、日本的战争罪责反思,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国际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各种看法和意见,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国在历史认知、社会教育和国际责任感等方面的不同取向。
荷兰记者伊恩·布鲁玛在其1994年出版的《罪孽的代价》一书中,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布鲁玛将德日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归因于两国战后民主政治制度的差异——不是文化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决定了德日战后战争责任反思的差异。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著
倪韬 | 译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战后,西德在经历了盟军的去纳粹化、冷战的保守派回潮、中左翼自由民主社会力量的反拨和矫正,以及学生运动抗争和公共领域的理性探讨之后,最终走上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道路。相形之下,日本因为日美同盟政治体制对于战争追责不彻底(麦克阿瑟庇护裕仁天皇,将其排除出东京审判;冷战导致日本前军国主义者全面回归政治体制),使得日本右翼势力未能彻底清除和转变,不时沉渣泛起,制造波澜。
布鲁玛同样引用了雅斯贝斯“四种罪责”的划分框架,他强调指出,对于纳粹政权或天皇政权这些已经被废除的政权来说,“政治责任”是棘手的问题。日本政治、军事领导人的责任,因为天皇的模糊角色而变得复杂。
二战结束时,希特勒自杀身亡,为德国的罪行背了黑锅。希特勒受到的指责越多,德国人就越觉得自己得到了宽恕。但在日本,人民没有权利对国家政策投票,天皇也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1945年战败后,天皇在东京审判中逃脱了罪责,成为日本清白的象征:他的清白就是日本人民的清白;和天皇一样,人民也被军事领导人“欺骗”了。
但是,天皇实际上涉及日本帝国很多政治军事决策,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当时的日本民众也并非全被好战的宣传所欺骗,而是积极投入、支持侵略战争。战后,一个被欺骗的、无辜的、爱好和平的天皇的形象得以维持下来,因为这是战后日本的统一因素之一——和平主义的象征。日本民众及政府得以回避反思天皇政权、军国主义国家乃至庶民百姓的“战争罪责”,在迷梦中“幼稚地”自我麻醉,“天真地繁荣昌盛”。
三
2004年,德国历史学者曼弗雷德·基特尔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中,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德国、日本两国反思战争罪责差异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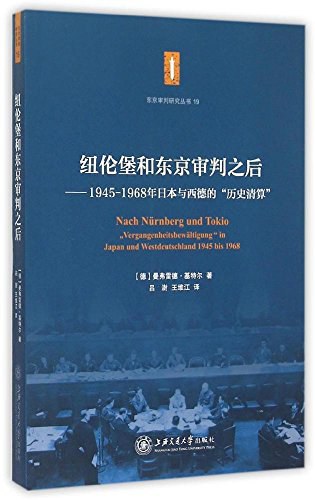
《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年-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
[德] 曼弗雷德·基特尔(Manfred Kittel)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吕澍 王维江 | 译
2014年9月
基特尔开篇即指出这个巨大差异:在一个幸存的美国战俘看来,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纪念战犯的方式,就像德国人计划“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了一座大教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总结说,日本人不像德国人,“在处理二战期间制造的暴行和可怕灾难时,既不公开,也不诚实”。
基特尔尖锐地指出,二战后,日本对待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一直维持着“没有多少正义性”的认识,耿耿于怀的则是基于广岛、长崎核爆经验的“受害者意识”;有关历史罪责的讨论,只是强调政治军事主政者要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而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西德则坚决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公开承认纳粹主义是“民族的集体耻辱”,彻底清算了纳粹主义,左中右各翼政治派别一致达成了反纳粹主义、反极权主义的社会共识。
基特尔认为,德、日“历史清算”的巨大差异,是由一系列国际、国内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因素的差异决定的。
第一,是纳粹种族屠杀犯罪行为的极端特殊性。纳粹实施的犹太人“种族大屠杀”,因为带有工业化、现代性的恐怖维度,初看起来比日本的“战争罪行”强烈得多。虽然日本的战争罪行事实上也无比残暴,也带有种族灭绝的特性,但在“德国罪行”的陪衬下,看起来没有特殊性。
相反,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人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掩盖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德国人尽管在二战后期遭受了盟军的战略轰炸和“东部驱逐”,遭受了苏军的“内姆斯道夫屠杀”,但是却难以逃脱罪责——即所谓“德累斯顿和内姆斯道夫不是广岛;南京不是奥斯威辛”。
第二,盟国占领军在德国进行的“去纳粹化”措施比在日本实施的“去军国主义化”更为有力。同时,冷战局势对欧洲和日本的记忆文化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冷战开始后,日本作为美国单独占领的抵御东亚共产主义的堡垒,在历史记忆文化方面受到的国际压力,远远小于亟需融入欧美国际经济和欧洲国防安全共同体的西德。
第三,由于内战阻碍、民族分裂的原因,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受损害最大的中国、韩国人民,未能对日本提出强烈的赔偿要求,其中的核心是要求日本对“反人类罪行的受害者”进行赔偿。日本国内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能从内部呼应中国、韩国施加的外部压力。
第四,日本、德国虽然经历了类似的民主化改造,拥有相似的民主制度基础,但政党政治差异明显。
对于1949年—1969年执政的德国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政权)来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因素和自由民主主义因素的融合,使联盟党经历了对于纳粹主义的深入反思和内部转变,转化为西德全民性的中间阶级代表党,积极融入欧洲和西方来寻求国家的未来。而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从未发生过反军国主义抵抗运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执政,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内部反思和思想转变,在精神上仍然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的延续。
德、日政党政治的差距,从德、日(左派)反对党的比较中也可见端倪。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态度,是与前纳粹政治保持距离,尤其是之前被纳粹迫害者,力主彻底进行“历史清算”。而日本的左派政党(日共、社民党)不仅政治上羸弱,在民族历史记忆的议题设置上也很被动,因为它们担心此类竞选主题不会引起选民的兴趣,或者偏向于“反美的民族和平主义”,把“核爆受害者”设置为中心议题,却未涉及日本军队的侵略罪行。
第五,马克思主义者主宰的日本历史学界,在记忆文化上鲜有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力有限。而西德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处于社会的“主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虽然强调切割俾斯麦/威廉“第二帝国”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第三帝国”,辩称威廉德国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与希特勒政权“生存空间”的狂想之间具有非延续性,但也坚决地与第三帝国制度及其罪行保持距离,将之钉在耻辱柱上。
而在1952年美军撤离之后,日本的历史记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反思和质疑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声音,在教育文化机制里越来越少。在日本,不论学校、媒体、政府和议会,几乎都没有传播现代史的问题意识,“历史清算”在1950—1960年代的年轻一代中几乎没有影响。
第六,德、日民主制度建设中,政治精英的精神反思和思想转变的程度不同。
阿登纳时代,一些存在严重历史问题的“纳粹精英”,在西德司法界、警界乃至国防军中受到重用。德国左翼历史学家韦勒曾主张,这些纳粹追随者应该被“排挤到社会边缘”,以便进行民主化建设。但是基特尔辩称,阿登纳时代这种“被屈从的政治投机”,使得“前纳粹精英”中不少成员有了向自由民主主义、反纳粹主义转变的思想基础,西德的民主建设得以巩固。战后,日本民主政体中同样融入了大量前军国主义政权官员,但其家长制寡头官僚体制结构得以长期存在,原因在于日本政治体制中人员和思想上“清算历史”的不彻底。
最后,基特尔也强调,在日本这个曾经盛行武士道的国家里,核爆经历和去军事化过程,使得和平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在社会扎根,深刻影响了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变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很难再度复活、泛滥,为害国家和国际社会。布鲁玛所谓日本历史反思“幼稚化”的说法,并不确切。
日本学者宫泽浩一和德国学者奥斯滕对基特尔的研究评价很高,认为基特尔的研究是德国历史科学第一次以系统的比较眼光,揭示日本战后历史反思与德国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基特尔探讨的日本缺乏“历史清算”的后果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残余——并不仅仅限于极右派及其末流“政治暴力犯罪组织和讹诈集团”——在日本至今犹存,为祸不已,值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警惕。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成名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积极支持德国发动战争,鼓吹德意志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浪漫主义。他盛赞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为“实干家”;狂热崇拜德意志军队,声称“天才在于军事组织和军人美德”。
年岁渐长,面对纳粹主义的汹汹来势,曼才逐渐觉醒、成熟,逐渐与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潮流决裂。纳粹掌权后,托马斯·曼只能远遁美国,声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回忆初见托马斯·曼时说:“那时我觉得自己是成年人,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躯壳里;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躯壳里的孩子。”
或许可以说,托马斯·曼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思想、精神上成熟的历史,就是一个个体从孩童到成人精神成熟的历史;德国彻底地反思二战罪责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历史;而日本,尤其是其右翼、极右翼政治势力对于战争罪责反思的推诿、暧昧、回避和不彻底,则是这个民族——正如麦克阿瑟所谓“日本在政治上只是个12岁的孩童”的评价所暗示的——精神发展上虽不“幼稚”,但仍未成熟、仍然需要成长的征候。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