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工作的吕振兄前些日子寄来几本他这几年出版的书,其中那本署名“雪野”的《望乡书》我最喜欢。他在这本书里写他的村庄、他的亲人、他的童年、他的学校和他的乡村文化史。雪野是八零后,《望乡书》既是一位八零后作家为自己的村庄写就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他献给老村老屋的自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
鉴于此书的记录全面与记述细致,多少年之后,其社会学意义或许会等同它的文学价值。这也是我边翻此书边感叹的原因。我的老家距雪野的莱芜故乡不过百余公里,《望乡书》中记录的许多场景、风俗与情愫,我读起来都有“家乡感”。我一直以为我们六零后一代对当代农村翻天覆地的变迁感受尤其深刻,没想到这一场老村内外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位八零后回忆起来竟如此刻骨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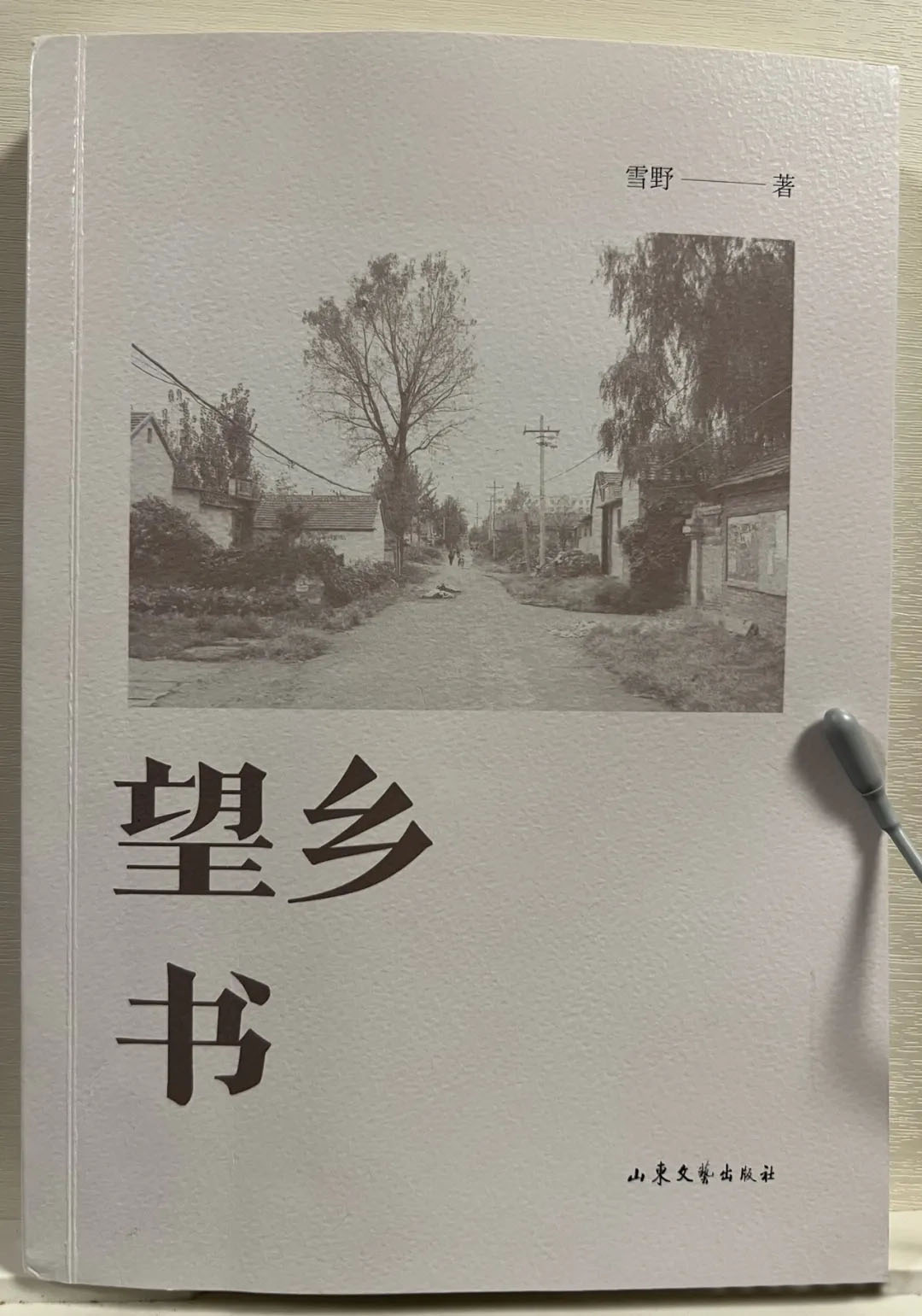
今晚我终于承认我写不出这样的书。我在农村刚刚开始巨变的1979年离开故乡,从此不仅远离农村改革的历史现场,更疏远了城镇化后父老乡亲生活的震撼与阵痛。我没有完整经历几十年间农村的渐变或突变,更没有记录这一变化过程的机会与积累。但是,八零后却可以完成这一见证与存史的使命,雪野他们这一代农村变革中长大、大学毕业后进城的作家,既有资格为“空心化”的故乡招魂,也有情怀为故乡的消失洒泪告别。
况且,雪野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大姓,他的曾祖和高祖于1920年代还照过一张合影,而且这张合影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今天,这真是命运的赐予。

今晚我终于承认我写不出这样的书。我在农村刚刚开始巨变的1979年离开故乡,从此不仅远离农村改革的历史现场,更疏远了城镇化后父老乡亲生活的震撼与阵痛。我没有完整经历几十年间农村的渐变或突变,更没有记录这一变化过程的机会与积累。但是,八零后却可以完成这一见证与存史的使命,雪野他们这一代农村变革中长大、大学毕业后进城的作家,既有资格为“空心化”的故乡招魂,也有情怀为故乡的消失洒泪告别。
况且,雪野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大姓,他的曾祖和高祖于1920年代还照过一张合影,而且这张合影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到今天,这真是命运的赐予。
这是一张摆拍的父子照。摄影师把他们请到老屋外面的窗台前,父坐子立。椅子、茶桌都是刚搬出来的,茶壶茶杯是精心布局的,两盆夹竹桃左右对称摆放,背景上方中央是栅栏式糊纸木窗,窗台上居中放着的,是仙人掌盆栽吗?照片下方中间的那盆花,雪野说是金钱莲。照片上的父与子,雪野的曾祖与高祖,照相时的穿戴堪称“盛装”,那应该是过年才会有的打扮。1920年代,有多少农村家庭可以有这样的排场?有多少父子可以消费得起这样的摆拍?雪野说这张照片看上去是“普通的乡绅之家”。我觉得没那么普通。
这张照片正是作者对故乡故土、老屋大族视觉记忆的起点,或记忆起点的视觉。他们家院子的年龄即使从照相时算起也一百年了。“一进院门,有一棵老白杨树,两个大人才能合抱过来。它静静地立在那里近百年,见证了这个院子的人事代谢、荣辱兴衰。”雪野说,“我的高祖父、高祖母、曾祖父和三叔,在这个老屋里相继去世,他们我都没有见过。自从我记事起,在这个院子里送走了我的曾祖母、爷爷和二叔。这三次丧事,我都有着深刻的记忆。”
他没见过自己的高祖父母与曾祖父,但是,他却可以见到高祖父母与曾祖父无论如何见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事,那就是这个老院子、老屋乃至整个村庄的消失。《望乡书》中那篇《老屋》雪野这样结尾:“今年春节回去,有位本家伯父,指着院子里那两棵银杏树告诉我说:'你爷爷当年栽下的这两棵银杏,现在是村里最老的银杏树了。爷爷栽树,孙子乘凉啊!'他还告诉我,市里要进行旧村改造,这老房子都要拆掉盖成楼房,银杏树也要砍掉。我不敢去想,如果这老屋不在了,银杏树不在了,还有何物能寄托这无尽的乡愁呢?”

乡愁?等“乡”陆续消失,以后或许就没有“乡愁”了。岂不闻,深圳的衡水籍作家王国华正在中国最年轻的城市里呼吁留住“城愁”。乡村城镇化了,乡愁也就城愁化了,是这样吗?既然没有了“乡愁”,雪野也就不用发愁“何物能寄托”了。
可是,雪野他们这一代人还偏偏要问“乡关何处”。《望乡书》中他就是以一篇《乡关何处》结尾。他的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很快会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他的父老乡亲,抬头再望不见银杏树,望见的却是几栋高楼。雪野只好自我安慰说,故乡会转变为精神和观念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心里建造一个自己认可的故乡”。
我勉强可以认同八零后一代心里的“乡愁”,尽管我认为他们可以从此淡化一下“乡愁”也未尝不可。当然他也说他已经认同了现在居住的大城市,还是“深层次的心理认同”,但是,他接着说了一番我不怎么认同的话。“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庆幸自己生在农村,是农民的儿子。”他说,“我在农村生活过,后来又到了城市,既能过穷日子,也能过富日子;既见过百姓生活的艰辛,也见过高官富贾的安逸,这种人生体验是相对完整的,这样才能了解真实全面的中国。相反,如果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可能再到农村体验生活的机会就很少了,就不会和土地、和农民建立起实质性的亲密关系,就缺少了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一个视角。”
我绝不庆幸自己生在农村,尤其是生长在1960、1970年代的农村,尽管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只要有可能,我不要通过“穷日子”来让自己的人生体验完整。我不要通过挨饿受穷来了解“真实全面的中国”,我宁愿从小就在富足日子里建立真实全面的自我。至于是否和农民“建立实质性的亲密关系”,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这就是六零后的农民后代如我,和八零后的农村子弟如雪野的区别了。我们成长在不同时代的农村,对土地和苦难的感情自然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羡慕他们家有那样一张来自1920年代的老照片。1920年代,我的父母相继出生,但我对我们家的那个时代无从记忆,也就无从说起。这也难怪我快把雪野的《望乡书》读成我自己的“忘乡书”了。
胡洪侠/文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