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丹亭/文
1902年,沙俄军官、地理学家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奉命考察乌苏里边区。对于当时的他来说,那里比潘多拉星球还要遥远、诡谲、神秘。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北上,亲眼见到了无数美不胜收的景象,也历经了一次次生死考验。此后8年间,他又对这里进行了3次大规模考察,对当地的居民、动物、植物、气候、地貌进行了详尽的记录。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德尔苏·乌扎拉》和《在锡特霍山中》三部书稿,前两部在20世纪70年代以《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为名在中国出版,近几年又多次再版。阿尔谢尼耶夫的《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也被引进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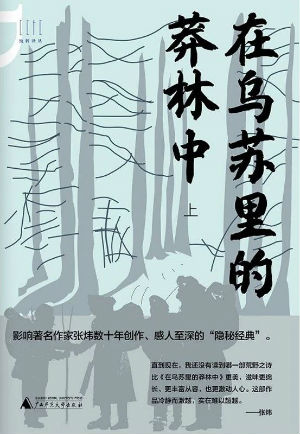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苏联]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 著
西蒙 | 译
纯粹Pura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阿尔谢尼耶夫不仅是一位优秀学者,也是敏感的观察者和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在考察中,即便身处危险,他也依然醉心于乌苏里莽林的美丽与变幻莫测。正因如此,这片土地把它最瑰丽、最暴虐的面貌一一向他显露:他邂逅过美如宙斯化身的求偶公鹿,遭遇过模仿鹿鸣的猛虎,目睹过貉子捕鱼、野猪迁徙……他在森林大火和暴雪中幸存,与激流搏斗,遭受过匪徒“红胡子”的伏击……这一切被他写得跌宕起伏、雄奇壮美,堪与伟大的英雄史诗比肩。
阿尔谢尼耶夫的文本尤其最令人着迷的,是其展现出的多义性。阿尔谢尼耶夫笔下的乌苏里莽林,看似远离人寰,实则如同一面镜子,映出的是处于变革之际的文明世界的倒影。无论我们把他的作品当作自然文学、科考记录还是民族志来阅读,都不可避免地触及丰富而多元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与“野蛮”的对峙、移民和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国家地缘关系、个人的身份与归属……
化外之民
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是在一个剧变将至的时期进行的。考察除了科学目的,也承担着收集军事、经济、民族资料,及对乌苏里地区复杂的人口构成进行摸底调查的任务。
乌苏里地区,是指乌苏里江以东直至太平洋海岸的大片区域。这里对于沙俄是一片崭新的土地。1858年和1860年,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清帝国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乌苏里地区也包括在其中。这里少数民族众多、外国移民混杂,是“化外之民”的理想栖身之所。少数民族在乌苏里边区定居,为的是在强势民族和国家政权的指缝里寻求一点生存空间。他们躲藏在国家建构与权力鞭长莫及的深山老林之中,以最艰难最原始的方式求生。而来此定居的各国移民,大多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在故土立足,只能冒险前往莽林深处寻求新的生存之道。
从某种角度看,生活在边区的人都是国家权力和制度的漏网之鱼,而阿尔谢尼耶夫对乌苏里居民的考察,实际上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他是居民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一方面,他又在潜移默化地试图将化外之民归入“化内”,纳入整个社会架构之内。与此相对应的是,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帮助,考察根本无法进行,这也给了阿尔谢尼耶夫接近不同种族,细致观察、记录他们的生活、劳作和家庭关系的机会。阿尔谢尼耶夫着墨最多的,是戈尔德、索伦、乌德盖、鄂伦春这几个民族,他们多为女真后裔,靠渔猎为生。他们或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或被中国人同化,变成所谓的“鞑子”。由于阿尔谢尼耶夫并未在书中对这些民族做出明确界定,为避免混淆,本文在此稍作考证:
戈尔德人(通常译为果尔特人),可能是指赫哲人。据考证,俄国人一般用“果尔特”来称呼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赫哲人。
索伦,推测和鄂温克指的是同一民族。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书中,这两种称呼都出现过。在历史上,“索伦”曾是鄂温克、鄂伦春及达斡尔人的统称。直到清朝中期,“索伦”才为鄂温克族所专用。
乌德盖人(一译乌德海人),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土著民族,很多学者认为他们与满族同宗同源。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统一被视为俄国公民。
阿尔谢尼耶夫记录了土著居民精湛的狩猎和野外生存技巧,以及从容应对极度严寒的本领。他们常年与自然角力,在最险恶的处境中也能求胜;他们是天然的地图阅读大师——因为山川树木的影子早就在他们头脑里编织出了一幅幅精密图像……然而,阿尔谢尼耶夫也悲哀地察觉到,这传承千年的能力和智慧,正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些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即便有着出神入化的体格和技能,面对天花病毒和外来文明也不堪一击。
土著居民从前只懂得以物易物,即便是最好的猎手,也不知道猎物在“文明世界”的价值,轻易就会被欺骗;他们甚至不认识钱,只能根据纸钞的数目来臆断价值。有人利用这一点,欺骗他们欠下巨额债务,再残酷地压榨、奴役他们。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几乎每个失去男性劳力的土著家庭都面临着沦为奴隶的命运。鸦片也污染了这片土地,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家家户户吸食鸦片,连一两岁的婴孩也不能幸免。
土著居民的遭遇一次次触动阿尔谢尼耶夫,在这片物产丰富,但生存空间和资源极为紧缺的土地上,民族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竞争正日趋白热化。他看不到这些处于两个庞大封建帝国夹缝中的民族的归宿究竟在何方,也许只有默默消亡,或者迁往莽林更深处……
中国人和“蛮子”
在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中,中国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
根据他的记录,生活在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被俄国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称作“蛮子”。(沙俄地理学家伊凡·纳达罗尔的《北乌苏里边区盖现状概要》一书则认为,“蛮子”主要是指汉人。)这个称呼颇具意味:自古以来,作为“天朝上国”的子民,中国人习惯将异族人称作“蛮夷”,可一旦视角变换,一向自认为处于文明轴心的人,也会变成“蛮子”。这一称呼,映照的是居住在乌苏里的中国人,其处境的窘迫、尴尬,特别是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通过一纸条约,沙俄占据了大片土地,但想要去除中国的烙印,却难上加难。首先,乌苏里地区有许多中国人长期从事农业、渔猎、商业等活动。俄国科学院学者亚·格·拉林在《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一书中记录道:《北京条约》签署时,乌苏里边区居住着2000至3000名来自中国的狩猎者、淘金人、采参人、逃荒者,以及流放罪犯。即便土地划入沙俄,中国人在经济和文化上,依然处于强势地位。大量少数民族居民已被中国人同化,在经济、生活,甚至农业生产上对他们形成高度依赖,少数民族的孩子也在中国人开办的学校学习……乌苏里地区实际上成为了中俄两个帝国激烈博弈的前沿阵地。
第二,沙俄政府希望可以对乌苏里进行开垦,而当时在此进行农业活动的主要是中国人。据亚·格·拉林考证,19世纪末,有近两万名中国人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19世纪80年代起,俄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将其治下的欧洲农民迁移到这里,给予优厚的补贴;与此同时,将中国农民从他们开垦的土地上强制迁走。然而,乌苏里自然条件复杂,俄国式的粗放耕种方式无法适应。不少土著或哥萨克人,干脆把政府分配的土地租给中国人耕作。
在此背景下,阿尔谢尼耶夫在文本中呈现出的对中国人的复杂态度,其实也是沙俄帝国对华态度的缩影。在称赞中国人勤劳、谦恭、大方、团结互助、有惊人的生存智慧和致富能力的同时,他也将其视为强劲而危险的对手。他认为,中国人是无法“归化”沙俄社会的,他们身处异乡,却能够迅速建立自己的社会架构——村社、族长、家法、帮会……沙俄政府对此无力插手。这也为乌苏里边区带来许多问题:一些不法之徒偷越边境,拉帮结伙贩卖鸦片、白酒,将低劣的产品高价卖出,又压价从少数民族手中骗取值钱的货物,更有甚者,他们用虚构的债权奴役他人,瓜分地盘,形成垄断。某些中国人为了最大限度获利,进行掠夺性开采,哄抢自然资源、矿产、珍稀动植物。这种野蛮的攫取,为生态带来了不可修复的破坏。他的书中详尽记录的中国人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谋生方式(他认为他们种地不过是为打猎和捕貂提供粮食的工具而已)作为参考:捕猎——猎鹿(及养鹿)、捕麝、猎貂、猎熊、猎虎;采集木耳和苔藓;捕捞河蚌获取珍珠;打捞海产品——海参、海带、章鱼、螃蟹、虾、扇贝、海虹;挖掘人参和黄芪……而由此获得的资源或者金钱,往往流向中国。
尽管著作中处处流露出地缘博弈所引发的忧虑,阿尔谢尼耶夫还是尽可能客观、翔实地记录着一位位具有魅力和弧光的中国拓荒者。通过他的描摹和特写,我们得以从历史尘埃中,分辨出中国移民的面貌。他写过沉默寡言,却胸有定见的挖参老人,是他将科考队带离了险境。他写过不计回报的中国主人,把他们付的住宿费丢到门外,又跋山涉水为他们运送给养。他写过讲述宽永王历史的老人,金戈铁马的古老时代在他的叙述中栩栩再现……还有一位贯穿阿尔谢尼耶夫几部作品的张姓“中国队长”,此人极具威望,侠肝义胆,带领中国和鞑子青年追击“红胡子”,还参与了阿尔谢尼耶夫在1907年的科考活动,成为他最仰赖和信任的伙伴之一。
阿尔谢尼耶夫着力描写过一位独自在乌苏里无人区居住了34年的老人。他因与家人结怨,将自己放逐到莽林深处。他对阿尔谢尼耶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追悔中对着熄灭的篝火枯坐了几小时,艰难地做出了重返故乡的决定。他拜别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山川草木,走上归途……这位老人的故事,也是许多乌苏里的中国居民的人生缩影——无论多么奋力地在莽林中求生,用自己的语言为这片土地的山水命名,他们似乎都永远是异乡人,是远离故土、丢失身份的“蛮子”。他们深入莽林,不过是在苦求一条重返家园的道路。
最后的赫哲人
阿尔谢尼耶夫在作品里记录了无数乌苏里居民,他们当中最耀眼、最不朽的,是猎人德尔苏·乌扎拉。《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将这位藏身莽林深处的“最后的赫哲人”展现在世人眼前。任何一部虚构、非虚构作品中,都找不出能和他比肩的人物。德尔苏全程参与了阿尔谢尼耶夫的前三次考察。他们不仅是默契的伙伴,更是生死与共的兄弟。1906年第三次考察后,德尔苏在森林中被歹人杀害。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也是阿尔谢尼耶夫献给这位异族兄弟的挽歌。
德尔苏的传奇能够被记录,纯属一个巧合。他毫无预兆地闯入了阿尔谢尼耶夫的科考日记,靠着自己的魅力逐渐成为记述的主角。1902年考察之初,科考队偶遇了土著猎人德尔苏。当年的他53岁,高颧骨、单眼皮,皮肤黝黑,个子不高,肌肉发达,全身散发着质朴、祥和的气息。德尔苏和阿尔谢尼耶夫如此投缘,从此便自然而然地陪伴在他身边。这位赫哲猎人有着高超的生存本领,能预言骤变的天气,推断野兽的行踪,也能像阅读书籍那样查看土地的印迹,读取其中的所有隐藏信息。他在暴雪、急流、山火和老虎口中,多次挽救阿尔谢尼耶夫的性命。和德尔苏的接触越密切,阿尔谢尼耶夫就对他越着迷,这位学者全方位地记录了德尔苏的言行与世界观,使他那瑰丽、丰富、纯净的精神世界得以留存。
德尔苏的世界观极其绚烂、独特。他将万物生灵、日月星辰、金木水火都称作“人”。他天然地将主体性赋予世间的一切,坚信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都和人一样,有情绪和盘算,有善恶和言语。他说虎守护着森林,鱼会骂人,熊和鸟狡猾,鼯鼠则是死孩子的灵魂幻化的。在他的世界里,大地是头枕西南的巨人,雾是饿殍的游魂,水和火都被强烈的生命力支配,终日嘶叫、哭泣、玩耍,北极星则是一个顶大的人,星星都要绕着他转。就连外来的录音机和墨水(他叫脏水)也被他赋予了值得赞赏的人性。他还说过,灵魂不是人和其他生物所独有的,并以此来解释海市蜃楼的成因:“不仅人、走兽、鱼、鸟、昆虫有灵魂,而且植物、石头以及一切无生物也有灵魂。人睡觉的时候,灵魂离开肉体,到处游逛,看到各种景物。无生命的灵魂也可以脱离本体,海市蜃楼就是这些事物的灵魂,因为这些事物正处于静止状态。”有趣的是,德尔苏对天文现象的理解却相当务实:当流星从天空划过,他不会把这与人的生死联系到一起,而是简单地说:“一个星星掉落了。”当士兵为彗星的出现恐惧时,他淡淡地表示:“他常常自己在天上走,跟人从来碍事的没有。”
在德尔苏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仁爱和利他主义信念。正如阿尔谢尼耶夫所说,“原始的共产主义精神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切行动”。他把自己打到的东西平均分给所有人,也不分民族界限。在森林的窝棚过夜后,他会修补外墙、补充给养,供后来者使用。他不允许阿尔谢尼耶夫伤害老虎,把吃剩的食物留给动物……德尔苏的存在有力地反驳了人性自私论。他身上自发的利他精神,以及对他人全心全意的信任,似乎本不可能出现在生存资源奇缺的乌苏里莽林。但或许,百万年来,支撑人类族群在逆境中活下来、逐步走向文明的,正是“唯有仰赖彼此的帮助才能幸存”的朴素信念。
作为一支古老族群的最后一人,德尔苏身上背负着渔猎民族的智慧、高超精绝的技能、以及淳朴善良的道德观念。但是,独自肩负这一切的德尔苏,内心总是孤独和悲凉的。他一次次向阿尔谢尼耶夫诉说自己被亲人环绕的童年生活,流着泪悲悼被天花夺走生命的妻子和孩子……他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宿命——如同所有史诗、神话中的英雄,他也抵不过衰老这位宿敌;他多次问过阿尔谢尼耶夫同一个问题:以后怎么办。他其实早已预知自己逃不脱死亡的落网,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以放弃自己的生存方式为代价,前往大都市安享晚年。《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一书,以德尔苏的死亡而告终,这也预示着乌苏里莽原的传奇即将终结……几十年后,阿尔谢尼科夫在《乌苏里山区历险记》的后记中沉痛地写道:“这个地区开始失去其特色,正经历着不可避免的文明所带来的变迁。”
而德尔苏的乌苏里莽林,永远留存在阿尔谢尼耶夫写下的字里行间。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