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入秋/文
并非只是普通的“焦虑”,
而是“恐慌”和“神经症人格”
当代表着焦虑的橙色情绪“焦焦”惊恐地张大眼睛,抓着头脑总部控制台的操作杆,周遭的橙色旋风发疯般旋转,我们看到了恐慌症发作时脑内状态的具象化情景。而这样的恐慌,仅仅是由一场冰球比赛中的犯规暂停引发。在《头脑特攻队2》中,这高潮的一幕不仅刺激着故事中13岁女孩莱莉的神经,也刺激着坐在大银幕前的所有观众——显然,这已经不只是普通的焦虑情绪了,躯体化的恐慌状态和神经症人格才是《头脑特攻队2》所呈现的核心。比“我不够好”的信念在女孩莱莉的头脑中回荡更严重的是,在“自我”完全由焦虑塑造后,莱莉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对的事情”,她无法开心,无法哭泣,直到那个一直把握着一切的“焦焦”在事态失控后,恐慌着流出了眼泪。
“恐慌症”和“神经症人格”是怎么发生的呢?《头脑特攻队2》显然关注着这个当下困扰着许多人的心理学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坦言自己仿佛“做了一次心理咨询”的原因。
作为续作,《头脑特攻队2》的剧情并不复杂。女孩莱莉进入了青春期,情绪变得起伏剧烈且难以控制,在她的脑内世界,头脑总部的控制台警铃大作,各种情绪角色哪怕只是轻轻碰一下按钮,都会让莱莉做出强烈到超出常理的反应。莱莉仍然在打冰球,在即将升学时,她得知两位一起打冰球的好朋友无法和她进入同一所高中,这个消息让她措手不及。于是,“我不想没有朋友”这个念头,成为了她接下来所有行为的核心驱动力。
与此同时,头脑总部也迎来了强势的新情绪。在“快乐”“忧伤”“愤怒”“厌恶”和“害怕”这5种情绪角色的基础上,新的情绪随着青春期到来。橘黄色的“焦焦”很神经质,绿色的“羡慕”总是星星眼,巨大的穿着帽衫的粉色“尴尬”总是一手汗,还有紫色的“丧丧”总是躺在沙发上。很快,“焦焦”拔掉了过往莱莉的信念所形成的坚信“我是个好人”自我,并把先前的5种情绪赶出头脑总部。
在同样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心理咨询过程的畅销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中,探讨了儿童的基本情感:“快乐和深情、愤怒、悲伤、恐惧。所有这些情感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自然型儿童,而这是整个儿童自我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基本的情感关乎人的“感受力”,莱莉的新情绪焦虑、尴尬等更多是人在社会化之后,对周遭刺激的反应。最基础的感受力由儿时开始,离开了它们,人很难健康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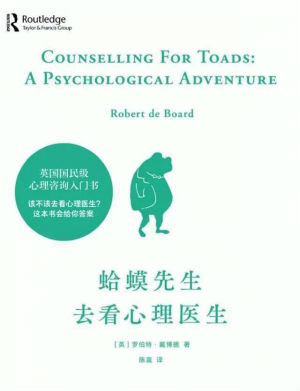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英] 罗伯特·戴博德 | 著
陈赢 | 译
果麦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青春期确实是头脑主导情绪的一次“移权”,面对更多现实压力和混乱、难以控制的情绪,青少年没法再自然而然地由“快乐”等基础情绪主导自己,开始体会到“焦虑”等复杂的情绪。但是,并非所有经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都会陷入“恐慌症”和“神经症人格”的困扰。
有趣的是,莱莉本人不是天生会恐慌的“神经症人格”。在恐慌症发作的时候,被焦虑操控的莱莉执着于要在冰球集训最后一天的比赛中获得第三分,撞飞了自己初中的好友,被教练判罚下场两分钟。同样的场景在电影的开头也发生过——莱莉在比赛中不小心撞人,被罚下两分钟,她发了一下脾气,平静地坐在场下。等她上场的时候已经到了赛末点,她和两位好友配合,在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之前完成了绝杀,为球队取得了胜利。
同样的处境,失去基础感知的莱莉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天壤之别,她对自我的认知与对客观现实的判断出了问题,让她陷入了失控的恐慌状态。
这样的对比正验证了神经症人格的特质——“神经症人格不可避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痛苦,必须为自己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的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的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被焦虑塑造的“自我”
和对“客观现实”的感受失调
焦虑到底是什么?在《头脑特攻队2》中,当焦虑出场的时候,解释了“焦虑”与“害怕”的区别:害怕是对肉眼可见的此刻的危险的反应,焦虑是对未来看不见的危险的反应。
对此,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有更精确的心理学定义:“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神经症人格的焦虑涉及的是内心所感受到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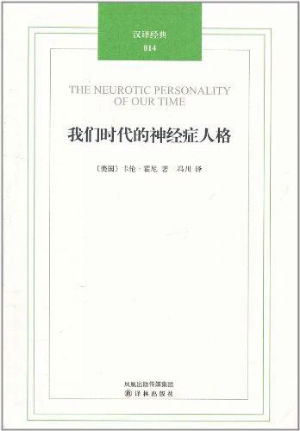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美] 卡伦·霍尼 | 著
冯川 |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5月
这很有趣,提防着“未来的、看不见的危险”看起来是一种成熟的、有预见性的理智,但当我们冷静下来会发现,这种“想象中的危险”其实是一种无穷无尽、无法植根于当下现实的“推测”。这种“想象中的危险”此刻并没有发生。事实上,我们无法真的为它做些什么。
当焦虑主导着莱莉,莱莉就失去了“判断自己的恐惧是否真的会发生”的机会。在故事中,莱莉所害怕的是初中的朋友离开了自己,上了高中就不会有朋友了。“焦焦”让头脑中的插画师们不停画着莱莉没有朋友、独自一个人吃饭、只有老师知道她的名字的场景,来加强莱莉的恐惧。但从现实层面来讲,这样的几率大吗?
显然,莱莉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那种女孩。当她凭自己的信念与本心行动的时候,她不顾同学的排挤,帮助了被嘲笑的女孩,于是拥有了初中时期的闺蜜。这样的缘分并非计划出来的,也不被恐惧驱动,正相反,是勇气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获得了自己的“想要”。所以在影片中,“焦焦”所渲染的那种让莱莉不择手段行事的“孤身一人”的恐惧,在现实里几乎不会发生。
为什么莱莉认识不到这点?因为不论是她的基础情绪,还是她的自我,都失效了。普通的焦虑不会让一个人失去自我、失去感受力,但在情节设置中,“焦焦”这个角色远非焦虑情绪那么简单。她来到头脑总部,就很快拔掉了莱莉的信念构成的自我,并且赶走了快乐、忧伤等情绪,让莱莉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和对周遭的“核心感受力”。这种破坏程度更像是由极端焦虑导向的“神经症人格”,也正因如此,一些观众对这部电影提出了“妖魔化焦虑情绪”的质疑。
这种质疑并非没有现实根据,在最初的创作动机中,导演与编剧们想探讨的就不是普通的焦虑情绪。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导演凯尔西·曼坦言,他想创作的就是一部关于焦虑的电影:“焦虑是关于潜在的威胁,恐惧是你对已知威胁的感知。如果假设老虎无处不在,那我们就更可能安全。但这可能会让你不堪重负,一切都是为了未来。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如何只担心现在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如何管理焦虑,这也是我们试图在这部电影中加入的内容。”
这样的创作核心听起来很实际,甚至有些工具价值,并不像过往皮克斯动画重视“生命体验”的创作理念,而是近似于人们在心理咨询室中面对与剖析的问题。
这样的创作方向或许正是从现实中演化出来的。面对皮克斯14%(175名工作人员)的裁员计划、来自母公司迪士尼的压力,还有近几部原创动画,如《疯狂元素城》的票房表现平平,焦虑的蔓延不足为奇。
同时,《头脑特工队》的成功和皮克斯经营状况的疲软让续作团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头脑特工队》的导演、皮克斯首席创意官彼得·道格特并未继续导演系列续作,而是交由凯尔西·曼指导。《头脑特工队2》的编剧达沃·荷尔斯泰因坦言:“给一部像《头脑特工队》这样备受推崇的电影创作一部续集,会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焦虑。这是一部收获了奥斯卡剧本提名的完美电影——也是我个人最喜爱的皮克斯电影。”
编剧想在电影创作中探究的问题庞杂又沉重,达沃对自己所体验到的焦虑的描述很有趣,那是嘴里泛起“一股特别的橙果珍味”,这不禁让人想起“焦焦”那神经质的橙色。“这部续作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要做一部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完美的电影——拿出10亿美元票房的成绩,把皮克斯的观众拉回电影院,让大家有笑有泪,同时在电影演到79分钟的时候,回答一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否需要解答的哲学问题。我6岁的儿子会观看这部电影吗?他会觉得这部电影拍得比《赛车总动员》好吗?一部电影真的可以做到去跟自己(《头脑特工队1》)一较高下吗?”
显然,焦虑成了笼罩着一切的情绪,于是,“焦焦”抓着莱莉头脑总部的控制杆,让一切向前疾驰。
基于“优绩至上”想象出来的“更好的自己”,
损害了完整的人格
当莱莉在集训营里收到了她所崇拜的冰球健将学姐的邀请,与那些高中的“酷女孩”们一同吃晚饭时,莱莉头脑中的“焦焦”与“慕慕”(羡慕情绪)兴奋极了——这是他们的作战大成功,是莱莉成功打入更高级圈层的标志。这时,莱莉的两位初中好友向莱莉打招呼,慕慕翻了个白眼说:这些过去的朋友怎么总是在我眼前晃!我们才不会与她们分享胜利的果实,她们就是嫉妒我们。
这很微妙,与其说“焦焦”和“慕慕”是为了让莱莉在高中时期仍然有朋友而谋划与作战,不如说,在表层的掩饰之下,他们在用“优绩至上”来驱动莱莉。莱莉的头脑中种下了“鄙视链”而不自知,她将过去的自己和好友都打入了被鄙视的低级圈层,而进入高中冰球队的学姐们,是更成功、更高级的圈层,她需要与过去割裂,来成为一个全新的“强者”。这样的“赢家与输家”的思考方式是危险的,而更有害的是,莱莉对于友谊的质朴需求与之混淆在一起,难以区分。
为什么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会伤害自我认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指出:“优绩至上的准则所产生的情感,无论在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中,在道德上都不受欢迎。在成功者中,优绩至上催生了狂妄自大,在失败者中,优绩至上带来了屈辱和怨恨。”而这种区分本身,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这样的思维去争取“友谊”的莱莉,注定无法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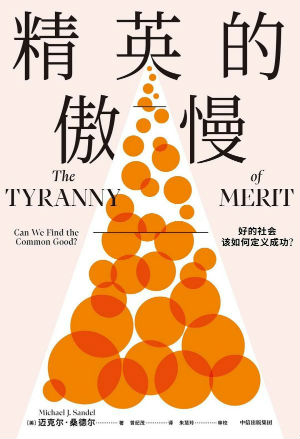
《精英的傲慢》
[美] 迈克尔·桑德尔 | 著
曾纪茂 | 译
漫游者 |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9月
更加讽刺的是,在集训中疏远初中好友、与他们割席并竞争的莱莉忘记了,她能够进入高中集训营的原因正是她与两位好友在冰球场上的配合,是她们之间紧密的协作使她们脱颖而出。但是在焦虑的驱使下,沉迷于优绩至上思维的莱莉早就忘了她的优秀并非仅仅来自她自身这一事实,执着于成为所有人中的“最强者”,期待凭一己之力获得三分,用碾压式的胜利进入高中冰球队。
这种忽视客观因素对自己成就的巨大影响的思维方式,正是迈克尔·桑德尔所指出的精英的傲慢的根源所在——“精英阶层的傲慢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而不记得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那些登上顶峰的人自鸣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报酬,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是咎由自取。”
在这样的傲慢之中,莱莉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某种程度上来自“焦虑”所坚信的一条准则: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控,实现“更好的自我”的承诺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一准则乍一看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是当下人的共识。但是,如果是拔掉了真实自我,将自我摒弃到鄙视链的低端,压抑了人生来的快乐、愤怒、忧伤等基础情绪,那这个“更好的自我”,又从何而来呢?或许只能从“优绩至上”的“卷”中来,形成的是一个核心信念是“我不够好”,一切评判标准基于外界的虚假自我。
事实上,若比较《头脑特工队1》和《头脑特工队2》的整体设计,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体验”与“优绩至上”的不同侧重。在2015年上映的《头脑特工队1》中,无法看到任何优绩至上的痕迹,它讲述11岁的莱莉因为父亲工作变动而搬家,由快乐主导的她强装无所谓,压抑自己的悲伤直到崩溃,离家出走又回家的故事。在莱莉的大脑中,快乐因为拒绝悲伤参与莱莉的情绪,而导致二者意外离开头脑总部,在记忆存储、抽象思维、想象世界等区域冒险。《头脑特工队1》着眼的是在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失去的过程中,快乐的回忆也会带上忧伤的色彩这一事实。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是莱莉儿时幻想出的玩伴“冰棒”,他是一只拉着彩虹小车、哭的时候会流出糖果眼泪的粉色海豚大象。他带来快乐又让人忧伤,他被莱莉遗忘,又一心想着带着莱莉再度“飞向月球”。记忆会消逝,儿时的幻想与快乐也会消逝,当冰棒在堆着黑色记忆球的山谷中对快乐说“替我带她上月球,好吗”时,观众会被这人生中必须承受的失去而难过。
而在《头脑特工队2》中,不论是故事情节还是莱莉脑内世界的设计,都带有强烈的“优绩至上”色彩。莱莉用来枕头大战的想象城堡里,全是被迫画令莱莉焦虑的想象画面的“打工人”。在职业花车巡游中,乐乐也直言不讳地嘲讽了“大法官”之外的文艺类工作。快乐、幻想确实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探险也没有那么重要——在续作中,快乐等基础情绪在头脑总部外的经历比起冒险,更像是逃亡。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院中,那些5、6岁的儿童观众会在暗色调的屏幕面前,感到有些不安和恐惧。而青少年、成年观众看后,会觉得宛若做了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会先面对自己的痛苦,然后再解决,不是吗?《头脑特工队2》在全球斩获了远超预期的票房,目前12.51亿美元的票房使它成为了皮克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并在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排行榜上位列第四。皮克斯管理人员和主创团队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一松了。这个植根于生命体验,创作出《玩具总动员》《飞屋环游记》《汽车总动员》《机器人总动员》《超人总动员》的动画工作室,会在票房的驱使下,向着“优绩至上”的世界继续进发吗?
我们无法预测,也无从苛责,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也都活在“优绩至上”的世界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保住自己的生命体验,区分我们的“恐惧”与“焦虑”——这也正是拨动《头脑特工队2》的信念树所发出的声响。
王入秋/文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