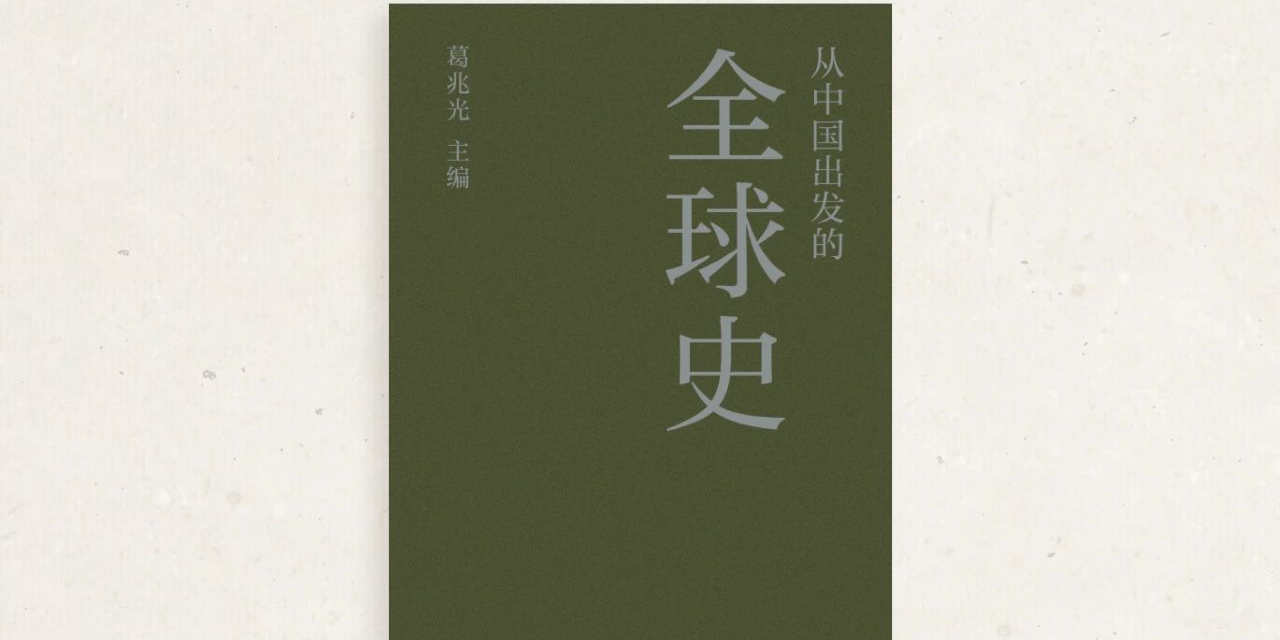
理想国imaginist/文 一直以来,我们关于世界历史的认知与想象,听到过的故事与讲述,大多都按照帝国、国家和族群的线索编织,但其实,在这些角度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更多的视野,那就是全球史。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国别史,“全球史”希望可以带你穿越国界,看到联系着的,互动着的人类文明。
2019年,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兆光、媒体人梁文道共同策划了一档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邀请二十余位不同领域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从中国视角出发,重新讲述文明的故事。五年后,这档节目落成文字,由葛兆光担任主编的三卷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与我们见面。
前不久,葛兆光、梁文道与这本书的二十余位撰稿者相聚在上海静安洲际酒店剧院厅,一起参与了《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新书首发仪式。大家从成书背后的故事出发,谈起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史,也谈起在当下书写与讲述全球史的意义。
当我们说起“全球史”
段志强:我们提起全球史,好像就是在说全球史是无所不包的,大家期待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但实际上,在写作全球史的过程中,恐怕得有非常痛苦的取舍过程。我想请教两位老师,全球史这个提法首先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提出来的,但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实际上,全球史这种史学方法或史学领域本身也成了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要怎么样看待又怎样应对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自己做的事其实就是对这种思潮的一种回应,但大家整体上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葛兆光:我首先要说的是,从欧美兴起的全球史本身就是欧美学者自我反思或者说自我批判的一个努力。我在欧美以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有过一些交流,我感觉到一个非常突出共同特点,他们都在反思自我中心主义。因此,所谓全球史,本身首先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写作。我也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一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告诉他们,从“中国出发”不是指从中国的立场和价值出发,而是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所以我一再强调,再好的全球史家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像上帝一样360度无死角地去看全球,你一定还是有一个你的角度,这个角度不等于立场,也并不是给中国抢份额。
我们能够加入全球史的潮流,最大的一个贡献可能就是我们给他们展示了一个从中国历史往全球历史去看的角度,这就能给他们的全球史做一个补充,而不是在颠覆他们。他们也颠覆不了我们,我们也颠覆不了他们,这不是在颠覆,是互相补充。

梁文道:过去20多年来,我们看到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做志强兄所说的这种对于全球史的回应工作。但做这种回应时,有时候并不一定在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比如说,明确地告诉自己,我现在做全球史了,一般往往是在处理自己的课题时,多了一个新的切入方法和视角。
这次做这件事,我最高兴的一点是发现国内有这么多一流的年轻学者在不同领域里,做自己的课题、做自己的研究时,都已经带上了全球史的视野和眼光。比如说,全球史中,有些很经典的著作,或者我们比较熟悉的著作,很多学者在工作时,并不会很明确地指出这个叫“全球史”,而是把这些当成是他的一种方法。
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去研究山西一个很偏僻的村庄,这个村庄里有存续了几百年的天主教徒,这个村庄的故事能完整颠覆过往中国基督教跟世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研究像西非多哥这类传统意义上算小国家的地方,比如这个国家北部有一个偏僻的农村,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农业上自给自足,但它的整个文化也是在和全球的互动中塑造的。做这些研究时,你不会很明确地意识到我在做全球史,或者你也会有这个意识,但你不需要把这些东西讲明。
我觉得所谓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在做自己的研究之余开始想象,我今天做中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题材,不管是多小的题目,多小的地方,多小的任务,可能都不会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一个传统的、固有的视角和方法中。
段志强:就像道长说的,全球史给我们增加了一种视角,原来看历史的时候是一种样子,但附加了一层新的滤镜或角度之后,看到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状况。实际上,我们总是在不断地重写历史,好像每一个世代都在重新书写所有历史,历史的面貌随着时间向前滚动而不断改变。有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未来是特别肯定的,但是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重新看待历史、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全球史可能也正在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在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时,也许全球史会让我们有一些新的武器。

梁文道:一定是的,但也得看书写历史的我们是谁。全球史当然提供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开启了我们很大的视野,问题是这个要写历史的人,这个“我们”是谁?在座的这么多学者都是写历史、做历史的人,问题是民间或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到处都有人在讲历史故事,就像葛老师也强调过,说历史或者说一个历史故事是每个人的某种天性,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们需要透过历史来说明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乃至刚才您说的,我们为什么能够那么确定未来,也是因为首先我现在能说出历史的一套东西,然后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葛兆光:我一直觉得有两个现象很奇怪,第一个现象是,现在新媒体上,为什么历史节目会这么受欢迎。第二个现象,近十年来,我们都能发现出版界有一个现象,世界史的书被翻译得特别多。这两个现象都让我们觉得要想一想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能够想到这些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为什么世界史这么红,或者为什么我们翻译了这么多,大概是因为中国史不太好讲。第二个原因,改革开放40年,大家也都越来越注意到,理解中国的事情可能还是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上,所以世界史就比较受人欢迎。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实的事不太好讲,但现实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可以讲的,就像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历史学家是诊断病原的医生,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既然可以诊断病原,就也可以让你从历史来联想现实,所以历史节目由此就比较受欢迎。
无论如何,做全球史,它对现实是有用的,至少它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就像梁启超讲的,它是怎样从中国之中国到了亚洲之中国,然后又变成世界之中国。

我们为什么需要自己的“全球史”
段志强:葛老师的话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和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聊起来,我说我正在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样一个写作项目,他马上回应说,对,就是应该做,我们中国这么厉害,早就应该讲讲中国在世界当中的地位。
也许没看过我们书或者没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看到这个题目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两位策划人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纠结,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中国或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在今天世界文化或思想界里,中国学者或来自中国的声音肯定是相对弱势的,其他地方的声音更大,他们的概念和想法更多被人接受。具体到现在的这个环境,又有一些另外的力量,无论是制度性的还是别的原因,也在讲中国有多么重要、多么厉害,我们是不是有点要在两种现状中找自己的道路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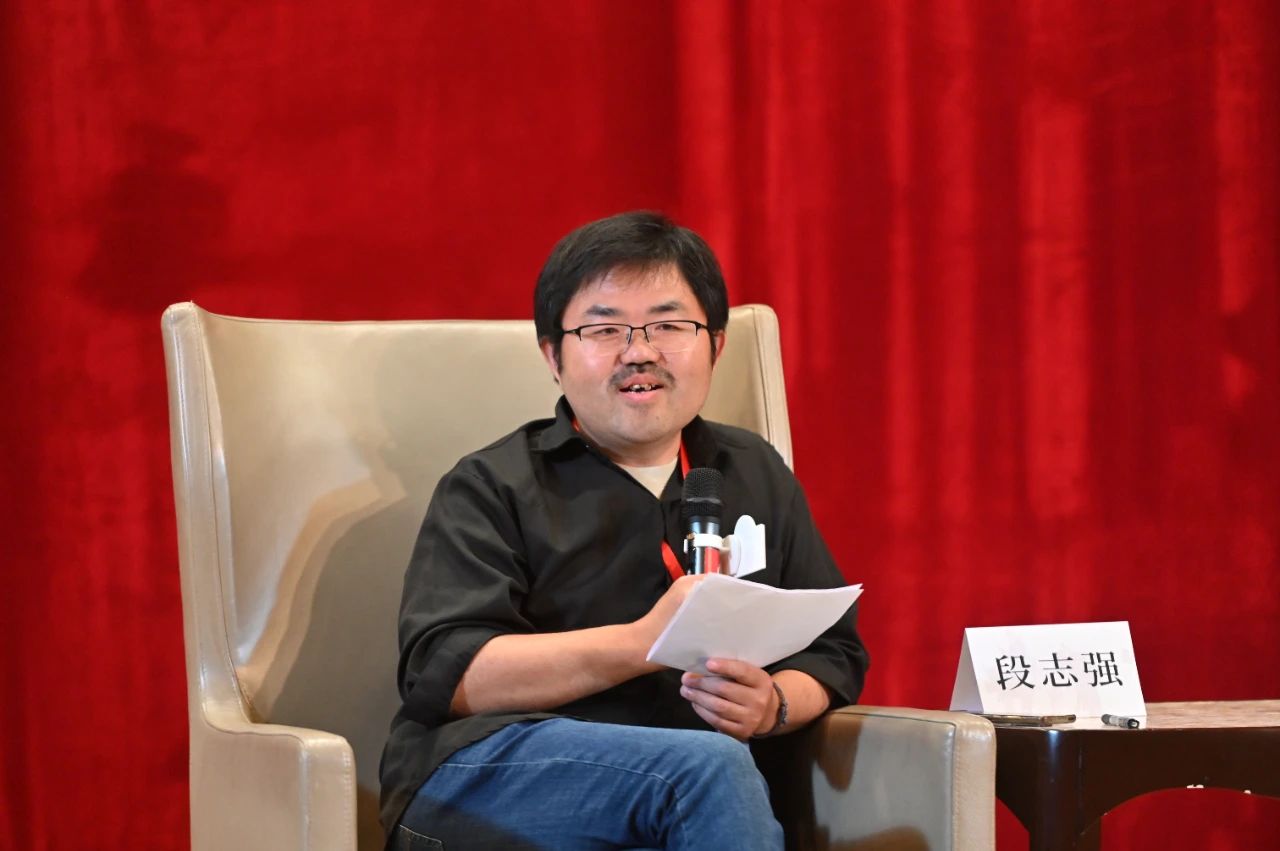
葛兆光:我刚从法国回来,在法国的经历让我感觉外面的学者并不见得对中国不关注,只是我们不太善于用他们也能理解的概念、语言和书写方式向他们传达中国历史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几次对谈、座谈和讨论中,他们反复提问,秦汉以后的帝国到底有哪些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秦汉帝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在文化习俗、文字、制度各个方面统一化,罗马帝国在三世纪以前没有要求各地统一化,他追问这个问题。当我提到秦汉帝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去地方军事化,他们也会问为什么要去地方军事化,罗马帝国也没有去地方军事化。
当他们想到四世纪蛮族入侵,最后导致帝国分崩离析或又重新统一这样的问题上,他们就会觉得你们的经验和案例可能对我们是有用的。所以他们并不是不重视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让他们重视的历史资源。至于现在我们在某一方面说中国很重要,中国很优秀,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从来不认为哪个文化比另一个文化更优秀,因为如果文化有优劣之分,那民族就有优劣之分了,民族有优劣之分,就变成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了。
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用世界通行的语言概念和叙述方式把中国的历史故事讲出去,当然不仅仅是现在常说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概念是没错的,问题在于你要怎么讲。

梁文道:我觉得有趣的是,很多人听到“从中国出发全球史”这个题目就会觉得有一股自豪之情涌上来。我们读历史、读本国史,对本国史产生敬爱,有自豪感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在于你是对什么事情自豪。历史故事的叙述中,常常有几点很值得探讨,比如,直到现在依然很容易看到世界各国都有说过,什么东西是我们国家首创的,土耳其人会给你讲起源于土耳其的伟大成就,中国人也会给你讲起源于中国的伟大成就。
我们这套书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去挑战这种自豪感,而是让我们对什么叫做起源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复杂的理解。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自古以来“本该如此”的事情,如果要讲源头其实相当复杂。这就像河流,今天常常讲黄河源头,你真的到星宿海去看,你会发现那是星星点点,无数小水渠构成了黄河源头。所谓“源头”,来自单一的泉源的概念,由它推演出来的历史故事是我们一般大众很主流的对历史的想象。我们做这套书、做这套节目,它带来的效果可能就是让读者们去发现,这些事情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更复杂。
关于什么叫“固有文明的想象”,书和节目中我也提到过,比如,最近世界各地哪里又发生了冲突,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立场,动辄说这是某种文明的胜利或者某种文明的失败,美国哥大学生被抓了,有人会说西方文明又被破坏了,也有的人会说西方文明快要被拯救了,文明史观中的这种想法也很常见,但我们不是说要完全否定什么,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空隙,一个那么坚硬、完整、有清晰轮廓的故事不一定就是对的,有很多值得挑战的地方。

这套书希望能让一般的读者和听众重新认识,中国从来都是在全球中的,不需要说有全球化的过程。我们以前太常有这种想法了,我们是怎么逐步加入世界、融入世界的?中国是什么时候打开门面向世界的?其实门从来都在那儿,没有关着,我们从来就在全球当中。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当历史陷入舆论的洪流
段志强:谢谢两位老师,刚才葛老师提到,我们应该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或概念向外部传达一些知识或我们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做历史写作或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两年历史写作或历史普及突然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背后应该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
我想起来2021年有次举行活动时,葛老师还在对谈中谈到学者对历史热潮的责任。也许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历史的奇怪的看法,专业学者有责任、有义务把经过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告诉大家。不过,我们刚才聊到的也表明,不见得存在专业研究者和一般社会受众的截然两分,也许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专业研究者,但在另外的问题上我立马就变成了一般受众。大家之前还更愿意看书、看文字,但现在因为新的传播手段,很多时候大家是看短视频来学历史知识的,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做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件事,一方面又面临着这么巨大且奇怪的舆论场,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梁文道:这套书和节目虽然是针对大众读者的,但今天我们在抖音上看到的30秒讲透中国史面对更庞大的大众。我最近发现越来越多人相信西方伪史论,比如我认识的一些人也在和我争论,说胡夫金字塔内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是拿破仑时代建造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直到世界上有比我们更伟大,更辉煌的古老文明。
面对这些,写一套《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有用吗?我想说其实没什么用,因为我们讲的故事比较不简单,而那些故事简单的地方在于,它迎合了今天很多人心里的情感诉求。大众媒体中大部分能火的音频、视频都是一种情绪消费产品,比如说某个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不知哪国的小伙子,来中国隐居学道,真的做起道长来,大家也会很兴奋,我们是有某种情绪点的,这些都是情绪消费,而我们做的东西很明显,没有这么强烈的情绪消费作用,所以很难比得上他们。
我作为一个媒体工作中常年的失败者,我觉得我们对付不了的那些东西,你是要投降的。不过好在他们相信的那套东西总有一天会遇到困难的。当有一天,你面对着越来越多跟你相信的想法相反的事实出现在你眼前时,你还如何维持自己一贯地基于某些虚假事实的信念?也许我们只能期盼这个,但说实话,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葛兆光:对于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区分这些奇谈怪论和严肃学术研究是比较好办的,就是胡适的一句话,拿证据来。有证据的就是合理的猜想和推测,没有证据的就是悬想。但对于公众来说,他如果没有受过一定的历史训练,随着情绪消费,很容易走向相信奇谈怪论。怎么办呢?实话说,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让全民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但这个办法又太理想化了。
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努力地去和风车搏斗,认为自己就要阻止这些说法的流行,别指望,因为你永远打不过这些信息带来的情绪消费能力。我也不觉得悲观,就算90%的人都相信了这些说法,问题是他即使相信了,能用来做什么呢?总不能把这些变成一块石头砸你。

梁文道:我倒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还是觉得这个现象很值得担心。因为情绪消费是个循环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东西,就会助长其他情绪。做学者也可能会遇到麻烦,比如现在有些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可能很容易遇到同学的挑战,那些挑战说不定就是某些奇谈怪论滋养出来的想法,如果你否定他的某些想法,他甚至可能给你扣帽子。将来这种局面会不会出现,我不知道。
刚才葛老师讲的,证据这一点,在公众讨论中也很流行,在我们做公共评论时,讨论事物也会讲证据在哪,但现在比较有趣的是,今天的公众情绪下还包含着对体制内的学术界,对所谓的知识精英的集体不信任。因此,当你质疑证据,并给出你的证据时,挑战在于,对方认为现有的这些证据,无非都是既得利益阶层提出来的,他们背后带有阴谋。
阴谋论是自我证成的,比如我们讲美国,我记得前些年我看到过一个数字,我很关注这个数字,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三四年前,美国国家地理做了一个调查,在美国有接近10%的人仍然相信地平说,另外有接近30%的人,不敢断定地平说的对错。对于地平说的支持者,比如说,你拿出证据给他看,NASA拍出了这个地球是圆的,他会说NASA是一个阴谋机构,伪造了太多东西。所以,阴谋论的东西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攻破,你无法挑战它,想要相信的人永远都会相信下去,直到有天他的阴谋论不能完整地覆盖所有缝隙为止。就像葛老师说的,我们只能期望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平和的、理性的、开放的整体社会公民情绪。


国出发的全球史》撰稿人合影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