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国imaginist/文 电车难题又出现了:一列失控的火车沿着铁轨疾驰,火车前方的铁轨上有五名工人,但是,火车在撞上那五名工人之前会经过一个岔道口,岔道口引向另一条铁轨,在那条铁轨上也有工人,但只有一名。你就在岔道口边,你可以选择可以按下开关,调转火车路线,避开那五名工人,却撞死另一条铁轨上的一名工人。你会按下开关吗?
如果你选择按下开关,觉得一个人的死亡可以换得五个人的获救,由此实现幸福最大化,那请你再设想接下来这个情形:有一个健康的人走进医院的病房,里面有五个人急需各种器官,他们不接受移植必死无疑:一个需要心脏,另一个需要肝脏,还有一个需要肾脏,等等。杀死这个健康的人,将其身体内的器官分给这五个病人,就可以救活他们。你还会牺牲这一个人吗?
同样是牺牲一个人来救五个人,为什么许多人在第一种情形下会选择这么做,第二种情形下就不会了呢?在什么时候牺牲一条生命来拯救更多生命是可以接受的?
这其实是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的思想实验。思想实验能通过一个想象的场景,引出我们的直觉,厘清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并揭示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深层理念。
在《哲学小史》这本书里,奈杰尔·沃伯顿还为我们展示了许多其他有趣的思想实验,更重要的是,他以简洁、诙谐而利落的方式,一下子串起了从苏格拉底到彼得·辛格等52位哲学家的思想,探讨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上帝是否存在、我们如何认识外部世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等关键问题。《哲学小史》试着“拂去哲学神秘的面纱”,引导着我们像哲学家那样思考、争论、论证和质疑,在妙趣横生的阅读中,发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下文节选自《哲学小史》,内容有删节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

有人敲门,门口来了一个受伤的年轻人,身上流着血,显然需要帮助。你带他进屋,为他包扎,让他平静下来,让他觉得他安全,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样做显然是对的,但如果仅仅出于同情而帮他,按照康德的说法,却称不上是一种道德行为。你的同情心与行为是否道德毫不相关,做这件事体现了你的性格,但与对错无关。在康德看来,道德不仅仅在于你做了什么,而且跟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关。正确行事不能单单出于情感:行为决定必须基于理性分析,从而明确责任之所在,与个人感觉无关。
康德认为,情感不属于道德范畴。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情感,基本靠运气。有些人有同情心、同理心,有些人则没有。有的人从不慷慨施予,有的人则乐善好施。但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无论情感如何,都可以选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康德看来,如果帮助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人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就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行为,原因是在相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你可能觉得这么说听上去很奇怪。你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如果出于可怜这个年轻人而出手相助,那么他的行为也很道德,因为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处境时心生怜悯,说明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亚里士多德也会这么认为(见第二章),但在康德看来,如何判断事情是否道德是很清楚的: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感觉而做了某件事,那算不上什么好的举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看到那个年轻人时心生厌恶,但出于责任感仍然施以援手。在康德眼里,这个人明显比因同情而出手相助的人更为道德,因为他提供帮助的行为完全受责任感驱使,而情绪只会推着他往反方向走。
让我们看一下“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故事。好撒玛利亚人帮助了一个躺在路边、需要帮助的人,而其他路人却视而不见。是什么让好撒玛利亚人成为好人的?在康德看来,如果好撒玛利亚人出手相助的动机是自己能因此上天堂,那就根本不属于道德行为,只是把帮助他人当作实现一己私利的手段。如果仅仅出于同情而伸出援手,那么和之前的例子一样,也算不上道德行为。但是,如果好撒玛利亚人认为帮助他人是自己的责任,也是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做的正确之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道德的。

相比康德对情感的论述,他对动机的分析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大多数人的确是通过行为动机,而非行为结果,来评判他人的行为。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人行道上,一个孩子的家长因为急着把孩子从马路上拉回来而不小心撞到你,你会怎么想?再想象另一种情形,还是在人行道上,有人为了好玩儿故意把你撞倒,你又会怎么想?那个孩子的家长并没有伤害你的意图,而那个使坏的人真的就是以撞你为乐。但是,动机良好并不足以使行为有道德,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又有人敲门,你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她面色苍白,神情焦虑,气喘吁吁,说有人在后面追她,那人手里提着刀想要杀她。你让她进门,她跑上楼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门口就是那个要对你朋友图谋不轨的人,他眼神疯狂,问你是否知道你朋友在哪里。她在这里吗?是不是躲在橱柜里?实际情况是她正躲在楼上,但是你撒了谎,说她跑去了公园。你肯定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对吗?把这个可能的凶手支开,也许因此救了朋友一命。你的行为一定是道德的,这难道还能有错?
康德可不这么看。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说谎,哪怕是为了保护朋友不被杀害。撒谎在道德上一定是错的,没有例外,没有借口。原因是,如果你认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撒谎是对的,那么推而广之,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情况而撒谎。回到这个例子,如果你撒谎把凶手引去了公园,而你的朋友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刚好也去了公园,那么你就在实质上帮了凶手,你朋友的死在一定程度上是你的错。

这是康德自己举的例子,足以说明他的观点是多么极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他认为,说实话是我们绝对的责任,或者借用他的话来说,说实话是一种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令式”就是一种命令。与定言令式相对的是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假言令式是“如果你想要x,那么就做y”,例如:“如果你想要不坐牢,那么就不要偷窃。”定言令式则不同,是一种命令,在这个例子中,定言令式就会是“不要偷窃”,直接告知责任是什么。康德认为道德属于定言令式,道德责任是绝对的,无论会有什么后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康德认为,我们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是因为我们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进行反思。如果不能有目的地采取行动,就和机器没什么两样。“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问题几乎总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不是出自本能,而是有原因的。康德将此称之为格律(maxim),是我们行为背后遵循的准则。要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问题,康德认为只有行动背后的格律才是真正重要的。他认为,应该只按照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le)、适用于所有人的格律行事。也就是说,只应该做任何人在面临同样处境时都会做的事情。所以你应该不断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不要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康德认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你不应该利用他人,而应该尊重他人,认同他人的自主性,接受其作为个体有为自己做出合理决定的能力。这种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是现代人权理论的核心,是康德对道德哲学的重大贡献。
用一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想象一下,你经营着一家水果店,对顾客总是礼貌有加,找零分毫不差。你也许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认为这么做会带来更多回头客。如果这是你找零分毫不差的唯一原因,那么这么做就是利用顾客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康德认为,如果让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人,显然是不对的,所以这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但是如果你找零分毫不差的原因是认识到不欺骗他人是自己的责任,那么这就是一种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是基于“不欺骗他人”这一格律,而这一格律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欺骗就是利用他人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可能是道德的行为准则,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欺骗他人,信任就会瓦解,没有人会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话。

再举一个康德用过的例子:想象你彻底破产了。银行不再借钱给你,你没有任何东西可换钱,如果不付房租,马上就会流落街头。你想出的办法是去找朋友借钱,承诺会还钱,即使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这是你最后一根稻草,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付房租。这样可以吗?康德认为,向朋友借钱而不打算归还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理性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能借到钱,在明知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承诺还钱,那实在是荒唐。所以,这也不是一条可普遍化的格律。因此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必须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会怎么样?”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每个人都做出这样的虚假承诺,承诺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如果别人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你这么做也不对,所以你不应该这么做,这是错误的行为。这种基于推理而非情感来判断行为对与错的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总能够产生正确的情绪,并因此做出恰当的行为。在康德看来,感情只会使问题变得含混不清,更难透过表面看清行为是否真的正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更积极的说法:在康德的理论中,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有能力做有道德的事,无论是否具有正确的情绪以驱动其行为。
不做质疑的人

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是一名勤奋的行政官员。从1942年开始,他负责将欧洲的犹太人运送到波兰的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这是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计划处死所有生活在德占区的犹太人。艾希曼并非这项杀戮政策的制定人,但积极参与了铁路系统的组织工作,使这一计划成为可能。要实现希特勒的计划,必须把犹太人从城市里的隔离区驱赶到其他地方,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屠杀。现有的集中营被改造成死亡营,其设施能够每天用毒气杀害数百人,然后火化。由于许多集中营都设在波兰,因此必须组织调动火车,把大批犹太人押上死亡之路。

艾希曼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收发文件、打些重要的电话这样的行政事务,可与此同时,数百万人却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死去。有些人死于伤寒或饥饿,有些人被强迫劳动至死,大多数人死于毒气。在纳粹德国,火车准点运行,艾希曼之流的工作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的高效率让火车像牲口车一样,装满男女老少,投入漫长而痛苦的死亡之旅。通常没有食物,没有水,有时酷热,有时寒冷,许多人在旅途中死去,特别是老人和病人。
艾希曼在这些罪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二战结束后,他却从盟军眼皮底下逃离,辗转抵达阿根廷,在那里秘密生活了几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Mossad)追踪到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将其抓获,给他下了药,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

艾希曼是一个邪恶的野兽、一个享受他人痛苦的虐待狂吗?在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如果不是那样,他怎么可能在大屠杀中扮演这么关键的角色?在那几年中,他的工作就是找到有效的方法将人们送上死亡之路。白天干了那么多坏事晚上还睡得着觉的人,必定是恶魔无疑。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一个移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为《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报道审判艾希曼的过程。面对面接触一个纳粹极权政权的产物,让她非常感兴趣。在那个极权社会里,人们几乎没有思考的空间。她想要了解这个人,亲身感觉他的行为表现,弄明白他怎么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他选择不去过多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虽然其行为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他并不是阿伦特之前所想象的恶棍,而是一个平凡得多但同样危险的人:一个不做思考的人。在纳粹德国,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思想被写入了法律,因此他很容易说服他自己所采取的行为是正确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一个事业成功的机会,而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为艾希曼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阿伦特觉得,当艾希曼辩称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他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这一点很难让人理解,许多对阿伦特持批评意见的人也认为在这一点上,她的判断是错误的。
与某些纳粹分子不同,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其背后的驱动力似乎并不是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因为他不像希特勒那样对犹太人恨之入骨。很多纳粹分子会因为一个犹太人没有致希特勒万岁礼而将其当街打死,但艾希曼不是那样。正是这样一个人,不但接受了纳粹的官方理念,更为恶劣的是,还将数百万人送上了死亡之旅。艾希曼似乎无法接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违法之处,即使在法庭上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时,他似乎仍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在他看来,因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直接杀害任何人,也没有要求任何人为他杀人,所以他的行为没什么不对之处。他从小就被教育要遵守法律,接受服从命令的训练,他周围的人也都像他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只是接受命令行事,无须对日常工作的后果负责。
艾希曼不需要看见人们是如何被塞进牲口车的,也不需要看见死亡集中营的情形,所以他没有去看。他告诉法庭,他无法成为医生,因为害怕看到血。然而,他的双手却仍沾满了鲜血。他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不仅遏制了他以思辨的眼光审视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让他无视自己的行为对活生生的人带来的灾难,他好像根本无法想象别人的感受。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要么他确实这么想,要么就是他觉得为自己辩护的最好办法是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依照法律行事。如果是后者的话,阿伦特就是被他骗了。
阿伦特用“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来形容她对艾希曼观察的结果。我们说某种东西是平庸的,就是指它是普通的、无聊的、无创新的。艾希曼的邪恶是平庸的,因为这是一名官僚、一名办公室经理所做出的邪恶,而非魔鬼所实施的邪恶。在阿伦特面前,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让纳粹的理念贯彻到了自己一切所作所为之中。

阿伦特的哲学灵感来自她周围发生的事情。她不是那种一辈子坐在扶手椅上思考纯粹抽象概念的哲学家,也不会无休止地争论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她的哲学与发生不久的事件以及生活经历有关。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基于她对受审期间艾希曼的观察,以及对他使用的语言和给出的辩解所做的分析。通过观察,她分析了极权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罪恶,及其这些罪恶如何造就那些对极权主义不做抵抗的人的思维方式。
艾希曼跟当时许多纳粹分子一样,没有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没有勇气质疑传达给他的规则,只是一味寻找最好的方式去遵守这些规则。他没有能力设想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阿伦特形容他肤浅、不会思考,当然这也可能是艾希曼为自己脱身而做的表演。如果他是一个恶魔,那确实很可怕,但至少怪物是稀有的,通常很容易一眼看出来。也许,艾希曼看起来很正常这一点更令人恐惧。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由于没有质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参与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邪恶的行为。如果他不是生活在纳粹德国,也许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邪恶的人。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这并不能消除他的罪恶,因为他对不道德的命令言听计从。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服从纳粹的命令就等同于支持“最终解决方案”。艾希曼不仅没有质疑收到的命令,反而具体执行了这些命令,从而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然而在艾希曼自己看来,他不过是编制了一些火车时刻表而已。在审判中,他甚至声称自己是按照康德的道德责任理论行事,仿佛他遵命行事是正确的。他完全没有理解康德认为尊重他人、给人尊严是道德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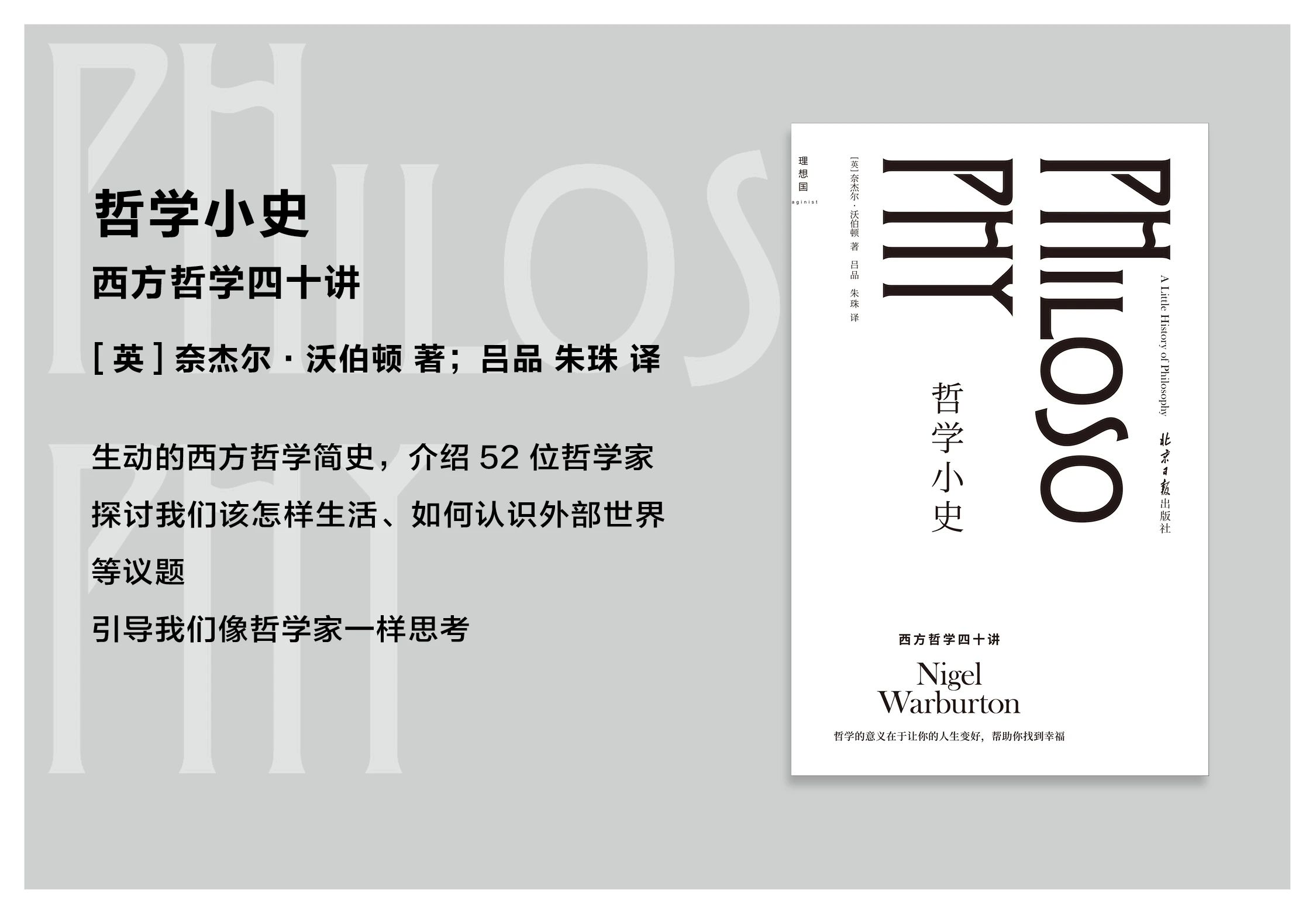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