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旭宇/文 我把东起伦敦桥西至黑僧桥,北起硕迪奇南至泰晤士河南岸一里的方寸之地称为诗人的城。1576年之后的60多年间,英格兰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创造了英国戏剧的黄金时期,之后无此盛况。
对于这里和这时,我都试图通过文字和探访与之联系,复刻当时的样子,因此我对于关于莎士比亚所在时代的社会和城市的书籍都难以抗拒。
航班延误了四个小时,恰好给我一段完整的时间阅读《莎士比亚与早期英国物质文化研究》。这是一本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书籍。我是从书末倒着翻阅时发现了该书的几处美德。
这本书的参考文献长达20页,可见作者胡鹏的勤奋和严谨。其中只有两页是中文文献名录。这大概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学者无可奈何的地方。在过去120年中,每年关于莎士比亚的出版物超过4000种,绝大多数是英文出版物。由于这本书的旨趣,参考书目远远不止莎学一科。
该书的附录在我看来是最有趣的部分。第一个附录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创作年表及材料来源,这个部分对于普通读者过于枯燥,对于专业读者却非常有用,可能也不乏争议。莎士比亚多数作品的创作时间没有出版实录,除了两部叙事诗以及他死后出版的戏剧全集有明确出版年份,其它作品都需要通过书业公会的登记记录,或演出记录,或观众日记,或宫廷账本来推测大致的创作时间,而创作时间和上演时间也不一定同时。因此,莎士比亚的创作年表本身就是一项专门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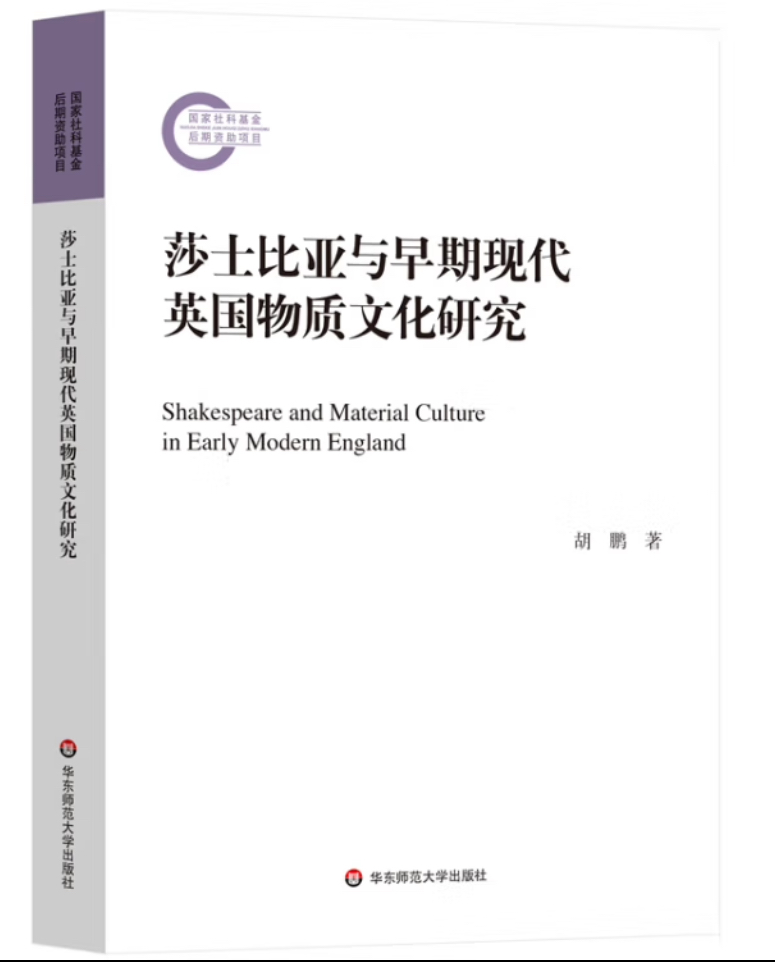
莎士比亚基本没有原创戏剧情节。因此,研究他戏剧的素材来源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延绵了200年。胡鹏把创作年表和材料来源放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一览的检索,对于专业读者提供了一览的帮助。但是年表本身也是研究推导的结果,各家其实还有不同见解,如果对每部作品的年表依据再拉出一张参考书目清单,估计不会太短。
附录二是莎士比亚年表及大事记给我带来强烈的阅读快感。即便我读过大概十种诗人传记,我依然在这30多页的大事记中发现很多未知和惊喜。有记录的莎士比亚人生事件只能写满两页,但是从18世纪以来,关于这个人的传记层出不穷。如果不把传主置于时代和社会叙事之中,通过考据、联系和推演,辅以自以为是的假设或想象,可能无法完成一本传记。这个附录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把他和当时的英格兰在社会、政治、外交方面的事件放在一个页面上。如果这个年表和大事记说明了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莎士比亚非常幸运,他出生在恰当时候,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似乎一切外部因素都在为他的天才服务。当然,最终这是英格兰和世界的幸运。
以下是我摘抄的部分年表和大事记,括号内是我的补充。
——1579年,莎士比亚15岁
斯特兰奇勋爵剧团和埃塞克斯伯爵剧团到斯特拉福德演出。(斯特拉福德是个只有2000人左右的市场小镇,莎士比亚很有可能观看了演出,此时启发了他的天赋)。托马斯·诺斯爵士翻译的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列传》出版。(这个事件有深远的影响,十多年后莎士比亚根据这本书提供的素材创作了伟大的罗马戏剧,包括《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1583年,莎士比亚19岁
2月,英国女王派约翰•纽伯雷前往中国,携有致明朝万历皇帝的信,要求开展两国间贸易,互通有无,但使者被葡萄牙人拦截拘留,未能完成使命。(如果女王特使到达了万历朝廷,世界历史会变得怎样?中国是否会出现在他的笔下?)
5月26日,长女受洗礼,被命名为苏姗娜。(因为他18岁时搞大了邻村比他年长八岁的姑娘的肚子。)
——1587年,莎士比亚23岁
同年,克里斯多弗•马洛写成无韵诗悲剧《帖木儿大帝》上篇。托马斯•基德写成《西班牙悲剧》。霍林谢德的《英国编年史》增订第二版出版。(马洛的这部悲剧震撼了整个伦敦舞台,开启了英语无韵诗戏剧的伟大时代,如果莎士比亚不曾前往伦敦,马洛就会享有英国戏剧黄金时代的头把交椅。据考,莎士比亚后来补写了《西班牙悲剧》的结尾部分。直到19世纪,很多英国人是通过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获得了历史教育,他的十部英格兰历史剧的来源主要就是霍林谢德的《英国编年史》。)
——1588年,莎士比亚24岁
英国第一家造纸厂建成。(可见该国的落后,而他的戏剧全集第一对开本的印纸是从法国进口的。)
——1594年,莎士比亚30岁
《威尼斯商人》在玫瑰剧场上演。西班牙人把红薯传入菲律宾,30年后,红薯进入中国境内。(我每周早餐的食物就这样和莎士比亚发生联系,红薯进入中国时,第一对开本出版销售。)
——1596年,莎士比亚32岁
伊丽莎白女王又派特使本杰明•伍德同伦敦商人乘3艘大船前往中国国,寻求通商,但一艘在好望角附近沉没,另两艘在布通岛附近沉没。(如果没有沉没,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将有何不同?)
——1598年,莎士比亚34岁
汤显祖写成《牡丹亭》。(中国学者把二人放在一起,做足了文章。他们两个死于同一年)
——1601年,莎士比亚37岁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利玛窦9年后死于北京,在他死后6年莎士比亚也去世了,他们算是同时代的人。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天主教、拉丁语、几何学、地图。莎士比亚戏剧直到19世纪末期才在上海英租界上演,中译本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这个之间,中西历史呈现出大分流的走势。)
——1605年,莎士比亚41岁
米古尔·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柯德》。(他们两个死于同一年同一天。)
——1607年,莎士比亚43岁
托马斯•史密斯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建立了第一个英国北美殖民地。(如今最大的莎士比亚图书馆就在美国,藏有最多的第一对开本。实际上,美国英语的拼写保留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拼写习惯,例如honor, color。)
莎士比亚研究早已成为一个产业,除了文本、语言和版本考据等方面,因其戏剧包罗万象,从宗教到种族,从地理到政治,研究细分无穷无尽,也形成了众多流派,不胜枚举。恰如作者所言,莎士比亚全集“所透露出的有关宗教、政治、文化、医学、科技、自名诸多面相,以及有关人物和群体身份(阶级、性别、国族等)的讨论,仍旧是个未尽的话题”。
胡鹏开宗明义,表示《莎士比亚与早期现代英国物质文化研究》是基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物质文化研究思路对莎士比亚作品中反映的16世纪社会物质文化的研究。本书的章节结构设计对应的也是布罗代尔的研究框架。
本书涉及莎士比亚全集中的21部戏剧和一部叙事长诗。但是这本书和戏剧和诗歌本身却没有太多关系,没有通读过全集的读者恐怕难以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形成判断和认识。当然,这本来不是作者的意图。胡鹏写道,他试图“体现出莎士比亚文本之外的物所包含的社会、政治、文化意义,重申对莎士比亚进行物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认为本书已经证明了这个可行性,但必要性则限于专业研究者。胡鹏表示,“通过物质文化视角分析莎士比亚,我们不仅能够以此明晰其作品的内涵,也能窥视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更能瞥见剧作家利用物的意义进行的或接受、拥护或反抗的种种态度”。对此,我不敢认可本书是否实现了瞥见剧作家态度的目的。莎士比亚的天才不同于其他剧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从不代入,人们在其作品中极少能辨别他的立场,例如宗教上他到底是偏向天主教还是新教,这种被济慈描述为“负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让莎士比亚本人完全消失在作品之中。
因此,需要明确的是,本书主旨是物质文化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文本上的物质和社会样本。然而,如果纯粹研究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物质文化,其他剧作家也提供了这个样本。那么,到底这个到底是研究莎士比亚还是物质文化,戏剧作品本身到底在其中是什么?我在阅读中经常会迷失在这个问题之中。
例如,第三章谈论的是《李尔王》中服饰的文化意义,我感到疑惑的是这里到底在谈服装还是戏剧?第四章用大量笔墨从偷窥视角探究克莉奥佩特拉贴身女官和她们的性欲,不仅远离了戏剧,也远离了关于物的文化的探讨。这章对罗马帝国政治的描述则更加偏离,而且作者试图通过戏剧中克莉奥佩特拉的任性和伎俩来映射伊丽莎白女王的为人和处事,并且揣度女王的性生活,这种带有英国小报特色的分析和写作,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和阅读趣味。
本书各个章节中,我的阅读兴致最高的是探讨福斯塔夫和酒,这个章节可以当作Arden版《亨利四世上篇》注解的延伸阅读。我的总体感观是,社会学科入侵了诗歌和戏剧,结果后者失去了本来的样子。
To be or not to be,这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句子,每个词都如此简单,组成的句子如此复杂。莎士比亚所有的历史剧和悲剧都以死亡为结局,喜剧(包括传奇剧)中虽然有死亡,但不多见。《莎士比亚笔下的N种死亡方式:蛇咬、剑刺和心碎》 (Death By Shakespeare: Snakebites, Stabbings and Broken Hearts) 的附录对各部戏剧中的死亡和死亡方式做了一个全面记录。
死亡不仅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常见的主题,也是他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话题。他出生前,两个姐姐都夭折了;他出生那年小镇上的一半新生儿未能活下来;他唯一的儿子在11岁时夭折了;他三个弟弟都先他死去;伦敦隔三岔五发生瘟疫,剧院经常被迫关门。在都铎时代,生命短暂,英格兰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8岁。“死跟活一样,都很平常”(《爱德华三世》)。重要的是,莎士比亚活到了52岁。他非常幸运,当然这是英格兰和世界的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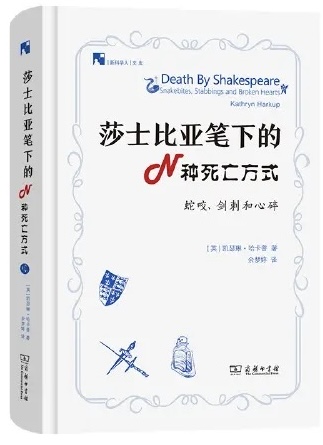
但是凯瑟琳•哈卡普(Kathryn Harkup)写作这本书并不旨在社会和文化研究,而是对于戏剧中死亡主题和戏剧本身的兴趣。或者说,她从死亡的角度带着读者重温了全集。这也让阅读非常有趣和轻松,哈卡普在回顾《亨利五世》中被执行绞刑的巴道夫时,从医学角度介绍了绞刑致死的过程和病理学,但是她不会走得太远,她的笔触总是在戏剧情节、人物和死亡方式和病理学之间保持合理的距离关系,不会过度解读,也不会让病理学喧宾夺主。
胡鹏摘编的年表和大事记附录最后一行是:1623年,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对开本出版。我对第一对开本也有一种迷恋,去年在《经济观察报》版写了一篇长文,纪念第一对开本400周年。假期还专程跑到伦敦目睹原版的样子。实际上,关于第一对开本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从其印刷、排版工分析、与四开本的文本关系,现存各本书所有权的沿革历史和每一本的装订特点和阅读痕迹, 都在过去100年被研究透彻。第一对开本的版本和制书的技术以及成为经典的过程等方面,Emma Smith,Anthony James West,以及 Eric Rasmussen在过去二十前做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因此,Chris Laoutaris必须在Shakespeare’s Book: The Intertwined Lives Behind The First Folio这本新书中另辟蹊径,找到新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副题所示,他的笔墨集中在莎士比亚剧团朋友和伦敦书商的社会关系之中。
第一对开本出版时,莎士比亚已经在家乡三一教堂的坟墓躺了七年。莎士比亚生前可能对于戏剧的出版并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出版戏剧对作者无利可图。但这不能说明,他对于出版作品完全不在乎。他的两部长篇叙事诗就是经过他自己的审阅,通过在伦敦做印刷生意的老乡Richard Fields出版的,以博得贵族赞助人的欢心和酬金。

据考,第一对开本的出版很可能是一次伦敦出版界和国王剧团(The King’s Men)之间合作的辛迪加(syndicate)。当时国王剧团只拥有莎士比亚全集的18个剧本,其它18个剧本被不同书商所拥有。出版这个全集是一次巨大的商业冒险,因此辛迪加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模式。
我从这本书中读到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这些书商和印刷商都在一个街区和一条街道上,彼此商铺相邻。这个地方就是在紧靠圣保罗大教堂北侧的街道,这里是伦敦出版和售书集中地。拥有莎士比亚四开本出版权益的人都是街坊邻居。这给组成第一对开本出版投资集团提供了交通和社会关系的巨大便利。
就如之前的传记,在非常有限的记录和历史材料条件下, 任何关于莎士比亚及其社会时代的写作需要依赖作者的关联能力和推理。Laoutaris在本书中对莎士比亚的社会关系的关联和推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把大量笔墨用在詹姆斯一世朝廷和西班牙的外交政治关系中,试图建立第一对开本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关系。至少,在我看来是很牵强的,而且对于了解该书的出版并没有太多意义。虽然莎士比亚剧团此时叫做国王剧团,演员在名义上都是国王的奴仆,但是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把这本英语历史上最重要的书致献给国王。当然,国王此时并不知道他当政的这十几年,英格兰出版了英语历史最重要的两本书:钦定圣经和第一对开本。
这也是莎士比亚时代最重要的物质。
-finis-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