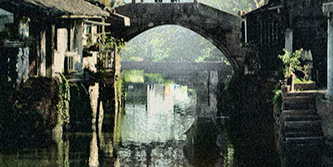
《乘船而去》是由新人导演陈小雨自编自导的一部家庭题材影片,陈小雨也凭借该片斩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编剧”荣誉。电影以疾病叙事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江南水乡的普通家庭如何从离散到聚合,最终被永远怀念的故事,试图探讨生死、疾痛与爱这三个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议题。
疾病症状的爱之显像
托马斯·曼在小说《魔山》中,借人物之口道出让人一时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认同的话,“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地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不是疾病带来了爱,而是疾病放大了爱,让隐匿于繁杂俗事后的爱显出其本身的相貌。
近年来,许多家庭题材电影以“疾病叙事”为切口进行情感的描绘。这或许是因为不同于社会空间的流动性,家庭空间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的构成主要是由其先天的非利益性和亲缘属性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这种空间下的叙事也就显得更加具有可靠性和通约性。“疾病叙事”之所以多在家庭题材电影中被运用的原因,或许是人类在短暂的生命周期之中,初始段落便是从家庭这个空间场域展开,人在家庭中第一次感受到爱,并形成初始的生命印象,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疾病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对于家庭来说,在经历疾病的冲击之后,或多或少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亲子关系成为家庭中的重要感情要素和连接家庭成员的重要纽带,这种亲子关系被电影作品反复描摹。如《小小的愿望》《再见吧!少年》《妈妈的神奇小子》中父母对于患病孩子的不抛弃不放弃,以及对于孩子梦想的全力支持和尽力实现;同样,孩子对父母也有赡养义务,譬如《关于我妈的一切》中季佩珍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婆婆的悉心呵护,电影《当男人恋爱时》中浩婷悉心照料患病在床的父亲并替父亲偿还债务。父母的抚养义务、子女的赡养义务等传统美德不仅是法理规定,也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形成的具有社会普适性的通约准则。毋庸讳言,作为家庭成员,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不断受到父母的关心和照料,并在耳濡目染的教化中被家庭伦理所询唤,进而成为家庭的主体,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百善孝为先”。
在《乘船而去》中,无论是姐姐念真还是弟弟念清,他们无疑都是孝顺的,只不过他们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份埋在心底的爱。姐姐希望可以用国外尚在实验阶段的药物去延续母亲的生命,她诘问弟弟“放下和放弃有什么区别”;弟弟则无法接受明知生命垂危却还要让母亲饱受疾病与治疗的折磨的事实,选择带妈妈享受生命最后的时光。姐弟俩一个希望握紧,一个希望放下,但这都是其自我对母亲的一种偏离主体的爱,是疾病的发生让他们意识到那久久缺席的爱。
其实,正如囡囡苏灿所言,“出了问题光靠医学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爱。在阴冷、空荡的病房里,念真表现出绝望无奈的神情,陷入了沉思。最终,她理解了什么是爱,爱是遵从母亲那并不过分的喜好,这或许是给弥留之际的母亲最大的爱。治疗还在继续,不过空间场域从医院转移到了老屋,那是母亲周瑾的家,也是苏家二姐弟的家。在这里,蒙尘的往事一件件浮现,那些久违的名字和面孔也都轮番造访这幢旧宅,他们的“归来”似乎是在思量如何去接受这场即将到来的“离去”。
归去来兮,何处是吾乡?
东晋陶渊明有辞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为何不再归家呢?目前看来,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前置疑问:何处是吾乡?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个人们成长起来的“家”逐渐变成了“老家”“故乡”。姐姐念真每个月都会从上海回到乡下看望母亲,但她更像个匆匆过客;弟弟念真常年漂泊在外,这或许是导游这份工作性质使然,但更像是他对于“家”的逃避。在母亲患病之前,他们从未真正回过家,他们不像母亲“只有这个家”。但这次回“老家”,他们仿佛又复归于“家”中,不再是一个漂泊的游子。念真知晓了旧日闺蜜一年前的死讯,念清也读起一封来自旧日父亲写给妈妈的信。往事迅速汇聚成塔,故园因母亲的病被唤醒,也与他们一家四口(包括父亲的遗照)一起被定格在了全家福相片里。
《乘船而去》中的家是由船连接起来的。父亲是个木工,喜欢讲述那些造船的故事,也会每年按时给船刷上价格日趋上浮的桐油;母亲乘坐这艘小船嫁过来,如今儿女们也划着这一叶小舟游弋在江南故乡;念真在母亲的病榻前吟唱起旧日歌谣,“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轻轻地摇船,摇啊摇啊摇。”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家,也象征了他们的人生处境,从离家到还家,再到最后永远的怀家。“家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很远的地方,但你要找到你的家”,外婆周瑾对阿涛说的略显哲思的话语,何尝不是对“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现代诠释。
母亲其实什么事情都知道,她看出来女儿和女婿的分屋而居;担心女儿“本事大的人弄到最后一场空”;也会生气地说“生毛病好,不生毛病你们回来吗?”;她甚至无需儿女,就可以领会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安排自己的葬礼,交代后事。嫌隙、隔阂、不理解与逃避都化为家人的相守相伴,最终随着生命的倒计时而化为过去的记忆。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影片《乘船而去》在江南水乡的田园风光中,用日常生活影像风格的镜头语言,谱写了一首关于生死、疾痛与爱的诗篇。它以一场葬礼开始,以外婆周瑾的葬礼作结,成为导演对于死亡的注解。思想家米歇尔·德·蒙田在《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如是说,“走在摆脱一切苦难的旅程上难过起来,这是何等的愚蠢!一切事物随我们诞生而诞生,同样,一切事物随我们死亡而死亡。为一百年后我们不会活着的一切哭泣,犹如为一百年前我们不曾活过的一切哭泣,都是一样傻。”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像哲学家一样坦然接受死亡,并“向死而在”,但或许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去爱、去思考以怎样一种方式告别所爱之人。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马恩扉页(系西南大学美学博士研究生)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