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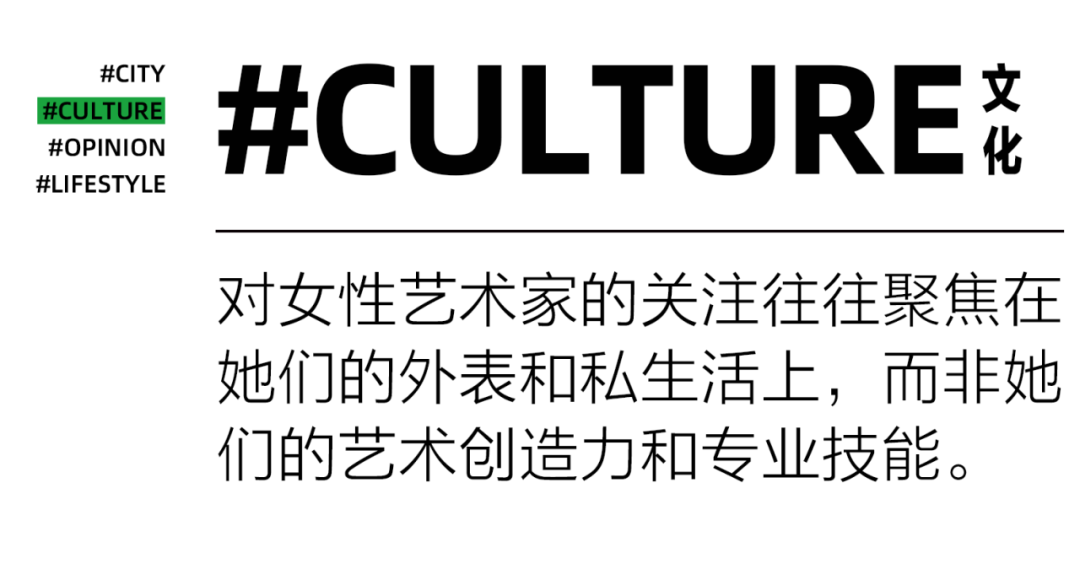
新生活方式/文 近期,美泰公司推出的新版职业芭比——艺术治疗师芭比,引发了人们对于广义上的女性艺术从业者形象以及她们在社会中角色认知的讨论。与此同时,该形象似乎与电影《芭比》中对芭比母公司美泰的批判性描绘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电影中被视为父权制的象征。
艺术治疗师芭比的外表朴实无华——穿着波点上衣和牛仔裤,佩戴粉色框的眼镜,与2008年推出的艺术家芭比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后者一头波浪金发、上扬眼线、红唇,以及紧身黑色半裙和渔网袜的装扮,若非包装上明确声明了她的职业身份,说成是玛丽莲·梦露的复刻版也能让人深信不疑。
这种设计上的转变不仅反映了美泰公司对当代女性职业形象的新解读,也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议题:在艺术的广阔世界中,在光线明亮的画廊与尘封的工作室深处,女性的声音时常在历史的叙述中被边缘化,甚至引发大众对女性艺术家的刻板印象。正如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其著作《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中所提出的,女性在艺术界的缺乏可见性并非才华所致,而是源于系统性的教育和社会障碍。在这由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女性从业者常以边缘人的形象出现,她们的作品往往被归于情感表达,而非技术和创新的展示。
长久以来,女性艺术家往往被束缚于社会对性别的传统期待之中,她们的作品和贡献被频繁地忽略或贬低。更多的关注往往聚焦在她们的外表和私生活上,而非她们的艺术创造力和专业技能。这种性别偏见不仅限制了女性艺术家个人的职业发展,也挑战着艺术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策展人祝羽捷正在为了扭转这种现象而努力。2024年春天,她策划了“柏拉图的阶梯”女性艺术家群展和艺术家徐今今在上海昊美术馆的展览“叩击”。在她看来,她的工作不仅是展示艺术作品,更是搭建一个关于性别、创造力和权力的对话平台。她与这些女性艺术家紧密合作,跨越了纯粹的职业关系,建立起一种深刻的共鸣和理解。从艺术的维度延伸开来,她们共同探索女性身份、表达和抵抗的多重方式,并试图通往某个全新的、更为明亮的目的地。


《新周刊》: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有意识地为女性艺术家做展览?
祝羽捷:大概在2015、2016年,我看了很多展览,学习了大量与艺术相关的内容,当时就对艺术世界里的女性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兴趣。因为我发现,原来贡布里希在写第1版和第 15 版的时候竟然都没有女艺术家。后来我又看到了艺术史学家凯蒂·赫塞尔(Katy Hessel)写的《没有男人的艺术故事》——她竟然写了一本全部都是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史,我才发现原来艺术史的书写是一个多么主观的事情。谁能进入艺术史?谁能成为正典?那个标准到底是谁制定的?了解得越多,我产生的怀疑就越多。
《新周刊》:一个艺术家最初是以什么特质引起你的注意的?性别身份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
祝羽捷:虽然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艺术家吸引我一定首先是他们的作品足够好,无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创作的理念,背后的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解读,去呈现自己的观念。如果只是一个观念也不行,还要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当然,不一定要是漂亮的,但要经得住考量。
但是,当你看的作品足够多的时候,就会天然地被一些作品吸引。然后再一看,果然就是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这个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因为我自己的生理性别是女性,我与女性创作者更有共鸣。
《新周刊》:你认为一个艺术作品应该有性别属性吗?
祝羽捷:在欣赏一个艺术作品时,我相信更多的人还是首先被它的艺术价值打动。但艺术家做作品一定是从自身的生命体验里面提取那些精华的部分,因为彼此身份的不同,哪怕采用同一种媒介,运用同一种意象,最终的作品也会千差万别。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性别带来的经验,但是不能只强调性别,那就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倾向的作品了。
《新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类似于光州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大型项目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策展人和女性艺术家的身影。以一个“当局者”的眼光来看,女性从业者在艺术领域里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祝羽捷:现在整个行业好像都在有意识地为女性创作者提供机会,特别是你看今年 3 月份,好多和女性有关的作品都有了展示的机会,出现了很多女性艺术家的群展。当然也有人会说太多了,会有些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颂艺术中心的群展“柏拉图的阶梯”开幕的时候,有一位艺术家跟我说,其实很多女性艺术家只有在每年 3 月份的时候才有机会做展览,也就是说在“需要”她们的时候,她们才能出现。

《新周刊》: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女性艺术从业者,无论是艺术家、策展人或是批评家,她们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她们过去都在哪里“神隐”呢?
祝羽捷:可能都是在各自的场域里磨练。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优秀的人自然能“好风凭借力”。
《新周刊》:年轻一代的女性艺术家似乎已经不像她们的前辈们那样,善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了。
祝羽捷:的确,她们拥有了更多样的表达方式。艺术创作本身的多元化和丰富化也为新一代的女性艺术家提供了助力。从前人们以为雕塑就是和石材打交道,那时女性学雕塑是很难的。可是“柏拉图的阶梯”其中一位参展艺术家张移北曾经跟我说过,她在英国留学的时候,雕塑系整个班上几乎都是女性。

随着艺术的多元价值观的发展,艺术创作突破了过去固有的那种媒介的束缚。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处境会越来越好。况且在这个时代,身体与权力已经不再是她们要讨论的中心话题了。可能她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自由了,也非常有主权意识,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溢出这个被前辈们一遍遍探索过的范畴,去关注其他内容。
《新周刊》:为什么我们现在如此热衷于强调性别?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女性是否需要强化身份把自己区别开来?
祝羽捷:我认为不需要过分强调,当然也没必要去回避。这是自然赋予的天性,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包含在内,或者我们所做的抗争也都与它相关。做自己最感兴趣的,最能打动自己的,让自己能够心安,并且认为正在做的事情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就可以了。没有一种所谓的标准,也不需要强加给别人一种标准,因为“告诉别人该不该做”这本身就是父权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所谓的女性主义就是为每一个女性赋权,给予她权利。那她就有权利去寻找,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新周刊》: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先锋的领域,往往是最先触及乃至引领时代思潮变化的。越来越多女性艺术家开始关注到更广阔范围内的人群,特别是女性、儿童这样的弱势群体。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祝羽捷: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女性跟男性相比,都有更细腻的情感,也更感性,能关注到细枝末节,这是生理性别决定的。我发现很多女性艺术家会关注到艺术与社会学交叉的领域内,给人感觉好像女性特别容易对社会学这种人文关怀感兴趣,愿意对其倾注自己的情感。而男性艺术家更侧重于作品背后的学术性。
艺术家胡尹萍将她母亲和那些小镇阿姨们织的毛线小玩意儿搬进美术馆,除了艺术创作以外,也推动了当代艺术这个小圈子与社会产生连接。包括在“叩击”这个展览中,徐今今将镜头对准了世界各地经常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以一种诗性方式巧妙地展示了女性身体的部分影像,其中每个女性的肢体通过半透明的布料投射于另一个女性的肢体上,从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叠加效果。艺术家选择不把这些边缘女性的样貌展现出来,因此少了一丝居高临下的观察、帮扶的意味,而是真正尝试去理解。
《新周刊》:展览“叩击”中关于“女书”的概念很有趣,作为一种流传于少数民族女性之间的文字,男性不使用也不理解。这个概念相对于今天的情形像是一种隐喻,某些知识、经验、情感或文化实践仍然是某个特定群体的专有财产,其他群体难以完全理解或接纳。能否分享一下你在筹备展览“叩击”的过程中的思考?你如何看待性别与知识、经验等元素的隔离这样的现象?
祝羽捷:从符号学视角,“女书”不仅是一种文字系统,还是承载特定群体经验、知识和价值观的文化与社会实践符号。它超越文字本身的意义,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内心与外界的纽带。它在申请“非遗”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的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在书写完之后就要把它烧毁。没有历史记载,它就无法被证明。
“女书”挑战的是传统符号权威,是女性争取话语权和自我表达的象征。它反映了身份、性别和权力关系,是一种文化实践,映射社会中的性别分工和女性地位。我们希望通过“叩击”项目内的三部曲——“她诗/她事/她史”,打造一个由女性集体协力构筑的诗性历史和声音共鸣之家,一个语言能够显现和被理解的场域。
而即便到了今天,身份和经验带来的壁垒仍然无处不在。女性从小受到的教育与男性截然不同,然而我们也可以看武侠片并且感受那种快意恩仇,可是男性如果过分沾染了女性气质就不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人人都在被规训,无论男女。
作者:Ariana
排版:张心睿
运营:李靖越
监制:罗 屿
编辑:宋 爽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