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林七贤是历史上相当特别的一群人,学者汤一介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正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魏晋风度,是以礼法教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中的异类。
然而,他们的洒脱起于无奈,汤一介说,他们“生不逢时”,所以借酒消愁,转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从看似消极中,另辟蹊径,开创出一种风骨,这大概就是七贤的独到之处。
下文摘选自《汤一介 乐黛云:给大家的国文课》,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魏晋风度”到底是什么?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这大概说的就是“魏晋风度”。
而“七贤风度”应是“魏晋风度”的集中体现。“七贤风度”既表现在他们的性情、气质、才华、格调等内在的精神面貌上,也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等外在风貌上。“七贤”的“七贤风度”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这种“风度”只能由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造成,也只能为“七贤”的特质性情、人格所造成。这种“风度”可以说最主要就表现在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上。
“越名教而任自然”一语见于嵇康《释私论》中。嵇康、阮籍反对当时的所谓“名教”,所谓“名教”是“名分教化”的意思,指维护当时皇权统治“三纲六纪”的等级名分,也就是说主要是维护自汉以来皇权统治的“礼教”。至东汉“礼教”已经为世人识破,当时有歌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所谓“任自然”从“竹林七贤”的言谈举止看,是指“任凭自然本性”或说“任凭其心性的自然情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内在的情感,而不受虚伪礼教的束缚。
曹魏政权相对汉末,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能阻止当时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司马氏作为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代表,其政权所依靠的集团势力一开始就十分腐败,当时就有人说这个集团极为凶残、险毒、奢侈、荒淫,说他们所影响的风气“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奢侈浪费腐化的风气,对社会来说比天灾还严重),可是他们却以崇尚“名教”相标榜。
在嵇康、阮籍看来,当时的社会中“名教”已成为诛杀异己、追名逐利的工具,成了“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那些所谓崇尚“名教”的士人“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外表道貌岸然,内里藏着卑鄙的感情,欲望无止境,而以欺诈伪装来追求名誉)。为反对这种虚伪的“名教”,《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些“七贤”的“恣情任性”,显露自己内在的真实感情、任凭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发挥以超越“名教”的束缚的言行。
关于阮籍遭母丧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三段记载。其一说,阮籍的母亲去世,他完全不顾世俗的常规礼仪,蒸了一只很肥的小猪,又喝了两斗酒。然后临诀,举声痛号大哭,因吐血,废顿良久(身体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
按照所谓的“名教”,临父母丧事,子女是不能吃肉喝酒的,而阮籍全然不顾。照阮籍看,临丧不吃肉喝酒只是表面形式,与自己内心的这种椎心泣血真情的悲恸毫不相干。阮籍在母亲丧事上的举动表现了他对母亲真正的孝心和深深的感情, 所以孙盛《魏氏春秋》说:“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阮籍的性情是非常孝顺的,虽然丧母没有遵守常礼,实际上悲痛得伤了身体。)有一次阮籍的嫂嫂即将回家,阮籍就去与她告别,遭到别人讥笑,因为这样做是违背礼的,按《礼记·曲礼》说,“嫂叔不通问”,于是阮籍干脆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邪!”阮籍敢于去与嫂告别,表现了可贵的亲情和对女性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这正是“七贤”坦荡的“任自然性情”的精神。
“七贤”中还有一位名士王戎。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戎和另外一“名士”和峤同时遭遇丧母,都被称为“孝子”。王戎照样饮酒食肉,看别人下棋,不拘礼法制度,其时王戎悲恸得瘦如鸡骨,要依手杖才能站起来。而和峤哭泣,一切按照礼数。
晋武帝向刘毅说:“你和王戎、和峤常见面,我听说和峤悲痛完全按礼数行事,真让人担忧。”刘毅向武帝说:“虽然和峤一切按照礼数,但他神气不损,而王戎没有按照礼数守丧事,可是他的悲痛使他瘦骨如柴。我认为和峤守孝是做给别人看的,而王戎却真的对死去的母亲有着深沉的孝心。”一个“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一个是“哭泣备礼”,而“神气不损”,究竟谁是假孝,谁是真孝,谁是装模作样,谁是孝子的真情,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据《晋书·刘伶传》说:“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刘伶感情豪放,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把外在的世界看得那么重要,齐一万物,淡默少言,不随便和人交往,可是和阮籍、嵇康在一起时,精神一下子就来了,拉着手到树林去喝酒了。)
可见刘伶也是一位有玄心、超世越俗的大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说刘伶常常不穿衣裤,裸露身体,在他的屋子里狂饮美酒。有人进到他的屋中,看到如此形状,就对他讥笑讽刺。然而刘伶却说:“我是把天地作为我房子的屋架,把屋子的四壁作为我的衣裤,你们怎么会进到我的衣裤里了呢!”
这虽有点近似开玩笑,但却十分生动地表达了刘伶放达的胸怀和对束缚人们真实性情的礼法的痛恨。这则故事是不是有什么来源呢?我想,它很可能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的一段话有关。阮籍用虱子处于人的裤裆之中做比喻。虱子住在裤裆之中自以为很安全、惬意,因此不敢离开裤裆生活,饿了就咬人一口,觉着可以有吃不尽的食物。当裤子被烧,虱子在裤裆中是逃不出去的。
阮籍用此故事比作那些为“名教”所束缚的“君子”,不是就像虱子在裤裆之中生活一样吗?阮籍认为,那些伪君子“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即制定并死守那些礼法,用它们来控制老百姓。
02
“世道越来越坏了”
为什么阮籍、嵇康那么痛恨“名教”,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对当时提倡“名教”的虚伪面貌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深刻洞察到“名教”本身对人的本性的残害。阮籍、嵇康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应和“自然”(指“天地”)自然而然的运行一样,是一有秩序的和谐整体,但是后来的专制政治破坏了应有的自然秩序,扰乱了和谐,违背了“自然”的常态,造出人为的“名教”,致使其与“自然”对立。
正如嵇康在《太师箴》中所说:上古以后社会越来越坏了,把家族的统治确立起来,凭着尊贵的地位和强势,不尊重其他人,宰割鱼肉天下的老百姓,来为他们统治集团谋取私利。这样君主在位奢侈腐败,臣下对之以二心。这个利益集团用尽心思不惜一切地占有国家财富。形式上还有什么赏罚,可是没法实行,也没法禁止犯法。以至于专横跋扈,一意孤行,用兵权控制政权,逞威风、纵容为非作歹,其对社会的祸害比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还重。
刑法本来是为了惩罚作恶的,可是现在成了残害好人的东西。过去治理社会是为天下的老百姓,而今天却把政权作为他们个人谋私利的工具。下级憎恨上级,君主猜忌他的臣下。这样丧乱必定一天天多起来,国家哪会不亡呢?(原文:“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同样深刻,他说:你们那些“君子贤人”呀,争夺高高的位置,夸耀自己的才能,以权势凌驾在别人上面,高贵了还要更加高贵,把天下国家作为争夺的对象,这样哪能不上下互相残害呢?你们把天下的东西都据为己有,供给你们无穷的贪欲,这哪里是养育老百姓呢?这样,就不能不怕老百姓了解你们的这些真实情形,因此你们想用奖赏来诱骗他们,用严刑来威胁他们。
可是,你们哪里有那么多东西来奖赏呀,刑罚用尽了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于是就出现了国亡君死的局面。这不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君子的所作所为吗?你们这些伪君子所提倡的礼法,实际上是残害天下老百姓、使社会混乱、使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的把戏。可是你们还要把这套把戏说成是美德善行,是不可改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难道不太过分了吗?
(原文:“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趋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照阮籍、嵇康等看,这样的社会政治当然和有秩和谐的“自然”相矛盾,因此他们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对“名教”做了大力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所谓“名教”是有违“天地之本”“万物之性”的,而“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仁义是用来作伪的,并非涵养真性的方法;廉让由争夺中产生,并非出 自人的自然本性。)这种人为的“名教”只会伤害人的本性,败坏人的德行,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由此,嵇、阮发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声。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遭母丧”条,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曰:“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复言之于太祖,籍饮噉不辍。”
何曾是崇尚“名教”的“礼法之士”,在晋文王清客座中,指责阮籍“恣情任性”(放纵自己的感情、任凭自然本性无束缚地发挥),是伤风败俗的人,现在忠臣贤相执政, 一切都有条有理。阮籍听着,不屑一顾,全不理会,照样不停地酣饮,“神色自若”,表现着对何曾的蔑视。“恣情任性”正是“七贤”最重要的“风度”。
所谓“恣情任性”就是说,“七贤”为人处世在于任凭自己内在性情,而不受外在“礼法”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这就是说,“恣情任性”正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嵇康有篇《释私论》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
(译文:真正称得上君子的人,内在的心性并不关注是非得失,可是他的行为不违背大道。为什么这样说呢?神气虚静的人,他的心思不放在外在的是非得失之上;胸襟坦荡的人,那些是非得失不会对自己的心性有什么影响,那么就可以超越名教的束缚而能按照自己的自然性情生活;情感不被外在的欲望所蒙蔽,那才能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才能对天地万物有真正的体认。能够通达天地万物的实情,这样就可以和大道合而为一。真君子必须能超越虚伪的名教任乎自然之真性情,因为外在的是非得失不关乎心性。因此说到君子,不把外在的那些东西放在心上,这才是根本的,要把你内心的真性情放在天地万物上。说到小人,应该看到他们总是隐瞒真实的情感,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隐瞒自己的情感念念不忘私利,是最坏的小人;不把外在的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一任真情,是君子所应实实在在做到的。)
这一长段的意思是说,作为君子应该不把外在的名誉、地位、礼法等放在心上,而是一任真情地为人行事;要敢于把自己的自然本性显露出来,不要顾及那些外在的是是非非,这样一方面可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另一方面又可以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自然”境界。上面所引的文字,说明所谓“七贤风度”就是要把肆意放达的自然性情放在首位。
03
生不遇时,所以借酒消愁
《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嵇康与吕安最为要好,每次想念到他,就驾车前去看望。又有《晋书·阮籍传》:“(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阮籍有时凭自己的心意,独自驾车外出,并不考虑有没有可行车的道路,直到无路可走,痛哭而返。)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嵇康驾车千里寻友,虽有目的,而完全是“恣情任性”, 表现了嵇康对吕安的真实感情。故该条有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则率尔命驾。”为什么嵇康要驾车千里访吕安?这是因为吕安和嵇康一样是一“恣情任性”、不顾礼法的大名士。嵇康的哥哥嵇喜是个做大官的礼法之士,有一次,吕安访嵇康,嵇康不在,嵇喜迎接了,吕安根本不理睬嵇喜,而在门上写了个凤字就走了。嵇喜很高兴,以为说他是凤凰呢,殊不知吕安说嵇喜是凡鸟(《世说新语·简傲》)。
又有一次, 吕安要从嵇康家离开,嵇喜设席为吕安送行,吕安独坐车中,不赴席。但是嵇康的母亲为嵇康炒了几个菜,备了酒,让嵇康和吕安一起吃菜喝酒,二人则尽欢,良久乃去。
干宝《晋纪》据此事,说吕安“轻贵如此”(看不起大官到如此地步)。阮籍的“率意独驾”与嵇康的“千里命驾”形式上相同,但目的不一样。嵇康是有目的地去访吕安,而阮籍是无目的地发泄胸中郁闷,所以他驾车跑到无路可走的地方,兴尽痛哭而回,这可以说是“情不系于所欲”(放纵自己的情感并没有什么具体目的)。
盖魏晋之世,天下多变,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名士,往往不得善终。阮籍有见于此,痛苦至极,而又无法改变现状,故而有此“率意独驾”之举。
在历史上,常有“借酒浇愁”之事。“竹林七贤”多是好酒如命的名士。他们并不是为个人的私事而酣饮消愁,而是因生不遇时,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抱负而“借酒浇愁”,且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豪迈放达之性格。
《晋书·阮籍传》中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本来有改变社会政治现实的志向,但是在魏晋之际,社会政治变化无常,许多有志之士遭受残害,于是阮籍只得远离政治斗争,大量饮酒来消愁。)
《世说新语·任诞》载:“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说得比较具体:“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说,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 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
(阮籍豪放任性,有傲世的性情,不喜欢做官。晋文帝对他很尊重,常常和阮籍谈话说笑,听任他做喜欢的事,不强迫阮籍做官。有一次阮籍轻描淡写地对晋文帝说:我曾去东平游玩过,对那里的风土人情 很喜欢,想到那儿去做官。晋文帝很高兴,答应了阮籍的要求。阮籍于是骑着驴子就上任了。到太守府后首先就把衙门的前后壁打通,使外面能看到衙门内的事情。于是教令清明。十几天后就骑驴子走了。后来听说步兵营的厨房中有酒三百石,又很高兴地要求去当步兵校尉, 一到校尉府中就和刘伶酣饮起来。)
又《竹林七贤论》中说:“籍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死。”此当非事实。因为阮籍于魏景元四年(263)即去世,而刘伶在晋泰始(265—274)时尚在世。“太守”是大官,阮籍去就此职,是因为东平有山水名胜,且民情淳朴。他就任之后,把衙门的前后墙壁都打通,是要让在外面的老百姓能看到衙门内的事情,然后他的行政教令使社会清净安宁。但他只在东平待了十余日,就弃官,骑驴走了。这真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步兵校尉只是个不大的小官,在那里的厨房有大量的美酒,阮籍很高兴地要求去就任,并和刘伶一起酣饮。阮籍的“任性”放达真是超凡越俗了。

刘伶也是酷爱自由、嗜酒如命的“七贤”之一。《晋书·刘伶传》说:“(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刘伶全不顾他的行为对他家族的家产有无伤害,常常坐着一辆鹿车,提着一壶酒,让随从的人拿着一把锄头, 并对随从的人说:“如果我醉死了,你们把我就地埋了吧。”)
刘伶就是对其外在的身体一点都不看重,这是由于他看重的是其内在的放达精神。他写了一篇《酒德颂》,大意是说:大人先生认识到人的一生比起无限的时间、无边的空间,是短暂而渺小的,如果能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和天地一样宽阔,把无尽的时间视为一瞬间,把狂放豪饮看成是“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事,能自由自在快活过一生,比起你们那些遵守“陈说礼法”、追名逐利、钩心斗角的,谁更快乐呢?我们就此可看出“七贤名士”的“放达”精神之可爱了。
关于刘伶还有一个故事,《世说新语·任诞》中说:刘伶太想喝酒,请他的妻子给他点酒喝。可他的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壶碎掉,哭着对刘伶说:“你喝酒太多,有伤身体,不是养生之道,快断酒吧!”刘伶说:“好呀!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断酒,要向神鬼祷告求助,向他们发誓断酒才行。”这样就得有酒有肉来祭祀鬼神。于是他的妻子置办了酒肉于鬼神牌位前面,让刘伶发誓断酒。于是刘伶跪着向神牌发誓说:“天生刘伶嗜酒如命, 一饮一斛,五斗酒下肚可以解我的嗜酒之病。”于是酣饮大吃,醉得像土石一样。
这些“七贤”酣饮故事说明,处于世事混乱之时,这批名士无力改变现实,只求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愉悦。
04
把“真情”放在第一位
正如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古来那些经典的目的是对人们进行压制和引导,然而人之本性所追求的则是以顺应其性命之情为快乐。引导和压制是违背人的意愿的,放任其性命之情才是顺乎自然的。追求顺应自然的本性才是根本的,因而不需要侵犯人性情的礼法之类的东西。)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七贤”之饮酒“恣情任性”是要求摆脱虚伪“礼法”之束缚,而求任自然性命之情,这正是“七贤风度”。
“七贤”之酣饮,在当时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此拒绝和抵制当权者种种要求。《晋书·阮籍传》:“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是否有所夸大,不得而知,但它所要表现的是当时某些名士不愿与腐败、凶残的当政者合作,有着不愿攀龙附凤的气概。
抱有济世之志的阮籍在“七贤”中也是强烈表现放达个性的一位,他作《首阳山赋》,以伯夷、叔齐自况,以示和司马氏政权不合作。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借楚汉相争事,暗示他自己所生之时缺少英雄,遂使司马氏得以专政。但后司马氏篡位,建立晋王朝,阮籍最终也不得不写了劝进文。在这点上,他或与有刚烈之性的嵇康有所不同。据《世说新语·雅量》,嵇康因吕安事被判死刑,将在东市被斩首,这时他看看日影,知道被杀的时间快到了,于是要了琴,弹起来,说:“过去袁孝尼尝希望跟我学《广陵散》,我没教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广陵散》了。”在他被杀前,“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广陵散》绝了,嵇康之人格是否也绝了呢?回顾历史,俯视现实,多少悲剧不是如此呢!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真是太软弱了。
“恣情任性”“情不系于所欲”表现了“七贤风度”,应如何评价,历史自有公论,这点不需要我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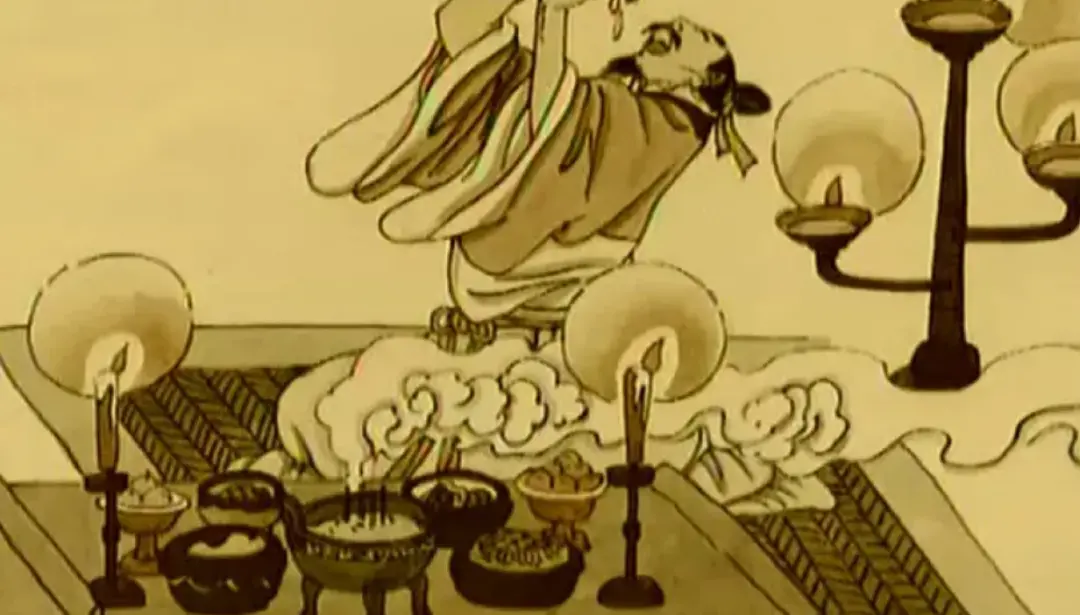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指出,魏晋时代是一社会秩序大解体、旧礼教崩溃的时代。它的特点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它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之前的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在它之后的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释、道三教的支配”。宗白华认为“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
王戎尝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意思是说,圣人太高超了,他们已超越常人的“情”,而最低下的人又对“情”太迟钝麻木,难以达到“有情”的境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名士珍视自己的感情,才敢真正把真情表现出来。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对“圣人”有情无情曾有所讨论。
何劭《王弼传》中载,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论说得很精彩,当时钟公等名士都赞同,只有王弼不赞同。王弼认为,圣人与一般人相比,他们的不同在精神境界上,而在五情上是相同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孔子对颜回“遇之不能不乐,丧之不能无哀”。可见圣人是有喜怒哀乐之情的。但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因其有一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可以做到“情不违理”。
在《世说新语·文学》中也有一条关于“圣人有情无情”问题的讨论。王修(字敬仁)在瓦官寺中遇到和尚僧意,僧意问王修:圣人有情否?王修回答说:没有。僧意进一步问:那么圣人不就像一根木头柱子了吗?王修回答说:圣人像算盘一样,算盘虽无情,但打算盘的却有情。
僧意又说:如果圣人像算盘一样,那么是谁来支配圣人呢?王修回答不了,只能走了。从此段讨论看,王修也许不知道王弼对“圣人有情”的看法,圣人有“情”但可“以情从理”。“七贤”名士有“情”,但并不都是“以情从理”的,而是“恣情任性”的,他们的生活是把自己的“真情”放在第一位,认为这样才是人之为人应有的,隐藏自己的“真情”是“小人”。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的邻居中有一位美貌出众的妇人,常烧饭菜,卖酒。有一天阮籍和王戎在那儿喝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妇人身旁。那妇人的丈夫起疑,就去察看,看到阮籍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刘孝标的注有个相似的故事说:阮籍的邻居中有一未嫁的女子甚美,不幸早逝。阮籍和她无亲无故,根本不认识,却到那里悲哀地哭,哭完了就扬长而去。刘孝标评说:“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阮籍的行为虽说是任情放 达但不够检点吧!)这两则故事都说明阮籍虽有违当时的“礼教”,但确实是“情”之所钟者。
无独有偶,阮籍侄子阮咸也有一故事,《世说新语·任诞》中载:阮咸和他姑姑家的鲜卑女仆有染。后阮籍母去世,姑姑要回夫家。起初说可以把鲜卑女仆留下,但临行前,他的姑姑又把女仆带走了。于是阮咸借了匹驴子穿着孝服去追赶,然而跑了一阵驴子跑不动了,不得不回家,说:人种不可失。因为这位女仆怀有他的孩子。虽然魏晋时虚伪的礼法早已败坏,但世家 大族仍然在表面上固守礼法。然而“任自然”的“七贤”多把“情”看得比礼法更重,因此常常做出违反“礼法”的事。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阮氏叔侄不仅因“情”而坏礼,而且对妇女也比较尊重。
在《世说新语》中还记载有嵇康锻铁、阮籍狂啸的故事,这都表现了“七贤”的“恣情任性”“逍遥放达”的性格和精神面貌。
《世说新语》赞扬当时某些名士如“七贤”所追求的“逍遥放达”,也并非无条件地赞美,而是以精神上的自由为高尚,认为言谈举止必须有“真情”,应顺乎“自然本性”,既不要拘泥于虚伪的“名教”,也不去追求肤浅形式上的放达,成为“假名士”。
乐广曾批评元康后的“放达”。他认为,竹林以后元康时期的“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之流“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盖“任放”是指任意放纵,而“达”是指一种“任自然本性”的精神境界。所以没有“达”这种精神境界的“放”只是“放达”的低级形式。魏晋之际,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如“七贤”等名士是有精神境界的“放达”,而西晋元康中的某些名士的“放达”是无精神境界的一种形式上的“任放”。
鲁迅说:“(竹林七贤)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一些所谓“君子”,只知道去维护那些虚伪的“礼义”,缺乏对人心的了解,所以在历史上有“真性情”的人常常被社会所误解了。我想,鲁迅是真的了解“七贤风度”的智者。

文章来源:凤凰网
作者:凤凰网文化读书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