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福东/文 齐邦媛去世,在海峡两岸掀起缅怀浪潮。这是她魅力与影响力的见证。我2011年春在台北市松江路“人文空间”专访过她,一转眼13年过去了,于今她的个人形象对我仍是丰满的。她那样儒雅,带着不刻意的西式幽默,平易近人——所有这些私下接触而来的个人感官印象,与她皇皇巨著《巨流河》所承载的大历史信息汇合在一起,让我突然很想念她,在成都飞北京的航班上翻检过往的采访记录准备写作本文时,我竟有些泪目。
齐邦媛对我说,她在写作《巨流河》的时候,眼泪没有干过。她那么想回东北家乡而不得,这是她的乡愁,也是《巨流河》始终未曾停歇的言说主题。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文学教授的表达天赋、细腻而充沛的情感、遭逢乱世的传奇家世——所有这一切构成这本现象级书籍的流行因子,它在海峡两岸都有引发共情的心理基础。
一个在中西文学教授与译介上贡献卓著的学者,在80多岁之后突然因个人回忆录而成就如此大名,这种案例并不常见。她一定契合了时代的某种情绪,而我们该如何归纳这种情绪呢?
齐邦媛生于1924年,是辽宁铁岭人——这个在脱口秀时代被戏称为“宇宙尽头”的地方,当年却是东亚的风暴眼。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满族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德国,在效力奉军郭松龄部期间参与兵变,最终流亡关内。作为张学良的宿敌,他后来成为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活动的负责人。这是齐邦媛与生俱来的时代背景,无可回避。奉军的内讧、与国民党的纠葛以及更为重要的被日本侵略军按在地上摩擦的血泪史,已经成为她个人生命中抹擦不去的底色。在任何意义上,齐邦媛都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人,她的这一价值取向无疑要从成长经历中去获得某种理解。
齐邦媛1947年去了台湾,潜心西洋文学研究,先后执教于中兴大学外文系与台大文学院。
在2009年出版的《巨流河》中,赴台前后是两段叙事情调迥然有别的章节。对中国大陆读者而言,普遍的感受是前半部分太过精彩,后面的章节则相对较少共鸣。这当然和齐邦媛在台湾的家庭与教学生活已没有那么多冲突有关,那些精彩的华章都聚焦在她生命中的前23年,它能部分回答《巨流河》到底契合了哪一种情绪。
值得感念的是,台版《巨流河》出版不久,大陆简体版也很快付梓,这让海峡两岸读者的共振成为可能。比较遗憾的当然是简体版删除了一万多字。隔着15年的烟尘,历史的纠葛在现实中似乎更加复杂,不知道齐邦媛病逝前内心怀抱着怎样一种乡愁。但这种从大陆撕裂又梦想回程的情结,随着齐世英与齐邦媛两代人的凋落,不知又将面临怎样的叙事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巨流河》是代表一个世代的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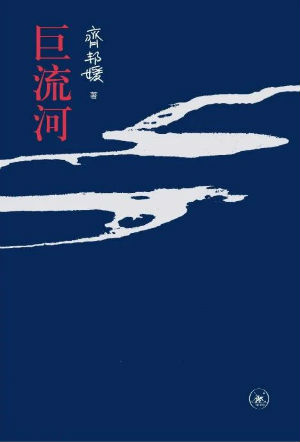
《巨流河》
齐邦媛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10月
一
齐邦媛过世的消息传来,我的朋友圈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论。简单说,争论的一方盛赞《巨流河》是他们读过的最好书籍之一,另一方则宣称这本书被过于高估。
我之前也曾为《巨流河》写过,就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评价:“齐邦媛一生与文学为伍,谨慎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但其政治理念受父亲影响至巨。齐世英与张学良矛盾甚深,晚年反蒋,齐邦媛在回溯历史时,所持观点立场与乃父相当。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她的历史叙事少了某些超脱的色彩。譬如,将郭松龄倒戈完全归因于‘厌倦穷兵黩武的政策’似亦过于简单。民国肇始后,各派军阀包括国民党均野心勃勃,互相厮杀且内斗不止,导致生灵涂炭,过于美化其中的任何一方均非平实史观。”
直到今日,我仍持类似的见解。
郭松龄毕业于奉天武备学堂,是奉军革新派的领袖之一,很受张学良赏识。1926年,他与冯玉祥合谋,倒戈张作霖,后兵败遭诛,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则成功出逃。齐邦媛在《巨流河》中给予郭松龄非常高的评价,说他兵变的原因是“早已厌倦穷兵黩武的政策”。
记得2011年采访齐邦媛时,她也提到郭松龄,对他的评价高到无以复加:“郭松龄兵变,我想历史上已经认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如果当年兵变成功,东北一切的资源都有,稳下来的话,日本人不可能过海来侵略东北。没有东北侵略,哪有后来那些事。郭松龄是真正懂知识的。我对知识救中国是深深相信的。”
郭松龄倒戈如果成功,结局会怎样,其实很难预料。他背后有苏俄支持,又与民国时期公认投机性最强军阀之一冯玉祥合作,还团结了奉军保守势力李景林。你觉得这个阵营,真的那么值得期待?
我们不妨看看王奇生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中对郭松龄兵变始末的描述与评价。该书提到,奉军内部倾轧不已,郭松龄掌握最精锐部队却受排挤没有地盘,所以与冯玉祥暗相结纳反奉,“密约内容除几条空洞的政治条文外,核心是双方协议打败张作霖之后各自的地盘分配。”节节溃败的张作霖甚至将下野通电都起草好了,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双方达成密约:张作霖同意日本人在东三省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与当地中国人一样的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并移让间岛地区的行政权与日本等;日本方面则出兵助张反郭。在日本军队的武力干涉和直接支持下,张作霖的部队很快扭转败势。
和1920年代走马灯的内部倒戈一样,郭松龄兵变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时人基本上把他与冯玉祥相提并论。
所以虽然有如椽大笔,配以“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这样的煽情情节,齐邦媛的历史书写终究有很多可疑之处,这是不可以“文学化”做辩护的。因为在任何意义上,回忆录都归于历史书写,而不是小说。
齐邦媛关于自己父亲齐世英的记录比较多,其中也有不少槽点。这在个人回忆录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倾向于美化自己的亲友。这亦可归于某种程度的“亲亲相隐”,不过这个规则在司法中具有正向性,但在史学书写上基本就是负分。虽然能够理解作者的初衷,但评论界其实有责任表达出这方面的不同意见。
关于齐世英,目前比较通行的出版物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和《齐世英口述自传》,均是带有强烈个人倾向的一家之言。如果研究齐世英,空间还是蛮大的。
二
最初读《巨流河》,给我最大震撼的是齐邦媛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前后的经历。我当时正对群体行为的心智着迷,她给出很多第一手的亲历者资讯,助益了我的思考。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彼时已是国民党CC系的骨干、“立法委员”,在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麾下从事秘密活动。齐邦媛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很自然在情感上支持官僚权力结构,对民间运动保持距离。这样的立场大有可商榷之处,但我们在做历史关照时,如果长期忽视这种视角或仅仅将其作为负面观念而加以妖魔化,是很难从过往教训中获取经验的——不仅历史失去镜鉴的可能性,事实层面的书写也必将陷入偏颇。《巨流河》中提到,她在珞珈山武大校园读书时,缪朗山教授在学生中有巨大影响力,她又由此提到闻一多,当时的群体运动给她带来巨大的“困惑与悲愤”。她说闻一多等人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
在接受我采访时,她提及此事,说之所以写闻一多那一段,是对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的一个很大反省:“闻一多我们崇拜过,他的诗我到现在还会背,他是我真正的偶像,也是很多人的偶像。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
抗战胜利,这个全民皆大欢喜的事件,在《巨流河》中却是“失落的开始”。“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后她在武大校园,更进一步感受到自己的“落伍”及与“前进文学”的距离。
不过,齐邦媛显然有对此进行“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的想法,但终归只是浅尝辄止。
她似乎想走得更远些。所以她又对我说:我现在要求我做近代史研究的学生做一点关于国民政府当年腐败状况的研究,那个时候到底有多腐败?所谓腐败,要有些具体的东西。我不敢说那些官员都好,可是,我们穷到什么程度?确实不像今天这样满地都是钱诱惑你去腐败。那时没有那么多诱惑你腐败的东西。那个时候生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齐邦媛诉诸了个人体验,她毕竟在国民党高官的家庭中长大。但这种个人体验有多大的说服性?且不说回忆可能经过了扭曲,她又对自己的父亲了解多少?至少我在《巨流河》中没有感受到她所说的那种“穷”。就如书中间接提到的:早在抗战如火如荼之际,齐邦媛就因自己的身份而受到“进步”青年的敌视。室友侯姐姐用大嗓门不指名地说她,“有些人家长在重庆做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齐邦媛的家庭毕竟处于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上端,“穷”本身尚需得到证明,更遑论用其来证明有没有腐败了。
齐邦媛的上述表述很难说有多少真知灼见,她仍在用过于感性的情绪来努力解释那个刚刚消逝的世界,提供的事实似也有剪裁的痕迹。但它仍具有巨大的启发性,齐邦媛的价值在于她敏锐的直觉、问题意识和文字表达上引发情绪共振的能力,个人、家族与时代的紧密纠缠也给了《巨流河》巨大的史诗般的感染力。因而,她的史观虽有天真之处,却得以在众多回忆录中脱颖而出。
三
齐邦媛曾编著了一本《洄澜:相逢巨流河》。“永远的齐老师”在台湾桃李满天下,《巨流河》的出版又是文苑盛事,所以我们能在这本书中最集中地看到针对齐邦媛与《巨流河》的名家评论与记者访谈。该书在大陆亦有出版。

《洄澜:相逢巨流河》
齐邦媛 |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1月
我为《看历史》杂志写的那篇访谈《“我现在还有一个精神在”》也很荣幸被收录其中。就是在这篇访谈中,齐邦媛老师谈到上述对郭松龄及国民党腐败的进一步看法。和写作《巨流河》时相比,她的思考有进阶,或者是她在书籍中未便直言的观点现在有了显性表达的时机。她的偏颇有时是明显的,譬如对郭松龄的评价,可为什么她在这一思考进路上越走越远?
《洄澜:相逢巨流河》或许能提供答案的一个侧面。
相对于《巨流河》传播的巨大声量而言,它所收获的回馈太过单一了。《巨流河》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但并没有几个人在讨论一部“历史回忆录”的得与失,所有最优美的言辞几乎都用于赞扬。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并不是传统的适宜场景下,当《巨流河》因齐邦媛的过世而再度成为话题时,我的几个朋友在微信群中讨论的竟然是:这本书被高估了。
齐邦媛看过很多《巨流河》的,但似乎并没有接收到一些更坦率的——譬如对郭松龄叙事的批评。没有思维的交锋,所以她任由自己的思考沿着既有进路前行。很难说这是文评圈特有的痼疾,但一个健康的生态的确要建立在更多元的观点碰撞之上。
王鼎钧曾评价《巨流河》“似乎没有史学抱负”,我觉得并不对。看怎么定义“抱负”吧,齐邦媛的确有强烈的重新评价历史的情绪,但她所擅长的终归只在文学。据说她是台湾最早将《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作品引入课堂的大学老师。在我看来,她一生强烈的政治倾向,一是对“左倾”群众运动的警惕——这来自她青年时期遭际;一是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晚年对大陆国际地位的升落都有强烈的代入感,这是她身世飘零、在台湾亦摆脱不掉“外省人”标签的应激心理积淀。
就文本与表达技巧而言,《巨流河》远胜过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但它的槽点也更多。《巨流河》是齐邦媛为时代留下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回忆,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文学化传统——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式的文学表达与阐释,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情绪共振,但也给想象、扭曲甚至杜撰留下了空间。
个人回忆录的“隐恶扬善”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记得前几年读近代金融大佬资耀华的回忆录《世纪足音》时,就有很深的感受,还为此写过一篇《两个资耀华》。《世纪足音》中那个“求真实而已”的资耀华,在《人民日报》中却是多次运动中主动批判别人的弄潮儿,只不过这些“黑历史”都在晚年的回忆中消失掉了。
个人回忆录的问题,与其归咎于文体,毋宁说症结在人性。对这种现象最温和的评价是:它是一种必然被高估的文体,是需要被甄别与汰选的历史记录。作为评论者,我们对齐邦媛老师最好的纪念,是尽量不落入文辞的圈套,是不要一味颂扬,是对一种必然被高估的文体进行纠偏,是完成她念兹在兹的追问,让围绕《巨流河》的评论提供事实与价值增量,而不仅仅是一堆华丽丽的赞词。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