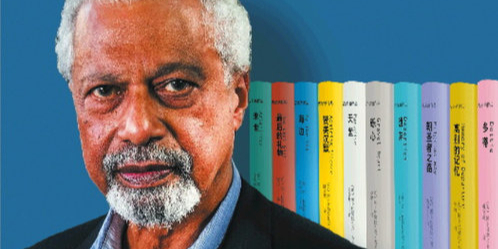
“虽然我从未造访过中国,但从地图上就可以感知中国的幅员辽阔。我一直想感受迷人的中国文化,希望在这几天里见识到各种有趣的事物,以及历史与当代的成就。”3月5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受邀来到中国,开启了他的首次中国之行。几天时间里,他到访了上海、宁波、北京,与作家格非、孙甘露、莫言展开了精彩的文学对话,到董宇辉直播间聊人生、阅读和写作,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进行了参访交流活动。
2021年,古尔纳因“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目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出版古尔纳的10部长篇小说作品。
古尔纳×格非
谈论痛苦
六百多年前,郑和以航线连接大洋彼岸的中国与东非,如今,两地的文学在上海相遇——3月6日,古尔纳与中国作家格非展开了主题为“我们必须谈论痛苦”的对谈。
“‘痛苦’这个词本身就是古尔纳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我们做了一些统计,发现古尔纳‘痛’得比格非还厉害一点,比如说在《海边》中pain出现了27次,suffer、distress加上程度比较深的torment、agony就高达70次,《砾心》中pain有31次,最新的小说《来世》痛得还厉害,光是pain就有53次。我们检索格非作品的时候也发现主人公都挺不好过的。我想问两位,这么多年写下来为什么痛苦一点没有减轻?越是新作越痛苦,难道写作不是一种缓解或者减轻痛苦的方式吗?”现场主持人毛尖以幽默的方式将问题抛出。
古尔纳表示他作品中的“痛苦”有别于物理的肉体的痛,而是一种强烈的感受或者情感,是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的、回望人生时的苦楚:“我想到我父亲生命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看他一个人安静地坐着在看街道,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他在想那些让他痛苦的事情。所以随着生命经验的累积、记忆的增长,你的痛苦也会增长。”
格非则认为痛苦代表着某种幽暗和晦暗,“就是身处其中却不明原因,就是光的不可抵达,正因为光不可抵达,你才会去寻求光,你要寻求光的话必须到幽暗中去寻找。‘哪里有危险哪里有拯救,拯救一定来自危险’,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小说家会把‘痛苦’作为一个共同主题的原因”。
谈及“乡愁”话题时,古尔纳表示:“对我而言,乡愁并不意味着远离家乡,而是失去家园。”这也与他的几部代表作,如《天堂》《来世》《海边》等小说的主人公的经历相呼应。他指出,现在普遍的一个文学的现象是,我们通常会说回到故乡,故乡总是让我们心安、舒心,而不会说故乡让我们觉得很恐怖,觉得很不同,“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我们要更加诚实地来面对不同的、复杂的感受”。
古尔纳×孙甘露
谈论写作
古尔纳1948年生于东非海岸附近的桑给巴尔,这座小岛后来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1964年,革命爆发,古尔纳踏上了前往英国的道路。他在那里接受教育,并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他笔下的故事如拼图一般构建起自己的文学世界,不断拾起每一位离散者和异乡人,试图解答每个人的归属困境。3月7日下午,古尔纳与中国作家孙甘露以“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为题进行对谈。
古尔纳表示,作为异乡人的经历对于他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假如我在10岁的时候离开家乡,我对从小生活的环境会有很多记忆和印象,但是更多的东西是想不明白的。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18岁了,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只不过还没有看透,没有想明白。”他的作品不仅写留在身后的故乡,还讲述生活当下的环境;不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叙述了几百万人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来到异乡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共处的这个时代的描写”。
“我作为异乡人,在异国他乡的地方,周围的生活也好,环境也好,对我来说都变得非常复杂,从一定程度来讲是非常艰难,我花了一定的时间慢慢适应这样的环境,去理解自己的处境,去梳理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移民英国后,古尔纳用了好几年时间慢慢地、认真地思考创作这件事。古尔纳在创作初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这条路上并不总是都是困难,因为我愿意去写,去创作,我发自内心想要做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本身你要自己发现很多东西,然后慢慢认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难的,但是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会觉得其乐无穷”。
孙甘露坦言写作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写作的困难就和人生的困难是一样的,因为写作就是要处理你人生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人生有多困难,写作就有多困难”。
古尔纳×莫言
谈论故乡与他乡
故乡是每个人生命的源头,也是游子心之所系的起点,更是文学永恒的精神母题。无论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古尔纳书写的桑给巴尔,都呈现出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和对世界的不断深思,由此诞生了诸多充满寓言意味和命运感的故事,3月11日,两位诺奖作家进行了题为“文学的故乡与他乡”的文学对话。
非洲对于古尔纳来说是“故乡”,而对于莫言来说则是“他乡”。莫言认为过去从作品中了解到“文学的非洲”与真正看到“现实的非洲”有很大不同。他曾在马拉河边等待着看成群结队的动物“英勇”过河的壮观场景,但始终没有等到;那些有耐性的、美丽的金色鳄鱼,的确会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任凭飞鸟落在它们身上,任凭阳光曝晒、劲风吹拂;当眺望“乞力马扎罗的雪”时,他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小说中那只高山上冻僵的豹子——“它是为了追寻光明和理想爬到高山,它的牺牲有一点壮美的境界”。
对于古尔纳而言,非洲则承载着不同的记忆:他的故乡是非洲的一座小岛,那里有大片的海滩——“我们的海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和世界进行着连接,与世界的其他文化进行着跨大洋的交流”。正如当年郑和船队的到来,让非洲了解了中国,家和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莫言进一步提出,随着作家创作经历的延长和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作家“故乡”的范围中。
谈到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阅读感受,古尔纳表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语言描写、叙事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气息”,他称赞莫言的小说特别擅长书写一个普通人在宏大历史中具体经历了什么,这对于读者而言是具体可感的。
莫言则从“讲故事”的角度强调,作家的写作一定脱离不了自己的故乡。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往往就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说家的自传或许包含着小说的成分,但小说家的小说却恰好表现很多自传的内容,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而仅仅是艺术的问题。他以古尔纳的《遗弃》为例进一步说明,不同于历史学家全方位、立体地描写一场巨大的变革,小说家更擅长的是“由小见大”,从一扇窄门进入宽广的世界中去。
莫言还谈及了当下的热门话题——AI技术,他表示,尽管科技日益发展,“给文学敲警钟”的言论层出不穷,但事实证明,文学永远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亡,他与古尔纳并不会因为AI的出现而“失业”,因为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这种思维的获取,需要从本民族传统里面寻找不可代替的资源,并且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接触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与现实追求,让文学可以真正走向世界,而这正契合了古尔纳的文学追求。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曲鹏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