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国imaginist/文 1967年的一个雨天,一个叫程守义的医院职工因政治斗争被关进塔里。第二天他精神恍惚,失语,畏光,不停地呕吐,手脚开始麻木。很快,他的手臂抬不起来了,双腿也不能下地走路了……
X光片显示,他的颅腔里被插入了一根两寸长的铁钉。
不久,内科医生汪良成在家里用一根输液管上吊自杀了。他是单纯因为恐惧,还是畏罪自杀,谁也无法弄清楚。有目击者称,那天下午确实看到他撑着伞朝塔的方向走,旁边还有一个人,穿着雨衣,看不清楚脸。那个人或是他的同伙,很有可能还是主犯。
没有发现可疑之人,也找不到确切线索,案子最终不了了之。然而,三个家庭,三代人,被这枚钉子牢牢地钉在了一起。

《茧》人物关系图
在张悦然的《茧》中,李佳栖和程恭以双重第一人称的方式重构起1960年代的一桩悬案,他们的回忆和想象相互补充,逐渐还原出家族的真相。“钉子”深深刻入血肉,祖辈的生死恩怨、父辈的情欲纠葛,连同这辈人的疏离颓废,织就了令人窒息的茧,当事人们该如何破茧重生呢?
雨夜的罪恶
*节选内容为程恭的独白
我爷爷是一九六七年出事的。医院的人划分成两派势力。爷爷当时是医院的领导,属于“保皇派”。还有一些人是“造反派”。“批斗”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姑姑对它的解释是,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一个人。爷爷就受到了这样的折磨,然后被关入了牛棚。

《茧》实拍图
爷爷当时被关入的牛棚,竟然就是我们每天去玩的死人塔。在一场批斗中,他被殴打,身上多处受伤,然后被关进塔里。第二天,我奶奶把他接回来的时候,他的精神很恍惚,也不会说话了,还很怕见光,不停地呕吐。我奶奶只当是受了惊吓,静养几天就会好。可是情况越来越糟,他的一只手臂失去知觉,抬不起来了。双腿也开始麻木,不能下地走路了。又过了几天,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只能支支吾吾地发出一点声响。我爷爷被抬进了医大附属医院。医生也查不出病因是什么。情况一天天变得更糟,没过多久,他全身都失去了知觉,除了会眨眼睛,有心跳之外,与死人一般无异。
医院召集各个科室医生会诊,给我爷爷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最终在X光片上发现,他的颅腔里有一根两寸长的铁钉,应该是从太阳穴附近插进去的。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创口,当时家里人还以为是皮肉外伤,也没在意。铁锈致使脑组织感染和溃烂,并且正在蔓延,必须马上开颅取出。
作案时间应该是在批斗结束,人们散去之后,凶手去了死人塔,把钉子插入他脑中。因为先前遭到殴打,他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神志也不是太清楚,所以很可能没有反抗。操作的人一定熟悉解剖学、有丰富操作经验,才能准确地找到这个位置,避开重要血管,令我爷爷不会当场毙命。伤口也做了适当的处理,可以加速它的愈合。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医大附属医院历史上最精湛的一次手术,只可惜没人知道主刀的人是谁。

《暴雪将至》
手术很成功。那根钉子被取了出来。它像搅拌器似的搅动着脑浆,使它在混入铁锈和细菌之后,发酵成了别的什么物质。烂掉的大脑已经开始发臭。医生竭尽全力将切除的部分减到最低,保住了三分之一的大脑。可是爷爷的状态和手术前毫无分别,既没有死,也没有醒。
如果爷爷死了反倒会好。烧掉了,看不见,摸不到,彻底失去了他的感觉,会让悲伤更长久。可他还躺在那里,睁着无忧无虑的大眼睛,排泄出恶臭无比的粪便,而且就算家里出了再大的事,都与他无关了。变成植物人,就像掉入了生死之间的一条沟渠里。活着的人过生日,死了的人有忌日,植物人既不过生日,也没有忌日。他们没有任何纪念日。
永远被钉在了回忆里
*节选内容为李佳栖的独白,“你”指的是程恭。
在短短几个月里,汪露寒经历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父亲用橡皮管勒死了自己,母亲躲进了衣柜里。哥哥远在北京回不来,她一个人撑起破碎的家,照顾精神失常的母亲,洗菜烧饭,做所有的家务。有一天弄丢了粮票,在街上一直找到天黑,第二天只好厚着脸皮去问亲戚借。还有一天下着大雪,她借了一辆底盘车,到煤站拉一车煤球回家。半路上经过一个大下坡,被两个少年拦住了去路。其中一个是你爸爸。你爸爸一直以报仇为名纠缠她。他们冲上去把底盘车掀翻了。煤球沿着坡道滚下去,埋进积雪里。他们在上面踩跺了一番,才满意地离开。汪露寒把碎掉的煤球从雪里拣出来,放回车里。我爸爸走过来,蹲下帮她一起拣。他一直远远地跟着她,像一个影子,忠诚而无用。在她被欺负的时候,他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什么都不能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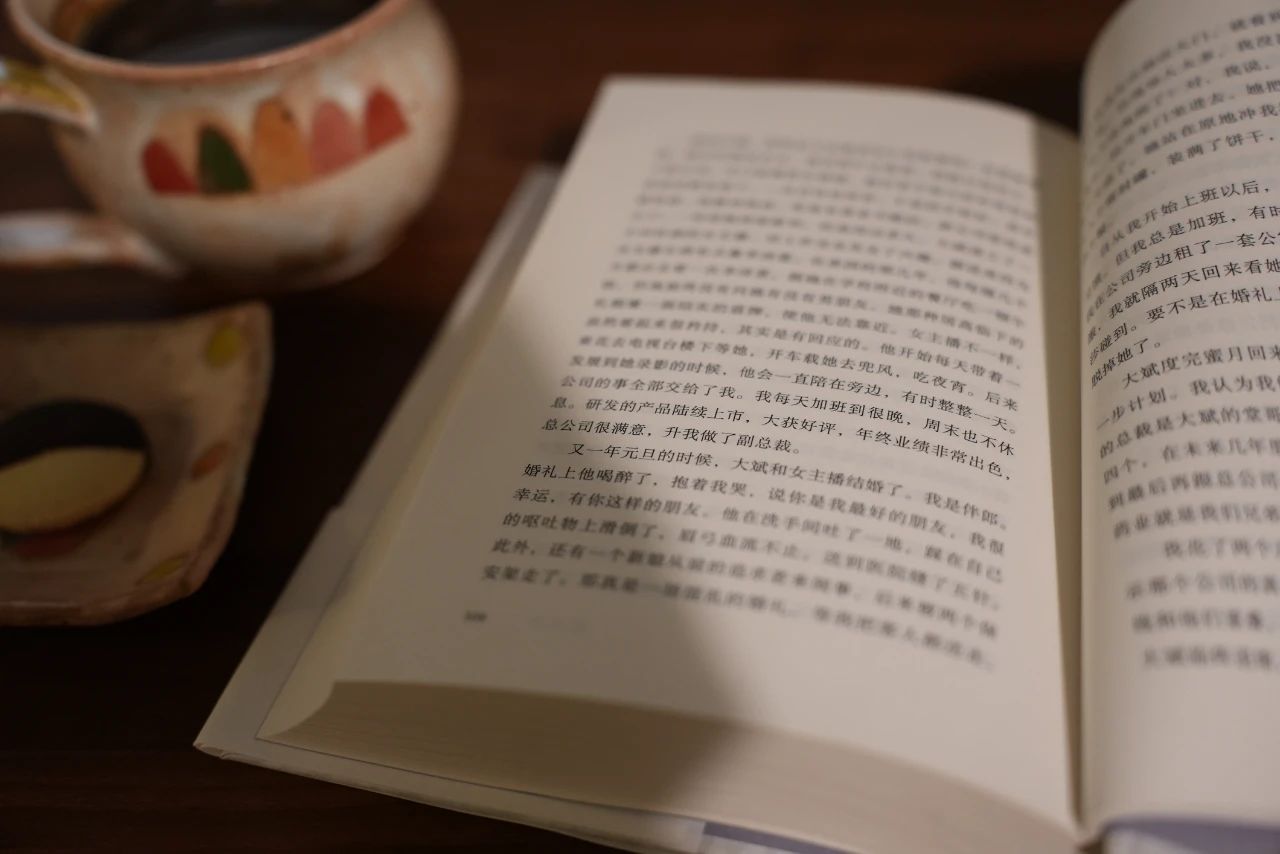
《茧》实拍图
我爸爸通常会在汪露寒家逗留到吃晚饭的时候。一旦她母亲犯起病来,这种短暂的安宁立即会被打破。
看着天光渐暗,一盏盏窗户点起灯来,她坐在黑暗里,开始发抖,对着墙壁呼喊丈夫的名字,哀求他不要丢下她。
“不要怕,又不是你干的,你怕什么,是你的钉子又怎么样,你什么都没做啊……”她不断重复着,好像再多说几遍就能让丈夫改变心意。她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个夜晚,回到命悬一线的时刻,试图用徒劳的劝解把丈夫从死神那里夺回来。她正在酝酿情绪,要好好发一次病。
她母亲不想从痛苦里走出来,那好像就意味着背叛。她也不允许汪露寒走出来。所有的快乐都是不敬的,应该被禁止。她母亲是一只从往事里伸出来的手,非要把她拉入那个记忆的黑洞。

《相亲相爱》
一九六七年那个审讯的前夜,外面下着大雨,闪电擦着窗户划过。汪良成睡不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妻子一直陪着,不停地安慰他。天快亮的时候,雨变小了,他终于听妻子的话,到床上去睡一会儿。没过多久,他腾地坐了起来。妻子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他说想起抽屉里还有两颗钉子,怕警察来家里搜,得找个地方藏起来。他走到外屋,把所有的抽屉都翻遍了,没有找到那两颗钉子。他将抽屉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趴在地上仔细地找。汗水沿着脸颊往下淌。他焦躁地拨拉着那些东西,呼吸越来越急促,直到一只手在杂物堆里触到那一捆橡皮管。褐色的橡皮管,像富有弹性的肉皮,带着人身上的体温,突突地敲打着掌心。窗外的雨声消失了,他心里变得很静。
厕所里有扇小窗户,与天花板齐高,他把橡皮管绑在当中的窗框上,套住脖子,踢掉了脚下的凳子。
是他的女儿先发现了他。她起来上厕所,推开门看到他吊在窗户上,青灰色的脸上蒙着一层雨水。她尖叫着跑了出去。
罪与罚
*节选内容为李佳栖的独白,“你”指的是程恭。
汪露寒低着头说,走吧,不用你管,你不是得跟我划清界限吗?
划清界限,我爸爸确实应该这么做,可是界限究竟在哪里?表面上看,他们的处境如此不同:她的父亲畏罪自杀,母亲疯了,整个家都毁了,他家却一切如常,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事实上,她是罪犯的子女,他也是。他父亲什么也不肯说,但是他知道他也脱不了干系。不同的是,他必须假装自己是正常人。
他也不想回家,家里压抑得让他喘不过气。父亲蹙着眉头,一言不发。而母亲只是偷偷地哭,然后把手放在《圣经》上祷告,主耶稣啊,请求您的宽恕。他觉得她对上帝似乎也不是很有信心,才非要讲那么大声,说那么多遍。全家人坐在方桌边吃晚饭的时候,各自低头扒饭,谁都不说一句话,屋子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一片响亮的咀嚼声,仿佛每个人都在啃噬着其他人的骨头。
你爸爸也开始找我爸爸的麻烦,逼问他为什么总是跟着汪露寒,让他承认他父亲参与了汪良成的阴谋。我爸爸任凭他们辱骂,什么话都不说。你爸爸就带着人到我爷爷家去。我奶奶吓坏了,好几天没下床。她把我爸爸叫到身边,求他以后不要再和汪露寒来往。离她远一点吧,她说,别把我们这个家给毁了。而我爸爸回答,这个家早就毁了。

《狗十三》
去年我差一点结婚。那个人叫唐晖,是我大学的学长,我们认识得很早,但已经太晚。我人生中的大事早已发生。他发现了这一点,但还是想试一试,只可惜到最后没有成功。
“在你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罪感。”和我在一起之后,唐晖变得很擅长精神分析,“你相信你参与过他们大人所犯的错,所以记忆慢慢被篡改,你让自己以为看到了那团东西,并且处置了它。”
负罪感。是的,我有。可它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随着一遍又一遍的回忆而产生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的确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走到他们当中去,分担他们的罪。也许是因为生活太空虚了,非得挤进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才能找寻到存在的意义。

《茧》实拍图
汪露寒不知道从哪里结识了一帮信教的人,跟着他们信上了耶稣。不是那种睡前读读《圣经》、礼拜天去去教堂的信徒,而是要有行动,每时每刻都想着如何赎罪,如何取悦上帝。她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去医院、福利院、残疾人协会,风雨无阻,一次都不落下。谢天成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偏执的教徒,像记工分似的做好事。后来她就失踪了。
我问,你觉得汪露寒原谅我爷爷了吗?
谢天成说,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也有罪。好像总得有一个人担着那些罪。你爸爸死了,她就承担起来了。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