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4年香港出版的《新希望》杂志,发表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华侨的信,标题是《谁先发现澳洲问题》,与此同时,新希望杂志指定专人就来信进行解答,并发出征文信息,吁请更多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参与讨论,以为厘清此题。各方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辩论,终因可证资料缺乏,未能达成相对统一的认知,这场浩大的讨论无果而终。可喜的是,著名历史与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以此为契机,迅速扩展,利用现有历史资料,以设题推演的学术研究方式,出版了轰动历史学界的著作《中国人发现澳洲》。
怪才卫聚贤

卫聚贤(1899—1989),山西万荣人,字怀彬,号介山,以山西商业专科学校毕业生身份考入清华学校(大学),跟随王国维、梁启超研究国学,追随李济学习考古,清华毕业先后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吴越文化论丛》主编、重庆“说文社”理事长,主编《说文》学术月刊,执教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为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员、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并长期在中国银行任职。
卫聚贤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堪称当时学界一大怪才。有人以这样的文字描述他:著作等身,外貌却像商人;山西人,却创办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研究国故,思想却开放;外貌粗鲁,却写得一手精细文章;古史专家,却是商科学校出身;头衔是学者,却在银行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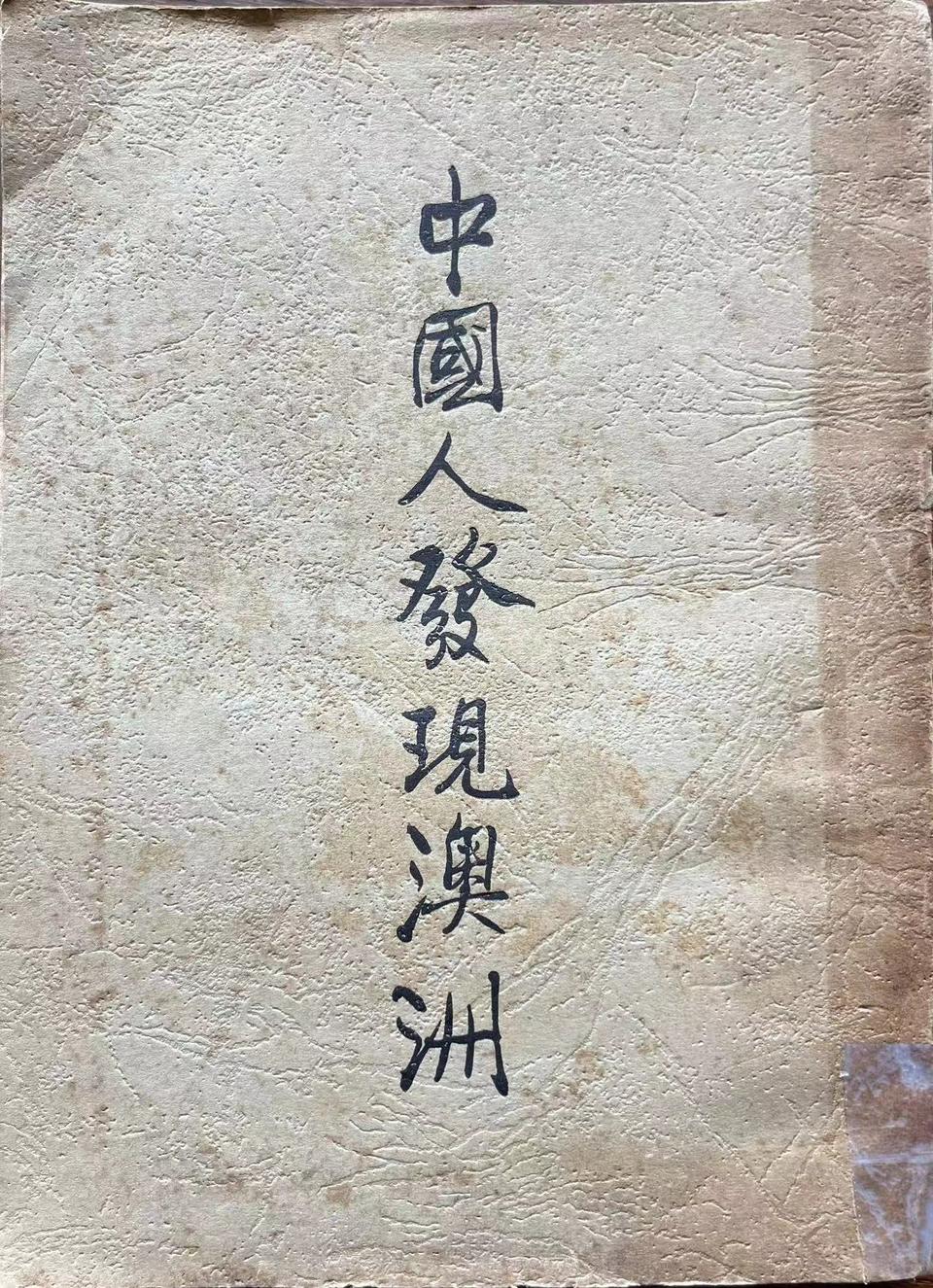
卫聚贤涉猎广泛,他是吴越文化研究的发端者,又是良渚文化的最初确认者,率先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著书立说剑走偏锋,既有《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这些鸿篇大论,又有《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澳洲》这样尖端难证的话题。难怪郭沫若也禁不住撰联调侃自己的好友,上联:大东家,大方家,法天法地,师古师今,难得一楼新宝贝;卫父子,卫娘子,聚民聚财,贤劳贤德,真成双料活神仙。
剑走偏锋看澳洲
1954年香港出版的《新希望》杂志,发表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华侨的信,标题是《谁先发现澳洲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澳洲华侨的一封信,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各种声音纷至沓来,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挂着著名学者、教授头衔的卫聚贤著作《中国人发现澳洲》。
该书序言开门见山:中国在北半球,澳洲在南半球,两地气候相同,中国人移居澳洲,或澳洲人移居中国,是很相宜的。中国在北太平洋,澳洲在南太平洋,中间又有南洋群岛联络,中国人到澳洲,或澳洲人到中国,是应有的事。至此,作者笔锋急转,抛出问题的症结:“中国的正史上没有记载中国人到达澳洲,也没有记载澳洲人到达中国。至于澳洲土人没有文学,当无记载可言。中国在考古上没有发现澳洲古物,而澳洲只在若干年前偶然发现一件中国玉雕寿星像,既非考古发掘所得,而又孤证难凭。在理论中,中国人发现澳洲,是可能的,但无证可凭,只好让1601年葡萄牙人到达澳洲后,为发现澳洲之开始。”
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之论据是:“空中生有的做法,没有一种直接的证据,而是从一百六七十种古书中,搜集材料,共分为三十章叙述,文约二十万字,插图共三十九。是从推断而出的。这对《中国人发现澳洲》虽属推论,但对中外交通史、南洋华侨史,以至古代中国人对世界观,很有参考之必要。”本书还有一个副题: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朱文鑫著《天文考古》(商务印书馆民国1933年出版),列有《春秋日食表》,将发生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0年至公元前481年之间的三十多次日食,逐一标注发生地。其中“南洋群岛”日全食两次,“中国以南”日环食一次,“菲律宾”日环食一次,“澳洲”和“澳洲南”日环食各一次。其他皆是发生在华夏大地,如黄河、长江流域,鲁国可以看到的有四次日食现象。
传《春秋》为孔子所作,实为鲁国史官逐年记录,属于官方修订的鲁国历史书籍。鲁国史官为什么要记载很多次在鲁国看不见的日食呢?卫聚贤推测,日食是各地常见的天文现象,何以《春秋》中没有记载欧洲、美洲、非洲的日食,而独记澳洲,极有可能是鲁国人到达过这些地区。到过这些地区的鲁国人回来之后,向当地人叙述看见日食的状况,鲁国的史官就记载到了史书里。以《春秋》所列的“日食表”,作为中国人到澳洲之证据,可信的程度不能说一点没有。
卫聚贤考证,《庄子》的山木篇有确切记载,鲁哀公曾于春秋末年、公元前479年左右,被一位叫做市南宜僚的楚国人所劝去往越南,“与道相辅而成”。《庄子》记:“市南宜僚见鲁侯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鲁哀公听了市南宜僚的话之后说:“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南越,当时而言是指楚国之南的越南,建德应该是越南的都城,这里有江有山,大概是在靠近今我国广西一带的腹地。
当然,古代有“百越”之说,今浙江为越,福建为闽越,广东为南越,广西为西越,越南的完整名称当为骆越。的确难以确定鲁哀公被邀去的是哪个方位的“越”,卫聚贤以各种史料作旁证,最后的结语也只能是“推论“而已。
卫聚贤“推演”飞来器、袋鼠
澳洲土著人使用了一种飞刀,叫飞来器,开始是作为猎杀飞禽走兽而用,后来兼具防卫与作战功能。澳洲土著人把这种飞刀叫做“回力角”,也叫“乌美拉”。它用坚硬的槐木,经过长时间精心打磨而成,被誉为物理性能超强、科技含量很高的原始武器。这种飞来器是澳洲土著人专用,每一个旋转的回力角,能够击落四五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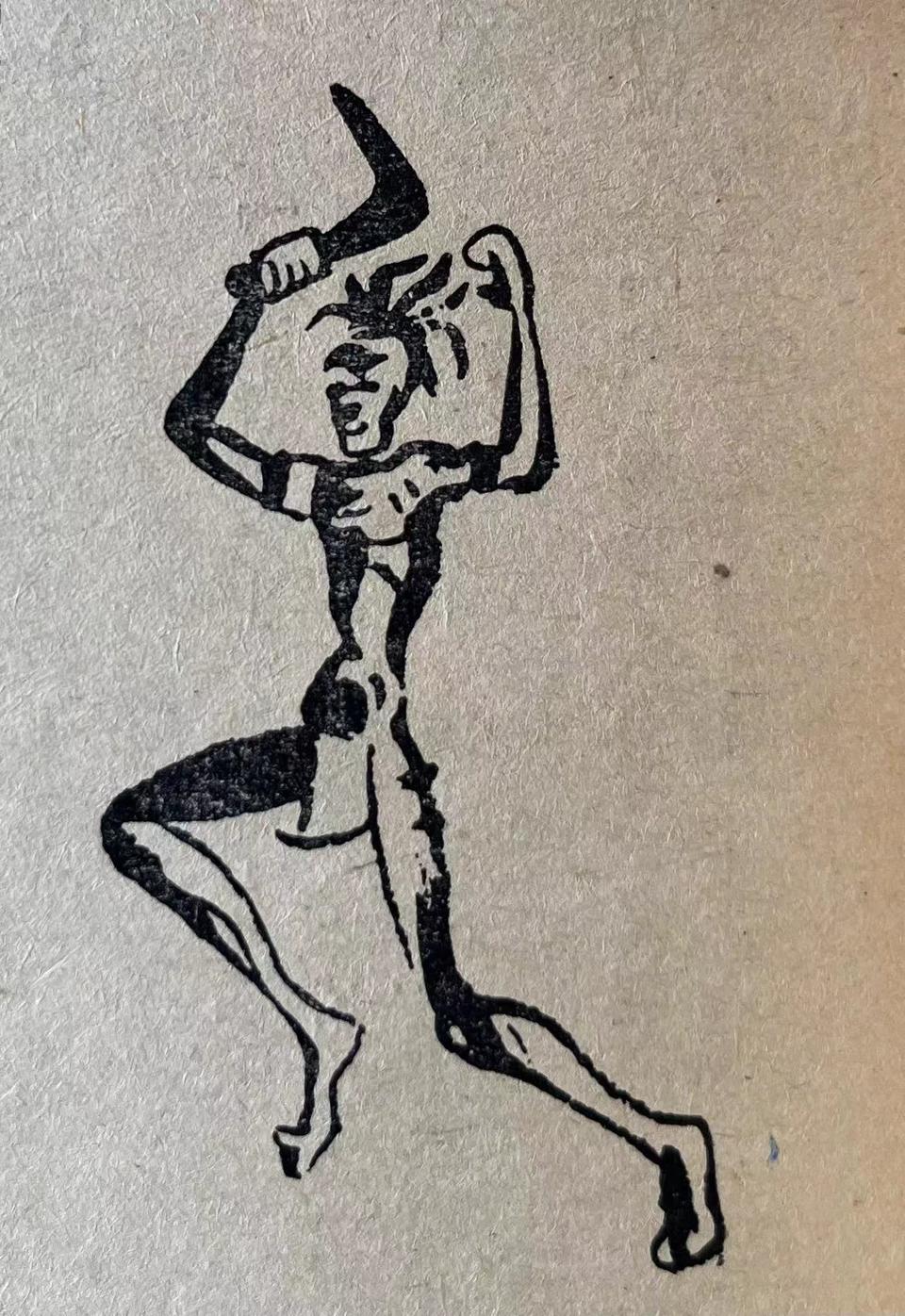

卫聚贤以中国古代兵器的弋来做推演,两者的形状与功能十分相近,甚至有同宗同根同源之缘。《说文解字》说:“弋,橛也”。弋即橛,像弋形,明证弋像极了飞来器。澳洲人使用飞来器,是1689年英国人到达澳洲之后看见的,但中国人看到澳洲人玩飞来器要比英国人早了两千年。《山海经·海外南经》说:“鑿齿持盾,一曰戈”。根据后人研究分析,此“一曰戈”乃“一曰弋”之笔误。其实,《山海经》的记载也印证了飞来器不是澳洲的土产,而是源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古老国度先人的发明与创造。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八千年前住在尼罗河谷的原始人,也使用飞旋器,因此很多专家认为,澳洲土著人仍在继续使用的飞来器可能是舶来品,或来自古老的埃及、印度,或来自中国。而科学实验证明,澳洲的飞来器与中国的弋,“血型”更加相近,存在基因同属关系。
澳洲的代表性动物毫无疑问是蹦蹦跳跳的袋鼠,其图案被用在了国徽上。袋鼠的形状非常奇特,似鼠似兔,前高后低,前腿短后腿长,身躯大小不一。据说,有袋类动物约有三百种,巨型袋鼠跟骡马差不多,小的比平常见到的老鼠还小。卫聚贤考证认为,中国古代的“邛邛巨虚”是澳洲的大袋鼠,“蹙”就是小袋鼠。
他引用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一段:“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丈,止则蹶然仆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漠中。予奉使日,捕的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蹙兔也,亦曰邛邛巨虚也。“沈括描述的这种所谓邛邛巨虚,的确与澳洲的袋鼠十分相像,但沈括没有说到袋鼠的唯一标志——袋。没有袋子了,何来袋鼠之说?而且袋鼠性情暴躁,一般人很难接近,更不用说随意捕杀了。
可能卫聚贤也觉得无法认定契丹“跳兔”就是澳洲之袋鼠,虽然他广征博引,最后的结论还是:“袋鼠原非中国有,中国人没有看见过。初见此物,以为它是新种——马父驴母,或牛父马母而产生的新种——这当然是乱猜,但我们可以从古人认为是新种这一点,知道袋鼠非中国物。”
中国人最早何时到达澳洲
卫聚贤是一位思想开放、具有大开大合思维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对历史问题的推演,始于史料,寄希望于新的考古发现,具有传统史家无可逾越的前瞻性与想象力。这也是《中国人发现澳洲》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中国人发现澳洲》一书还有一个副题: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不难看出卫聚贤进行此题研究的主旨或者中心思想,不是就事论事,以此确定“中国人发现澳洲”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历史研究是允许假设的,假设的课题需要大量的新材料予以证明其合理性。很显然从1960年《中国人发现澳洲》一书出版,至今已过六十多年,新的历史材料与考古新证仍然没有出现,这还是一道待解的题。
有科学家揣测,在远古时代,澳洲是与欧亚大陆,甚至与非洲、南极洲、美洲连在一起,中间并无海洋阻隔。约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年以前,因为地形发生巨大变化,澳洲与大陆分开了,而且越分越远,成为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大岛。该岛面积辽阔,周围都是海洋,与世界两个文化中心的亚洲和欧洲,距离甚远,形成了隔绝状态。有科学家早预想到地球的南方会有一大片陆地,只是没有得到证明,而暂时称为“南方未曾确认的大地”。元代时期曾经到过中国的探险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到,中国人早知道南方有一片大陆,但不知其详。亦有推测,明代航海家郑和可能在一次风暴潮的影响下漂流到澳洲,只是因为当时并不知晓此地为何地,而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航海日志中。
中国人成批前往澳洲始于1848年,共有成年劳工100人和童工21名,都是“契约劳工”。到黄金发现之前,已经有了五千多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澳洲南威尔士发现黄金矿,需要大量劳动力,英国早年虽然以大批罪犯流放澳洲,但数目终究有限。十八世纪末,大批华工不远万里到达美洲的秘鲁、古巴等地,因此澳洲也有人提出招募华工前来开采金矿。当地的一位矿主认为:“中国人极愿向外移殖。在亚洲人中,中国人最为勤劳,并富于技巧。他们不但可以供应英国在澳洲垦地劳工的缺乏,并可在一世纪之内,把这片广漠的荒野,化作一个茂盛的田园。”其后虽有大批量华工进入,并未准确统计。但有一种记载能够佐证华工基本数目,就是从1856年7月到次年6月底,一整年的时间,仅从墨尔本运往中国的黄金就达到了11万6千9百盎司,时值50万英镑。没有足够的人力是挖不出这些黄金的。淘金是一阵狂潮,发现矿藏,人潮涌般而来,一旦矿藏没落,采矿人瞬间散去。此间到底有多少华工说法不一,初步估计差不多10万左右。随着黄金矿藏枯竭,华工的数量锐减,到1901年澳洲正式建立联邦时,全澳350万人中,取得身份的华人不过万余,占比很小。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许志杰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