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镇菜市场摆摊卖杂货的十八年里,陈慧相逢过无数小人物的命运,这些人里有她的乡邻,常来的顾客,也有隔壁摊位卖鱼、卖肉、修鞋、换锅底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在新书《在菜场,在人间》里,陈慧以自己生活工作的菜市场为主题,记录了摆摊至今的十八年里遇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一个个平凡生命的庄严与贵重,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热热闹闹、挨挨挤挤,以及贴地而活的生之乐趣。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展开,其实也是一部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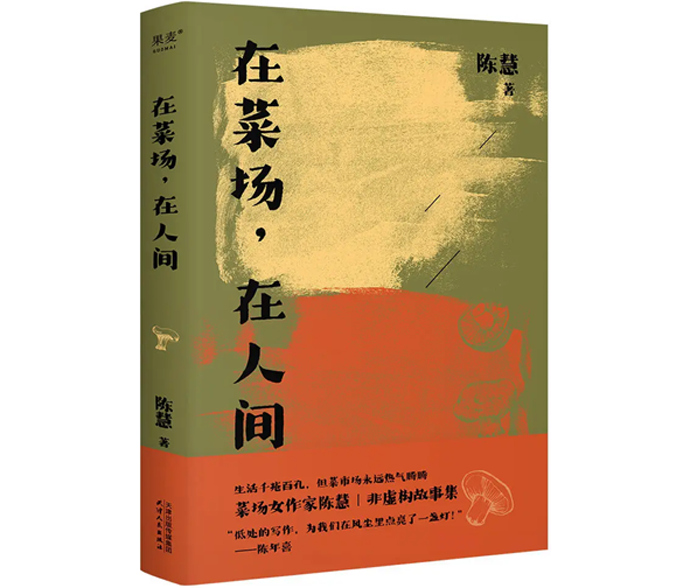
《在菜场,在人间》
陈慧 著
果麦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菜市忙人
文|陈慧
我摆摊的十字路口往左边拐进五十米,有一间很逼仄的楼梯间。以前是卖面条的阿权哥租着,放一张课桌,一只方凳,一块案板,再加上两只大肚子的竹篓筐,人在屋里头转个身就得小心翼翼了。
阿权哥租那楼梯间的几年里,我的小摊就摆在他的门边上,有时他出去办点事,我就主动帮着他照管一会儿生意。有时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他便赶紧顺一顺东西,让我把小摊子推进屋里避一避。他的租房合同到了期,力劝我租下楼梯间,说有个固定的地方,至少不必天天挨风吹日晒的苦了。
我没有接受阿权哥的建议,继续做我的露天“游民”,相对于从早到晚守着一间小店的寸步不能移,我还是更喜欢来去自由的灵活性。再则,楼梯间的面积实在太小了,仅是几平方米的不规则形,未来完全没有扩大经营的可能性。
阿权哥撤走后,那楼梯间一直无人垂青。七八月份,半山村一个烫杂粮煎饼的女人试租了一礼拜,眼见没什么生意,立刻撒手不干了。元旦前,有个胖乎乎的安徽人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开了一家芝麻大饼店。然而,两个月还没撑足呢,他便拍拍屁股走人了。腊月底,一个卖低廉服装的男人租了个短期,突击了十天左右的业绩,年后再没露面,房主不得不又在卷帘门上挂上了“吉房出租”的牌子。
牌子挂了好久,“吉房出租”四个红字都被太阳晒褪了色,总算来了租客。一个绍兴口音的老太太,高高大大,花白的齐耳短发,长条脸,一嘴的牙七零八落,看样子得七十好几了。
这个老太太原本是误打误撞摸来我们镇的。这地方过清明节、夏至、七月半、冬至以及年三十都要敬神祭祖,俗称“做拜拜”。老太太装在一辆四轮小拉车里沿街兜售的就是做拜拜时需焚烧的“经佛”和“元宝”。经佛其实就是印着莲花图案的、比巴掌大一点的长方形黄纸,名堂却是不少,我知晓的只六七种:四四佛、六六佛、八八佛、心经、弥陀经、观音经……各有各的价格,一扎几块钱到几十块不等。
老太太到小镇试了一回水,大概尝到些甜头,于是毫不犹豫地找到房东,当场拍板租下了那楼梯间。屋里起初还是空荡荡的,她下午匆匆乘公交返回几十公里外的家,第二天大清早又拖着沉甸甸的小拉车急急赶来。车马劳顿了几天,她开始一点点地添置物件,先是桌子板凳儿,接着是锅碗瓢盆儿系列,最后连床都搬进来了。老式木床窄窄的,一头顶着楼梯间的里墙,一头直逼到卷帘门下。卷帘门一旦推上,屋内的一切就统统暴露在了大众面前。她往床头上挂了一块花里胡哨的旧被面作为遮挡,好歹在众目睽睽之下拦出了个不怎么私密的私密小空间。
周围的一些居民见“新进成员”摆出了居家过日子的架势来,忍不住偷偷议论。这个说,一大把年纪了,不在自己家颐养天年,难不成还想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个讲,年轻人来开店都维持不下去,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还能搞出个啥名堂来?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地去和她搭讪,拐弯抹角地问了她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果然七十有三!一家五口人,儿子媳妇厂里上班,孙子读大学,老伴健在。我不解地问:“大妈,老伴老伴,不就图个老来做伴嘛,你把大伯留在家里,自己跑出来单住,他就没意见吗?”她瘪了瘪嘴,满不在乎地一挥手:“啊呦!这样多好,大家都清净!”
她的个性大大咧咧,喉咙音又响,有事没事爱站在店门外和路过的人套近乎,笑盈盈地搬出椅子请人家“歇歇脚”。亲和力十足的几波操作下来,她就顺利地收获了一些客户。然而,经佛这种东西需求量很少,除非派特殊用场,否则,不年不节的,哪有多少人来买呢?
头一个月,她盘了账,表情讪讪的,说房租都没赚到手。我们几个听到的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搭她的茬。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来菜市场的人一年比一年少,生意确实越来越不好做,她亏钱是意料之中的事。假如她租房时像之前的那几个人一样,只付少量租金,那她的损失顶多不过千元,可她签了铁板钉钉的合约,一次性付尽了整年的房租,即使她现在萌生了退意,拿出去的钱也讨不回来了。所以,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继续把经佛店往前熬;二,贴一张“旺铺转让”的条子,骗接盘侠上钩。
老太太既没有选一,也没有选二,她自行开辟了一个三。她把摊开的经佛一一叠进纸箱子里,只占了门边很小的一个位置,腾出来的地方放上了她从赶早市的本地菜农手里批发的应季蔬菜。她前后卖过新鲜的豌豆荚、毛笋、大豆、玉米、小青菜、水蜜桃、南瓜、茭白、鞭笋、洋芋、西瓜、花生、栗子、柿子等等。
她卖什么,屋里的地上就晾满了什么,人走进走出,不得不踮着脚尖,像是在跳芭蕾。她只卖不买,什么没卖掉,她的胃就顺理成章地消灭什么。变了颜色的大豆瓣,干巴巴的玉米和厚皮的老南瓜……她都在电饭锅里煮得烂烂的,一碗一碗地吃下去。是饭,也是菜,饭菜不分家。
也有不能及时解决了的东西,比如在水里泡青了的茭白和霉过了头的苋菜咕。一般的生意人早就扔掉了,她才不!细致地刨去茭白的青皮,拿盐腌好塞进玻璃瓶里,又是一样省事的下饭菜。“苋菜咕”是一种霉变食物,周作人先生曾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算是经典的浙江味道。青苋菜去叶,留梗,切成寸许泡入水中,一天一夜后捞出,沥干盛进坛子里,撒几颗粗盐粒,密封发酵数日,苋菜梗外壳硬度不变,内里却已酥烂。取一碗,浇一勺菜油上锅蒸透,吃起来有点像吸果冻,咕咕有声,据此得名“苋菜咕”。苋菜咕这东西很个性,爱它的人,觉得香气扑鼻,趋之若鹜;厌恶它的人,忍受不了它的异臭,避之不及。
老太太的苋菜咕是“升级产品”,第一步是出售成捆的苋菜梗,苋菜梗蔫了,没形了,她就自己动手制作苋菜咕。气温高时,苋菜咕易发生质变。为了确保姣好的品相,她又斥资九百元购买了一只小冰箱,专门保存成品或半成品的苋菜咕。尽管冰箱的门严丝密合,屋门也是从天蒙蒙亮大敞到天黑黢黢,但爆发力超强的苋菜咕气味还是彪悍地占领了她那狭小的楼梯间,并冲出门外,一再向四方蔓延。说实话,我闻到那味儿只想吐口水,可她反而又被那味儿激出了赚钱的灵感。
下午三点后,她在门口支起煤气灶,架好油锅,不慌不忙地炸起臭豆腐——老豆腐切成小块在苋菜咕浓汁里浸个透,就是正宗臭豆腐了。一只白色的泡沫盒里装八块,搭两勺辣椒大蒜水,售价五元。
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一溜儿人家,要数她顶顶忙碌。忙着拦住挑大口袋的山民进货,忙着招揽各路买主,忙着处理即将过时的产品,早忙晚忙,忙得她吃饭也没个准点儿。上午十点,她捧着碗坐在床上吧唧吧唧地吃东西。我人立在路上,脖子伸进门里,故意问她:“大妈,你吃的是早饭,还是中饭?”
她嗤嗤一笑,很爽利地回了我三个字:“早——中——饭。”
她不但卖菜,还卖房——不是真卖房,而是卖掉房子几小时的使用权。菜市场有明确的管理条例,外来人员不允许在路边上随意设摊。一些拉着独样货品远道赶来,存心做短线的贩子怎甘心跑个空趟呢?就在他们抓耳挠腮左右为难之际,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马上把她待售的几样蔬菜移去隔壁邻居的屋檐下,朝他们招手了:“来来来,我给你们腾了地儿!”
腾出的地儿半天起码换五十元。这样轻松的“二房东”,她一个月总能做两三次。
她再没发出过“房租也扳不转”的抱怨了,之前一心认定她要落败的人也不知不觉地向她投去了迥然不同的眼神——哟!这老太太有两下子嘛!
(本文摘选自《在菜场,在人间》,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陈慧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