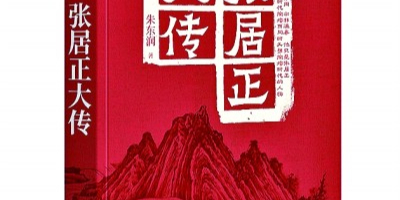
1943年8月,朱东润在重庆寓所写毕《张居正大传》的序言,将书稿交付开明书店,由开明书店于1944年出版,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并请作者撰写了《三版后记》,这是朱东润生前对《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一次修订。《张居正大传》出版的八十年间,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中口耳相传,被列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张居正大传》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条新路,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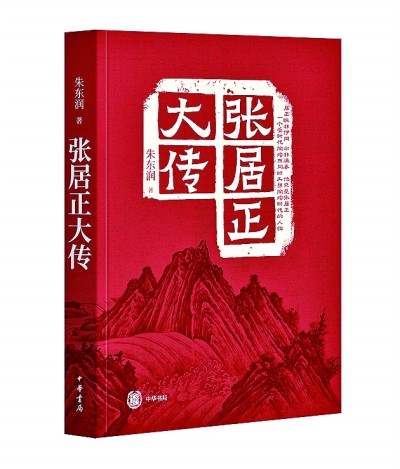
《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 著 中华书局
“大传”之为体
1941年,朱东润所在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置“传记研究”课程,于是有教师开设韩柳文专题。但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样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朱东润自传》)这引起了他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思考。
朱东润早年留学英伦,对欧洲传记,特别是英国作家的传记,下过一番功夫,对西方的传记理论、传记作品和传记作家都非常熟悉。回国任教后,他又多方搜集资料,写成十余万字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作了一番梳理。在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他有着比前人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学养。在他看来,从秦汉的史传,魏晋的碑志到唐宋的墓铭、行状,明清的文集、年谱,乃至西方传记学者和作家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信,中外传记文学的体裁各有优势,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于是他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替中国的传记文学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张居正大传·序言》)。
目标既定,就要考虑写法的问题。朱东润认为,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可谓家喻户晓,但“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言简意赅,“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但又失之太简;最后,朱东润决定做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这几条原则看似平常,实际上对写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朱东润将其命名为“大传”,对此他也作了一番解释:“‘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在创作《张居正大传》之前,朱东润曾作《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对史传的写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传统史传对同一事同一人的记载,常有所谓“互见”的笔法,读者往往在某人的传记中得到一种印象,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甚至在史书的幽微隐晦之处,又会发现这个人的另一面。显然,朱东润所创立的“大传”,既沿袭了传统史传“解说经义”的宗旨,又有不忌烦琐、叙事完整生动的文学特色,并非传统史传一字含褒贬的“春秋笔法”,而是一种融汇中西传记传统的新尝试。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所谓“传记”,似乎本该如此,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这还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本书的开创之功,正在于此。
“张居正”之为题
体裁既经确定,接下来便要选择一位传主。朱东润认为,对一位优秀的传记文学家来说,无论人物大小,任何人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部优良的著作,但一个平常的人物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还是要从伟大人物着眼。传主的时代不能太远或太近,太远了对读者来说有隔膜,太近了则会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
除此之外,时代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朱东润创作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亲见战火蔓延、民生困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身在后方,又对当时政府公文政治的作风深有体会,也深为不满,他在1941年重庆出版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讨论唯名主义的文章,意在批评当时政府只重言论、公文而不顾实情的作风。有感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作者最终选择了张居正,对此,他解释说:“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的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把张居正作为一个“救国救民的范本”来写,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上,《明史纪事本末》中即对张居正有“救时宰相”的评价,他对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写作的“出”与“入”
20世纪30年代,朱东润已经对历代史传做过系统的研究,决定创作本书之后,他又查阅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张文忠公全集》等史料,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实际写作中,他有意避免唐宋墓志那种“谀墓”的习气,要求自己言必有据。今天看来,最终问世的作品也达到了他自己的期望,对传主既不一味颂扬,也不专事批评。但作者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加之熟悉史实,对张居正的言行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因而行文中常有感情流露。例如,讲到张居正因关照徐阶后人而招致高拱及其门人的攻击,朱东润写道:“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显然,作者认为张居正此举是出于道义和感情,而不是更复杂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时常抽离历史语境,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分析局势。比如万历即位之初,作者对张居正与慈圣皇太后、神宗和冯保的关系做了一番分析,使读者对张居正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有大体了解;再如对争议颇多的“夺情”一事,作者援引众多史料,从皇帝的态度、百官的态度到张居正的个人感情、现实考量等诸多方面,条分缕析,说明在这样一场牵涉众多的巨大矛盾中,是不同立场的人物出于各自目的所作的选择,共同造成了最后的局面,为张居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作者也不是一味同情和颂扬,对传主的某些缺点乃至污点,只要是史有实据的(比如张居正的专权、贪污),也并不避讳。
传记是写人记事之作,用朱东润的话来说:“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但我国传统的史传文学都是以文言写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付诸笔下的口语变成了文言,人物说话都是“之乎者也”,读起来颇不生动。朱东润又援《史记》改写《尚书》之例,认为史籍中的文言对话是可以转写的。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转写的结果应当是明代人的口语而非现代人的口语,于是他以张居正奏疏中保留的对话为据,对史料中的文言进行了改写,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诸如“说与皇帝知道”“与先生酒饭吃”这样生动的口语。翻阅明代的官方史料和私人书牍,不难发现,这样的改写工作是颇费工夫的,作者必须精通文言,又对白话运用纯熟,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古”与“今”的分寸,写出现代人能看懂的“明代人的话”。
《张居正大传》既能借助大量材料还原历史,让读者身临其境,又能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剖析人物事件,窥见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当时”与“今日”之间自由出入而游刃有余,是这部传记的高明之处。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李若彬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