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柏林动物园海象居住的水池边,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在一只死去海象肚子里找到的所有物品,里面有:
一枚粉色的打火机;一只手镯(大概是银的);一只安抚奶嘴;一根发卡;一把儿童水枪;一个罗盘;一个婴儿鞋,还有墨镜,还有小项链,还有很多很多。
它们成为展品完全是出于偶然——不过是海象兴之所至的饮食习惯。面对这些被留下的琐碎物件们,我们忍不住想象的总是它们背后的故事,比如早已远去的物品主人,或者发生在那天的一场偶遇。博物馆里陈列的东西总是这样,留下来的只是失去那部分的纪念。
我们的老朋友,克罗地亚女巫杜布拉夫卡在新书《无条件投降博物馆》中,也讲述了一个关于失去和纪念的故事。生活的溃败被时间冲走,事物则被留下来,比人们更长久。当原本的生活被剥夺,还留在我们手中的那部分,包括一本相册,一件旧外套,包括所有的记忆,甚至我们自己,是不是都只能是一个纪念,一件博物馆展品而已?
书中共有七个章节,其中四章都是由带编号的叙事构成,长则数段,短则几行,剩下的章节则包含了日常生活中遗留下的清单、菜谱、日记、自传、档案、系列故事等等。也许破碎的生活只能用破碎的语言来讲述,当我们穿行在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文字中,往昔生活的真相也将在我们面前铺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选择了《无条件投降博物馆》中的部分展品,欢迎大家在其中寻找记忆。
到了第二天,你还能记起被弄丢的东西吗?
它们曾腼腆地,最后一次请求你(然而没有用)
让它们留在你身边。
可是掌管失去的天使,已经用翅膀轻轻一碰;
它们不再属于我们,而只是被强行留在这里。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第一件展品:装满苹果的箱子
她坐的是火车。从瓦尔纳到索菲亚,从索菲亚到德拉戈曼,那是她地理知识的边界,也是她即将穿越国境线的地方。就要进入南斯拉夫时,她突然害怕起来,或许是因为海关关员的黑胡子,或许是因为她此番离家的决绝。总之,她一边打开手提箱,一边在心里盘算,或许还有机会改变主意,或许还能回去,然而手提箱却从她手里滑走了,一些不起眼的行李从里面掉了出来。她记得那些在地上滚动的苹果(有很多很多很多苹果,我也不知道自己干吗带这么多)。她的记忆,停留在了滚动的苹果上。而且,仿佛是苹果,而不是她,替她做出了决定:就在她忙着把苹果都捡起来的时候,回去的火车开走了……

《乘火车去旅行》
很多事她都记不清了。在那遥远的1946年,她乘半空的火车,颠簸着穿过一片被蹂躏的国土(一切的一切都被毁了……)。她把地上的东西一件件放回手提箱里:她的乔其纱夏裙,雅致的丝绒鞋,她的书,她的软木塞高跟凉鞋,款式是巴黎时尚杂志最时兴的样式(那年冬天,黑海从某艘沉船上给瓦尔纳港冲来大量软木塞。转年夏天,瓦尔纳女孩们就都穿上了这种软木塞做的凉鞋,脚步轻软地踏在温热的鹅卵石上,所到之处都留下海水的气息。)。她把苹果放在了最上层。
她透过油腻的玻璃窗,希望能看到什么新东西,但一切都旧了,毁了,无望至极,接着,开始下雨了,黏腻的细雨飘飘洒洒,一连好几个小时,窗外迷蒙一片。她蜷缩起来,想着自己的未婚夫,一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南斯拉夫小伙子,一个她在瓦尔纳海滨步道上遇见的水手。她想象着两人未来的家,在心里第一百次重复着下车的站名,想象他的微笑会在车站等着她,在这模糊的未来所带来的微暖中,她睡着了。就那样几小时几小时地颠簸着,昏睡着,偶尔醒来吃几口苹果。
她唯一清晰记得的(我不知道这么多事里我为什么独独记得这一件。她说,重音放在这么多事上)只有一个老人(他有一张高贵的脸),老人在某一站进了她的车厢。她给他一个苹果,他拿出一把小折刀,熟练地给苹果削皮,把皮做成一朵玫瑰。
“给你,小女士。”他说。
(真是太神奇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玫瑰!)
她在自己念叨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一站下车,手里提着箱子。然而,站台上并没有人在等她,黏腻的细雨飘洒着,天已经黑了。
在那里,就在站台上,她用一块黑布,将自己的过去盖了起来。我只能偶尔从这块黑布上抽下一两根线。

《乘火车去旅行》
第二件展品:母亲的财富
书是母亲最大的财富,在这笔财富里,有一部分是她跟苹果一起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她来这儿以后陆续买的。
我的出生也有书为证,那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父亲没有读过它,但受到书名的蛊惑,认为很应景,就买下送给了刚生下我还在医院的母亲。
在战后普遍贫穷的年代,我们(除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外)有一句特别流行的口号,叫书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宣传口号称,知识就是力量、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民间俗语也有头脑领导力量,力量掀翻木桩之说,除此之外,一系列有关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如何对自己千锤百炼的故事,也说明了书的重要性,有些人好像一天到晚在读书,比如列宁;有些人借着月光也要读,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无足轻重的农民通过教育可以将自己改造成会说几国外语、精通钢琴演奏的学者,比如铁托。(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改革家的套路故事,在四十年后,当我们新的克罗地亚总统需要经营他的媒体形象时,还会再流行起来,他曾要求别人给他拍一张照片,照片上,他手拿小说,沉浸在阅读中。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约翰·艾文,真是太应景了!我一边看着这张令人作呕的摆拍照片,一边想起了另外一个艾文,艾文·斯通,他在我母亲的战后收藏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书店》
我母亲对书的热情是真挚的,并非由任何外力所驱使,这种热情也感染了我,于是她小小的收藏,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而由于这份收藏中,面向少儿的读物非常少,只有《帕街小英雄》和《赫拉皮克的小学徒》这种,我干脆很快读起了《卢克雷齐亚·波吉亚》(教皇的私生女)和厄普顿·辛克莱尔的《石油》。《石油》是母亲的收藏中较早的藏品。我记得是父亲1946年买的,当然还是因为书名应景,因为他当时的工作属于石油工业。厄普顿·辛克莱尔、艾文·斯通和西奥多·德莱塞是母亲最喜欢的三位美国作家。后来还出过一套电影书,有一本扉页上有一张《第一夫人》的剧照,于是斯通的《美国第一夫人》就在母亲的收藏中占据了永久的位置。
母亲馆藏中的书名对考据“一战”后期克罗地亚出版与翻译状况的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母亲有意识地陆续把战后文学市场上不多的出版物全都买下来了。
我们二人共同培养着阅读品味,为特里格维·古尔布兰森的《山里来的风》和《无处可逃》,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国王班底》,拉约斯·塞拉西的《死泉》,皮埃尔·拉穆尔的《红磨坊》,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瑞贝卡》,巴尔扎克的《小麻烦》,司汤达的《阿尔芒斯》,乔治·梅瑞狄斯的《自私的人》,克朗宁的《帽商的城堡》,马里沃的《玛丽安妮的一生》,左拉的《真理》,朱利安·格林的《列维坦》,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究竟孰优孰劣而争论不休。
1951年,母亲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梅兰克莎》,我想她并没有读过。她买这本书纯粹是因为她喜欢书名里带女人名字的书:《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魔女嘉莉》《阿尔芒斯》《瑞贝卡》《露西·克劳恩》……以女人的姓名为书名,说明她可以把自己的命运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进行联系,进行比较。有时她买书纯粹是喜欢书名,比如买莫泊桑的《像死亡一样坚强》。
尽管如此,有一本书,是我与母亲都共同挚爱的,那就是1954年出版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之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因为这本词典有很多很多图片。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绘本,没有电视、录像、电脑,书是唯一的娱乐。我饥渴、懵懂、塞满书籍、充满疑惑的儿童的大脑,会以通过母亲的小说学习生活的同样的热情,去探究《知识之书》中的那些鱼、花、蝴蝶、船、拉丁动植物名与名人介绍。
我们办了图书馆借阅卡,与管理员玛吉塔交上了朋友,她是个安静的人,酷爱阅读。玛吉塔荐书给我时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依据她自己的标准。于是,当其他孩子都在一窝蜂地读卡尔·麦时,她借给我的却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既然小说讲的是人变成昆虫的故事(玛吉塔想),那么小孩子肯定会感兴趣的!

《书店》
玛吉塔与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与我和母亲的读书会互不相干的阅读关系,我的阅读轨迹,在不知不觉间偏离了母亲,而这,天知道为什么,又是法国人的错。
在我小时候,有许多一听就着魔的词,其中有一个,在当时意义还很模糊,那就是索邦。起因是母亲曾提到某个人,说他在索邦大学念书,说的时候,好像这是什么奇迹,而成就这一奇迹的人,当得起最由衷的褒奖。当时我念索邦的方式长期是错的,我念成了索布朗。
另一个有魔力的词是梦莎。这个词听起来跟索邦一样叫人着迷,其意味也跟索邦一样模糊,但我对梦莎只在巴黎有的信念坚如磐石。但我不太确定什么地方有索邦。
于是,法语逐渐与梦莎、巴黎、索邦这些词汇联系在了一起。我曾经常把家里第一台收音机调到法语频道,开心地听里面汩汩流出的法语。我透过尼古拉·特斯拉的绿眼睛,乘着法语的河流,飘出总是下着煤灰的偏远小镇,进入一片广阔、未知的天地。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成为像儿童文学家米努·杜露哀一样出名的人。后来又立志成为弗朗索瓦丝·萨冈,为此还剪了个《你好,忧愁》中珍·茜宝的发型。
再后来,我又决定要找一个像让-保罗·萨特一样的男人,跟他一起住在一间梦莎里。那个梦莎里没有我母亲的位置。最后我放弃了梦莎与萨特,但法式诱惑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在属于我自己的图书收藏里,最初的几本书,都是法国文学。
第三件展品:玻璃球
我用手指划着玻璃球。我将它握在手里,像握一个苹果那样,用我的手心温暖冰凉的玻璃,用冰凉的玻璃冷却我的手心。玻璃球中,坐着我的母亲,她正在舔指尖上的雪花。
我透过玻璃看着她,想着她,试图感受内在的她。我将玻璃球倒过来,爱玛·包法利,玛琳·奥哈拉,苔丝,魔女嘉莉……她们的脸纷纷划过她的面容。她们的影子,根据某种神秘的亲疏关系,交织、缠绕、联系在一起。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与母亲相同的闪烁的眼睛,看到浆洗过的雪白围裙,看到发间的发卡,看到一种体态、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动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她们被同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粘力联结在一起,这力量来自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伯德家的苔丝》
我看着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见的这些女性都是内在的她,而与这些女性——与苔丝、玛琳、嘉莉、艾娃、安娜、爱玛、贝蒂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实,又不真实。我看见那两条法令纹,势不可挡地往下走,伤感地结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见她忍受命运时的愁眉苦脸,这命运开始得像小说一样,却没有结束得像小说一样,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让她老去,但再没有赋予她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隐约的渴望,只是一个玻璃球。我在她的脸上看见她曾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看见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或许坚强、浪漫、炽烈,却统统听命与导演的构思而结束了一生,只有她,继续过着模糊、苦涩的日子,她曾经对未来的期许有多光明,这日子就有多灰暗。
我翻转玻璃球,突然间,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这么的小,这么不自由,她一定很孤独,很冷……我将玻璃球握在手里,像握着一个苹果那样,我将它送到嘴边,用我的气息温暖它。母亲在水汽中消失了。
第四件展品:衰老的第一张快照
我记得小时候她有时会突然大笑起来。我总是惊讶地看着她,有点怕她这样笑会噎住。通常这时候,父亲都会摆摆手,撤离现场。而这又会让她笑得更厉害。这种笑,好像能让她暂时突破内心包裹着、监禁着她的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现在想来,这种迅速爆发、势不可挡的大笑,其实是她对自由的短暂的夺回(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是她再回到常态之前的一次深呼吸。
她笑完,就会像开始笑时一样突然停下来,擦擦眼睛,满足而深沉地叹一口气,再余音袅袅地轻笑几次,怕又笑起来似的,放松一下自己笑得发紧的下颌,确保自己完全镇静下来,然后抱着我说:我没事,别担心,狂笑结束了……
父亲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们与亲戚一道出去玩。她穿一身黑,半裙包得很紧,并不是适合踏青的服装。当我们在树林中安静地散步时,她突然深吸一口气,毫无理由地提起半裙跑了起来。她跑得很快、很轻盈,像小孩一样提着裙子。她跑得真快啊,她的身体向前舒展着,仿佛再过一秒、再踏出一步,她就能穿过那层缚住她的茧了。当最后气喘吁吁地停下时,她用手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动作,仿佛在擦眼泪(与她大笑过后一样),又仿佛挥挥手,在说对不起。
我想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开始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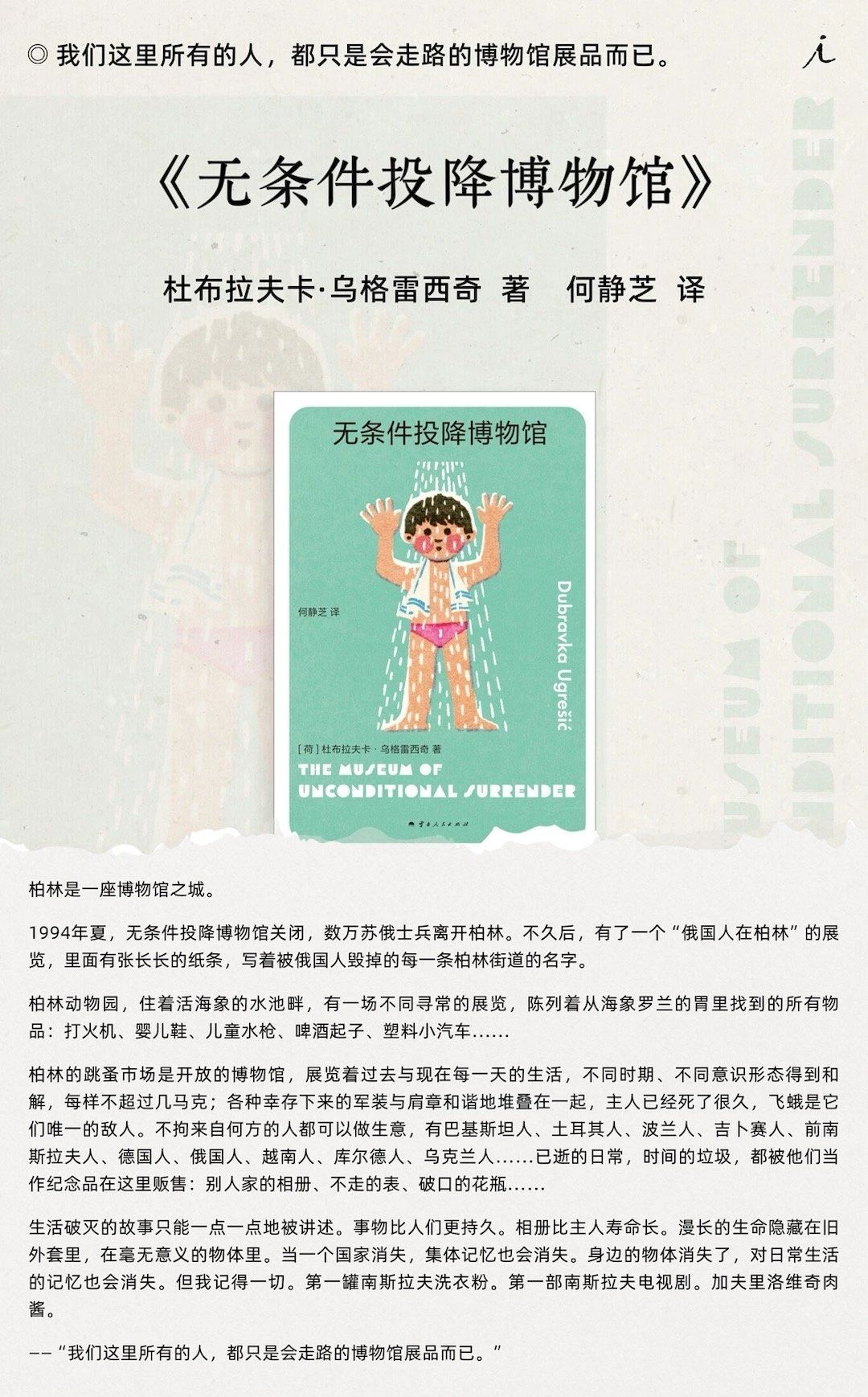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