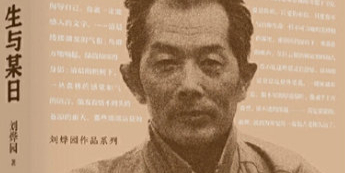
人与书的相遇总是那么奇妙,似乎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意味。
2023年岁末,我等来了刘烨园的《一生与某日》(冯秋子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置于案头断断续续地读,深夜时分认真咀嚼,竟产生相见恨晚的精神和鸣。
当我们谈论散文的时候,该谈些什么?刘烨园,这位并没有走远的思想者给了我们答案,最关键的是他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大陆。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恩·福瑟近日发表演讲时说:“说到散文体的部分,米哈伊尔·巴赫金是对的,他认为表达模式或者说讲述的行为包含着两种声音。简单来说,一个声音是那个说话的、写作的人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是这个写作者所描写的人物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往往互相融合,以至于难以分辨到底是谁的声音。”
两种声音互相融合,构成作品的双声部,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第一种声音,蒙尘藏垢的耳朵压根儿听不到。
读刘烨园,我有幸听到了第一种声音——作者内心深处真实的声音,也可以说是灵魂的喃喃自语,用张炜的话说:“他在用心灵的自语去启迪,寻找心与心的交谈。这一类声音正因为包含了意义,将来很难消逝。”
发出这种声音着实需要勇气,还需要健全的精神胃口,能够应对汹涌的舆论与各种误读,接得住暗箭与流弹,扛得住世俗的压力,安于一隅,独自消化,于苦难的土壤上开出花朵来。
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无比艰难的。
刘烨园是一个被忽略和被遗忘的艺术家,他的散文是他的精神自白书,敞开心扉痛陈生命的真相,掏心掏肺批判文学的弊病,那种赤胆忠诚和满腔热血让人感动,同时又无地自容。
冯秋子女士告诉我,《一生与某日》是从刘烨园生前出版的八部散文集中选出来的,还有两部待出版。他的散文或曰“往事与随想”,篇幅或长或短,却厚重大气,能够掂出思想的重量。
开篇序言《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揭示散文的真谛,也是文学的要义,“散文的复兴、发展,在于人的解放、心灵的真实,在于青年,在于‘散文’的批判。”可谓一语中的。
从人人都能写的“方便文体”到各种流派,再到思想者的精神自语,散文的敞开性和创造力日渐萎缩,这意味着藏在散文背后的那个“人”越来越小,几近模糊,甚至被牵拉、推扯、扭曲。因此,走出散文的困境,就是走出心灵的困境,就是放下自我的执念。
“散文不是亘古不变的日晷,是数不清的山,是千姿百态的树,是草原,是花群,是千百万人心中不同的夜空,是复活节岛的沉思,是现实的冷静、愤怒、调侃、享乐,是上溯地球形成的奇想、下至亿万年未来的推测……”我说不清什么是好散文,但我深谙散文忌讳什么,假嗓子、戴面具、眼泪染上醋味等。
刘烨园以“写出生而为人的文字”(出自冯秋子编后记)警示我们:先学做人,才能写好散文。好的散文应该与人格等量齐观。

“当生命真实地诉说时,月夜就是我们的节日。”真实是艺术家的命根子,谁也夺不走,却很难守得住,因为欲望的驱使。
以作家史铁生为例,他强调“写作之夜”和“回到零度”,可是他又不被作家的概念所束缚,“如果文学二字也已然被不断加固的某些界限所囚禁,我们毋宁只称其为:写作。”
他还说,“何妨就把文学与写作分开,文学留给作家,写作单让给一些不守规矩的寻觅者吧。”他看重的是自由本身,即心魂的飘荡与旅途。
刘烨园与他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自由的誓死捍卫,“保存创造力的唯一幸存方式,是再次意识到与所谓成功、荣誉并无关联的苦难与写作的‘零点状态’。”
刘烨园的反思自带“内宇宙”的忏悔与观照,是超越国界与地域的精神行走,关于文学、关于苦难等等。
刘烨园开诚布公,“你要钻探的是人性未卜的海底,是所谓时代变幻背后的共性……你的那支笔是深处的探测器和掘进机,你相信时间与漫长功力的公正。”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的精神之问,“人在哪儿能掩藏住自己?心的源流既然远远比地球要辽阔许多,我们又为什么在一间小屋里近视生命?堕落也应堕落得有气质……无奈就该忍受吗?谁说的?没有一次次的寻找怎么就知道它是无谓的?”
他让我这个身居陋室的写作者看到精神的辽阔与抵达,以及抵达过程中的探险和惊喜。
从山东半岛走出来的刘烨园,注定是一个“异质”而不竭的生命,恪守孤独的心灵吟唱,经常葆有心重如磐的精神负荷,孜孜探寻生命的诗核和本性,构成了他斑斓而浪漫的文学版图,纯粹的、朴素的、沉重的,也是没有尽头的“深渊写作”。
他倡导要把散文还给文学、还给艺术,提出生命感受性散文与生命精神性散文,前者浅显、狭隘、表面、琐屑、小情小调、小恩小怨,好像只是一些未经过咀嚼、熬炼的矿石型、素材型的东西,较为情绪化、一己化、流行化;后者则是博大的、深刻的、升华的、理性的、人的(人类的)、形而上的,就像苦难经历和苦难意识绝对是两码事一样。
当然,这两种散文并非对立面,而是强调散文的可能性和成长性,并寄予年轻人以厚望。
让我们记住他的恳切忠告吧,“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孤单,而是孤独。它是优秀的标志和家园,犹如被污染的都市稀有的一角晴朗。”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钟倩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