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空恋旅人》
“人会离开如宴席,但从来没有书走开这种事,只有人合上它抛开它遗忘它。”
很少能见到像唐诺这般恳切地爱书、读书的人,他这样描写那些值得一生携带的好书:“你才刚触及、还无法恰当表述的东西,却发现它早以某种美妙的、也更完整的方式帮你讲出来,仿佛等着你来。”
阅读《求剑》也有这种感觉,对人生、书籍、创作的大量精微洞察被唐诺以准确而美妙的文字完好塑出,令人一边读一边慨叹,觉得熟悉又新奇,仿佛有人帮我们照出书中洞天的同时,也照进生命深处,无形之中将我们的精神照亮。
《求剑》由唐诺的声音连成,也时刻回响着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屠格涅夫、伍尔夫、昆德拉、张爱玲的声音;随着年岁的增加,唐诺读书的眼睛更加清明,“能更精细地分辨,更知道如何读所谓的‘字里行间’、那些比文字更稠密的东西”——而借助唐诺的声音和眼睛,借助他的博学和慎思,我们也得以更明了地将自己的经验、所学所知、思维和生命与书写者的文字往复衔接。
年纪·暂时按下不表的死亡
还记得昆德拉那番有关人寿长度和人生命构成紧密关系的精彩发言吗?人知道自己“只能”活八十年和他“只能”活一百六十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平均生命大约有八十岁。大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想象、规划他的一生。我刚刚说的这事,众人皆知,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分配到多少年,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数据,或是一个外部的特征(像是鼻子的大小,或是眼睛的颜色),这数字其实就是人的定义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家伙可以使出浑身解数,活到我们两倍的时间(也就是说,一百六十年),那么,这家伙跟我们就不会属于同一个物种。
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东西跟我们会是一样的,爱情不同,抱负不同,感觉不同,乡愁不同,什么都不同。假使一个流亡者,在外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回到故乡,而他眼前还有一百年可活,那他根本就不会感受到属于伟大回归的那种激动,说不定对他而言,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回归,只能说是他生命的漫漫历程之中,诸多曲折绕行里的一次迂回而已”。昆德拉带着点忘情地滔滔讲下去,反复用自己最魂萦梦系、最日日周旋已生根成为他生命主体成分的那几样东西来说(感情、爱情、性爱、故国故土。可见他仔仔细细想了、检视了),而他的悍厉结语仍是,能多活一倍时间的人,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甚至不该同属同一个物种。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从四十岁延长到八十岁,医学其实已完成过此事一次了,轻悄悄把全地球上的人彻底更换过了,成为完完全全、不属于同一物种的人?——这样有点惊悚的想法我并不讨厌不排斥,还有点欢迎,这使我再想那些人只敢认为自己活四十、五十岁的往昔时代,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书,那时候的思维和主张,变得更复杂些也更仔细些并同情些,至少我自知多了前所未有的警觉。
像孔子据说活过了七十岁,但他想必不敢这么准备这么规划人生吧,一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活过了一百岁,可是他七八十岁当时就以为自己随时可死,不再做大研究大理论因为没时间了。孔子的人生大梦,是盛装在小很多、迫促很多的生命容器里,他的忧烦,他的平静和心急,他对世界、对人的判断和期待,都在这样更受限的前提之上发生并构成,只是死亡这回蹒跚而行,甚至像博尔赫斯的长寿老妈妈那样,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有趣老太太,每天早上醒来总这么问,这里是哪里?我怎么还没死?

《正常人》
多出来四十年长不长?这取决于我们想做的,以及应该要做的事多寡不好说准。对昆德拉,这八十年的、已被医学加长过的人寿仍如他说的是“太短的人生”,太多事都见头不见尾无法做成;可对绝大多数没什么非做不可,并且活于有退休制度(从法令规范到内化于心)的人,尽管也泰半同意这是长长益善的人生,却已明显出现时间太多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迹象这没错吧。或者说,我们已“享受”惯了这加长型的人生,已视之为理所当然不再心存感念,倒是一样一样开始察觉它的种种不舒服及其成本、代价。死亡被推远了,但也许因为没多少东西遮挡它或让我们忙碌分心(“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死亡看起来似乎更清晰更巨大了,事情因此变得有点奇妙起来,人怕死却又仿佛生无可恋,人使出浑身解数让死亡慢一点杀死我们,并同时使出浑身解数来杀死这些漫漫长日也似的时间。
在死亡和犹活着的我们之间,若没有足够有意思、有意义的事物挡中间,尤其人若还有过多的医学常识(正确的、不正确的),人的确很容易掉入所谓的“死刑犯处境”——判决定谳,数日子活着,时间的答有声,恐惧填空般伸了进来,生根而且一天天愈长愈大,这是人性,并非懦怯,并不可笑。
所以昆德拉的确是敏锐的,这不仅仅是时间加长而已,这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从而也改变了——整个人类世界—从自然环境到社会建构都相应起了变化并要求配合调整,也逐渐一样一样触及了各种极限。这已是当代生活的基本常识了,人可以活得更长已不是福音,倒愈来愈像是乌云罩顶大难将至的讯息,人也普遍开始切身有感的、有种种现实具体理由的(但不必非说得通)憎恶老人,这里面藏放着最后一句话:“你们怎么还不(去)死。”
不好直言,这有着人教养的、人道规范的约束,但也因为人其实都知道自己一样会老、会死(或更糟,不老但一样死),会轮到你的,这话也必将自噬地回头找到你。个体最善和集体最善的分离、背反严重地加深事情难度,难到就是矛盾—这正是奥尔森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整整半个世纪前所揭示的“人性”,让人看着极不舒服但难以驳斥。奥尔森指出,对个人最为有利的始终是,所有人都受到集体的规范,只有我一个人例外、豁免;而人也的确不断寻求自身的特例化、豁免化(政治里、商场中,以及每一生活现场),这不只人性,甚至是高度理性的。
所以,大家都依照交通规则好好开车,我一个人任意变换车道,开上路肩、抢黄灯闯红灯,这是最快到达目的地的方式;所有人都在七十岁,乃至六十岁前死去,独独我一个人活下来,这样就没长照的问题、没国家财政破产和地球承受极限的种种几近无解问题。布洛克在他最后一部马修·斯卡德小说《一滴烈酒》书里告诉我们纽约有如此人性的一种祷辞:“主啊,请让我贞洁不受诱惑,但不是现在。”“主啊,请让我平静地死去,但不是现在。”

《书店》
阅读·结论难免荒唐,所以何妨先盖住它不读
这怎么办好呢?那就试着把总有点荒唐的结论先盖起来吧。这是我近十年来阅读经常会做的事,索性不去读书的最后一章,更多是以一种超级轻松的、“这下我看你怎么收拾”的莞尔态度读它,这有着屡屡让我惊异的极好效果——明白而立即地,我发现很多书因此“活过来了”,很多原来让你很生气的书写者不再那么令人生气甚至开始有点佩服他(之前阅读时你只想逐字逐句驳斥他、挑他毛病,阅读无聊到像是寻仇),也因此,忽然冒出来一堆又可以读、该读的书,世界重新装满,而且空气通畅清新如起风,有一部分的自己也像恢复成年轻时候。
这么读似乎是聪明的,耳聪目明。
如果不只为着结论,那之前厚厚的这一沓话语就不是附属的、鹰架般只用来支撑、用后即弃的乏味证明过程了。书里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该用同样的态度来读它,价值由它的内容决定。你花四百块钱台币买的是一整本书,三十万字,估算多达两三万句话甚至更多,你不是只买了最后一句话。
会想要这么读也是因为自省,仔细想想,我自己的书写不也是这样?且愈来愈这样?怎么可以苛求别人非做成你做不到的事呢?——年轻时爱写结尾、总急着写结尾还很丢人会感动于自己写的结尾(经此,仿佛做了一番表态,一个有认真想过、有依据的决定,可以和世界更始也似的开始发展一个全新的、如此独特的亲密关系),但现在,几乎每一篇文字我都不晓得该如何较恰当地结束它,我只能松开手让文字“停住”。结个尾都如此不容易了,何况提出结论。
由此,我也慢慢知道了,原来所谓的曲终奏雅(意即一种万用的、约定的、“借来”的结束形式)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可以成立——千篇一律之所以无妨,当然其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实质,这是对人的体贴,甚至只是礼貌,用一个较赏心悦目的、乃至于有抚慰舒缓人心效果的方式,要的只是个结束,在应该要结束了却又很难结束时顺利结束,好放大家可以(暂时)安心离开。这是一种不必下结论的结束方式。

《正常人》
博尔赫斯曾这么揭秘地讲述自己的书写,说他总是像个站在船头甲板上的水手,远远看到有个岛,但先只能够看见岛的头尾两端,并不知道岛上(即中间)是什么,住着什么样的人、过什么生活、生养哪些品类的鸟兽虫鱼、有过什么故事等等,书写就是这中间部分的不断靠近和揭露。这样,博尔赫斯甚至把书的结束部分设定化了、前提化了,和书的开头并置并一起发生,发生在书写正式展开之前;也就是说,书写真正投注心力拼搏的是中间这里,不断发现并丰富起来的是这里,书写者最有把握的也通常是这里,所以啊,阅读者不看这里看哪里?
恰当结束一本书、一篇文字因此有困难,中间这部分成果愈丰硕、密度愈高就愈困难,像是把一个太大的东西硬生生塞入太小的瓶子里。难以忍受的通常不仅仅是得狠心大量舍弃而已,在舍弃同时语调也跟着改变,语言被挤压得又直又硬又锋利割人,原先的精致度、复杂度、暧昧度及其必要的限制性保不住,因此,它很难再和其他种结论、其他的可能相容或至少并呈,这极可能不是书写者的原意。书写者,尤其一个谦逊而宽容的书写者,得非常非常小心才能不让自己忽然变脸像是个严厉的导师、狂暴的旷野先知、自大无比的人、头脑简单的人、乔张做致的人云云,而这极可能正是他一辈子努力想离开、想避免成为的那种人—这也帮我们解释了,何以书写者的能耐全面进展同时,独独会感觉自己写结尾的能力不进反退。
这样想,曲终奏雅收场便不是个很糟以及不负责任的结束方式了(尽管我自己很难采行,有某种过不了的心结,如我很排拒那种无法履行的承诺、无法实践的安慰、无法信任的乐观),这起码躲开了自我破坏,不损伤内容;曲终奏雅,就是一个空洞但模样好看的句点,或者,休止符。

《正常人》
书写·剩多少个读者你仍愿意写?
书写不是情绪的抒发,不是不拣不择,不是玩那种朝花夕拾、比打字速度谁快的游戏。写一本书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工作,人把自己浸泡进去,专注于足够长的时间之中,几个月,几年,即使捕捉的、试图存留的是短瞬如春花如朝露的东西也得如此,在书写中,它一样得“长成”比第一印象更饱满、更富内容才够资格被书写,否则皆只是昆德拉所说“只配被遗忘的东西”;它转成了记忆,转成了随身携带的东西,转成了人心里持续发着光、依依不舍或赶它不走的某个形象,苛求你得想办法找到一种最恰当的、明显超出你此时此际所知所会的方式和话语写出来。
书写因此不是、也不可以是单纯的记录和描写(这是自然主义的谬误),书写是世界再加上人自己,或更确切地说,世界起了个头,但在书写进行之中,时光流逝,世界往往已经走过去了、遗忘了、连痕迹都拭去了,只剩人记得。书写因此只进行于人心之中,并一再地、一次比一次深入一些地折返人自己,所以书写同时也是人郑重的、持续时间最久的、累积的自省,超越了平常的、每天重新来过的那个、那一层自己。写一本书和写日记、写脸书文字因此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件事,也无法替代(妨碍和破坏倒是有,成为一种坏习惯)。
书写者屡屡有这一经验,被某个特殊的、戏剧性的心绪抓住所瞬间写出来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的、危险的、日后一想到就恶心一身冷汗的,它包含了还夸大了太多不配被写下、记住的无意义成分、莽撞错误成分和虚假作态成分,那些在真正书写时轻易可过滤掉的东西,所以太多太多书写者如此忠告我们,前一晚激动写的东西,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扔垃圾桶去。
但是,要如何凑足原来没有的、不属于你所有的读者数量好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要求呢?这真的是个难题,而且有愈来愈难的趋向,不只是因为再没有一整块一整块的新读者可开发而已,还有,人心缓缓变了,人和书的关系变了,其间某种荣光不再——相当相当漫长一段时日,这个问题被隐藏于,也相当程度消解于进步的耀眼荣光里,如某种庇荫。人置身在进步的浪潮之中,会生出对未来、对未知、对不可企及事物的极大善意,也往往乐于尝试,因此,读者的大量增加,不会只限定于热度较高的小册子和大连续剧小说,有一定比例会“溢”出来,旁及各种书包括那些他们其实不愿读、不能读的书,我称之为“尝试的”和“错误的”这两组读者。但博尔赫斯讲得很对,所有的诡计最终都会被揭穿,进步的源源荣光还是用得完,在此一进步意识不断被怀疑、已成强弩之末的今天,阅读的真相毕露,那些带尝试善念而来的读者或会弄假成真留下一小部分,但更多的,以及那些纯粹误解的则只会恍然离开,随风来随风去。
只是,这样并非绕一圈回到原点,因为没有原点了,永远不可能再发生那种五百本书就撼动一整个世界的事,新的规格、新的计量接管了世界—进步是美好的,但对某些书来说,回想这一场,却比较像是上了贼船。

《书店》
于是,今天的书写者总是得多做点事,或委屈或欣然,随人不同心性而定——书写不再只是书写者一个人的沉静工作,像朱天心所说作者好好写,读者好好读”那样极可能不够了(但这仍是最恰当的,我们仍该当它是一个理想)。这里比较尴尬的是,由于这“额外”的纯粹数量补充基本上是面向着尝试性的读者和错误的读者,这一定相当程度扞格于书写者本心、扞格于书的真正可能内容,所以很多真话不好说了,或至少只能轻轻地、含混地说,往往还得把最重要但可能最不安全最冒犯人那部分话语藏起来(这两种话语重叠性之高非常惊人而无奈),免得第一时间吓走他们,同时,书写者也得学会书写之外的其他种种本事,乞援于其他行业的专业技艺(表演业、政治业、公关业、广告业……),让自己更多知多能。
也就是,书写不再是倾尽所有竭尽全力,而是控制力道。
滴水穿石的,我们很可能慢慢淡忘了,乃至于抽走内容地改变了这个书写者最本命的、反求诸己的寻求和询问——书找寻它的读者,找寻的方式原是遴选和认出,每一本书仿佛都有它独特的音频,只有同类、只有某些人接听得到,如同我们稍前所说的“在人心和人心之间热烈传递”,如同月光下海面上浮起的鲸鱼用歌声召唤它的同类;读者原是非常珍贵的,甚至是难得的,用较浪漫的话来说是,这是和你一样心怀同一个问题,看向同一个世界、聆听同一种声音,并做同一种梦的人,这部分,也许你的家人、你三天两头相处交谈的所谓亲友都不见得能够,所以小说家阿城讲,他是写给那几个“远方厉害的朋友”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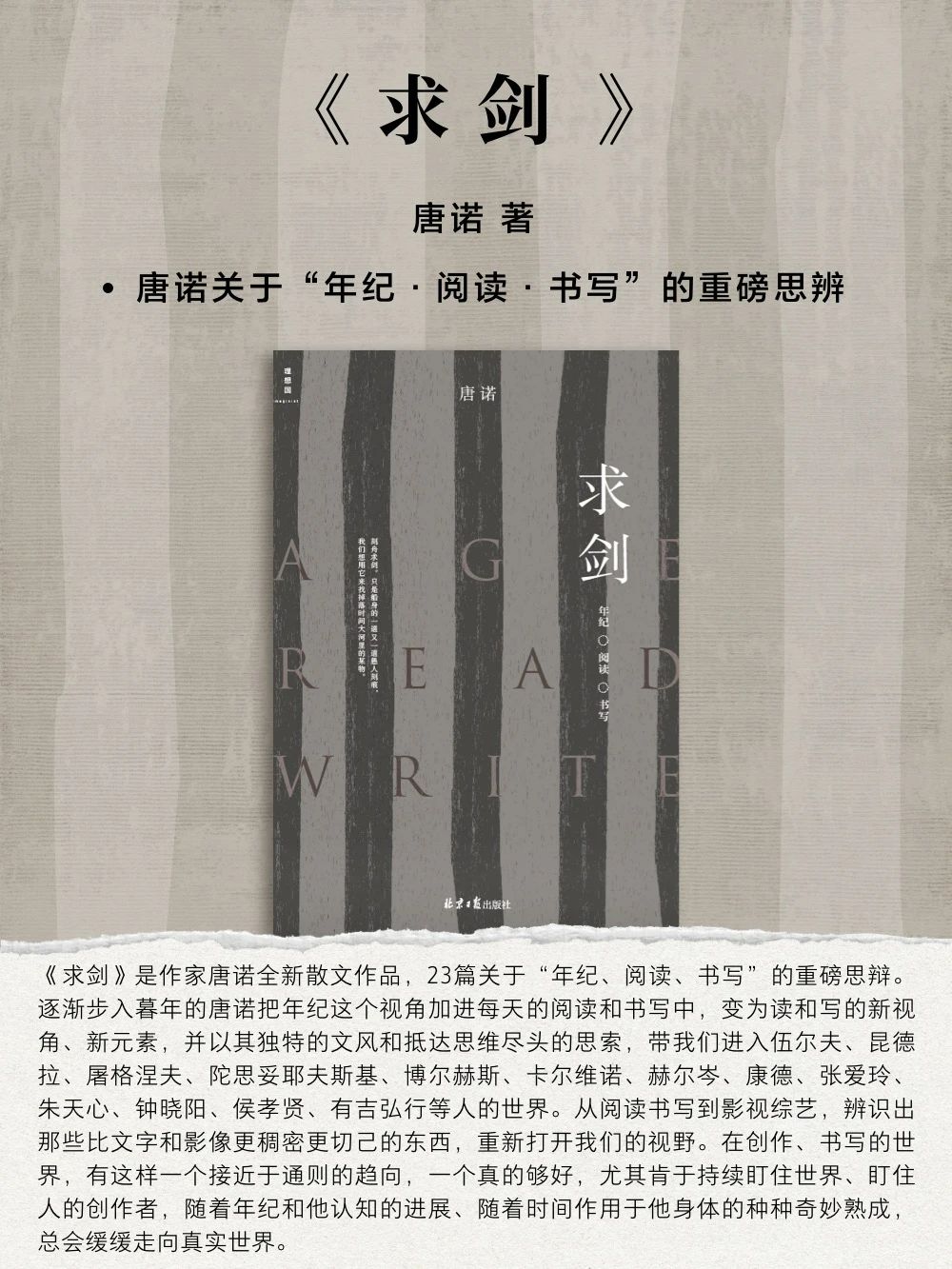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