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行员的妻子》
作为一个小小的古玩商、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不务正业小说家,费滢二十年如一日地晃膀子,处理着散落各地的事实碎片:
从地摊假货到良渚最北线里下河地区的先民;从十三区赌场里印度人抵债的半颗珠子到法兰西学院汉学所废置的图书卡片;从亚洲书店地窖里的伯希和木箱到戴克成的古玩店。
由于“研究目标”过于分散,导致博士论文无法完成,可费滢总号称自己是个“捡垃圾的人”,正在“收集世界的边角料”。
且慢,此人晃的膀子,跟本雅明笔下的flâneur(漫游者)是一回事儿吗?
为何她永远在打支线剧情,永远在捡垃圾,永远毕不了业?
留学生回国之前互相托付的那只大同电锅,和泰州光孝寺辗转取回的文物有何异同?
造假古已有之,搞历史、卖古玩、写小说都要面临共同的质问: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
……
而所有这一切,跟所谓的“文学”又有什么关系?
八月初,跳岛FM主播于是邀请《天珠传奇》作者费滢,以及“世界莫名其妙物语”的主播见师,一起聊了聊这些内容。经跳岛FM授权,理想国将本期文字精简版整理如下,也欢迎大家点击链接或移步小宇宙等播客平台收听完整节目。
晃膀子、flâneur和city walk有什么不一样?
于是:小费老师的两篇小说里面都有写到“晃膀子”。我想知道这个词的来历是什么样子的?
费滢:就是之前在豆瓣上曾经跟网友讨论说flâneur这个词应该怎么样去翻,然后我们觉得“浪荡子”有点不太恰当,比如小说中李石德其实是比较衣着考究的人,有点dandy,《天珠传奇》里就叫他们“荡弟”。所以其实晃膀子也不算是flâneur,而是一种“街溜子”。
于是:那你觉得它和本雅明笔下的flâneur是同一种类型吗?
费滢:我觉得不是。因为本雅明有一个很强的历史观,他会有一种新旧时代的交替,因为新的东西出现太快,旧的东西消失太快,从而产生的一种断裂感。他始终是一个观察家,他看着这些东西是如何产生、如何消失的,这是本雅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也有很多新的东西,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并不“新”,除了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本雅明复活,可能也未必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能像他的时代那样给他那么大的冲击。
像我们现在的晃膀子,有可能就是很多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比如说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多岁,十几年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我总得找一个活儿,但又不想进入朝九晚五的工作轮回,所以只能选择打点零活儿。晃膀子有可能就是这种,有了一点钱,我就要走在大街上把它花了,花掉之后我又要在大街上寻觅,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的,有什么吃的可以吃一下,或者是有什么零活儿可以接一下,这样的人。
见师:我觉得flâneur一般都是讲的是在拱廊街,那个时候先有了购物广场,就有人在里面溜达了,不然的话冬天就太冷了,走在大街上也没有暖气可以吹。除了flâneur以外,还有一些跟他类似的人,比如说赌博的、妓女。

《飞行员的妻子》
在本雅明看来,这几个类型是很典型的,在以前那种历史观里,他们是一些不太存在的人。在他提出这种历史观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刚才说的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他们的位置。那个时候除了本雅明以外,还有很多的人,比如说里尔克,或者波德莱尔这些人,他们提出“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关注的都是这些不知道该在哪里的人。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晃膀子的人,更像是没法进入体制的人,就没有他那么强的断裂感。
费滢:我觉得唯一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这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里可能都是一种偏向于谴责的行为。因为他不产出。
于是:所以是一个生存状态上面的不同,我觉得像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那个时代,基本上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期,所以他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像煤气灯、博览会、长毛绒玩具、电影这样一些新兴的事物。
但我觉得小费老师在小说中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游荡的时候,关注的对象并不是这些特别新的、作为社会现象的器物,而是一些老的东西,这个好像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但是反过来讲,本雅明自己也是一边搜罗老的东西,一边观察新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共同点。
说到逛来逛去,一定会讲到现在爆红的一个词City Walk,你们觉得City Walk算不算晃膀子?
见师:以前我心目中的City Walk,就是在Airbnb 或者Tripadvisor报一个旅游团,是很常见的一种当地旅游活动;还有一种就是在城里边带你逛逛菜场,跟你说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名胜古迹或名人,比如赛珍珠曾经在这里买过一条鲤鱼;或者你可以参加做饭活动。总之在我心目中它是一种主题旅游。跟晃膀子相比,它是一个非常有结构的、有明确的目的、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纯溜达的行为,不然的话你没法挣钱,对吧?
费滢:对,我也觉得它是一个消费活动。其实它是跟现在一些视频 App很想做的“本地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商业行为。把这个概念炒红之后,就可以推荐各种路线,搭配所有消费场所的门票,做一个团体的报价。
于是:那与此相比,晃膀子的人去的是哪些地方?看的是什么?消费的是什么?
费滢:其实晃膀子的人有一个一分钱都不花的本事。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想写一个和平里地区的生活,我整天在街上晃,那肯定是要先去麦当劳要热水,因为北京是一个完全没有地儿可以待的地方,街边也没有长椅,如果不在公园附近的话就很可怜,大商场里面也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除非你要去吃东西,所以你首先要去麦当劳里要热水,然后你要规划好沿途几个可以提供热水的地方,或者是沿途有什么样的公厕,因为哪怕你坐在星巴克里面喝咖啡,还是要去它旁边胡同里的公厕上厕所。所以你只要搞准这几个地方就可以了,每天消费控制在五十块以内就是胜利,最好是一分钱不花。
天气比较好的话,就可以在地坛公园门口的长椅上睡觉,天气不好的话,你一定得待在麦当劳。待在麦当劳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人,因为一般像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这样的地方,会给快递人员设立休息点,那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聊天,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快递员在等单的时候手上都在盘手串,然后小学生进来的时候手上也在盘手串。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汉庭酒店,所有华住会系统的酒店大堂都很欢迎你,还会给你酒店免费的矿泉水,你还可以看酒店大堂里的书。汉庭的人说,毕竟他们是一个平价酒店,只要上架一些比较贵的书,很有可能立刻就被客人顺手牵羊给带走了,所以他们就只能上一些很便宜的垃圾书,但我也看了大概四五十本,也就是说我豆瓣上标注的大部分书都是在汉庭看的。
见师:我要补充一下,我认识小费这么多年,她给我的建议一般都停留在这个范围里。十几年前在南京,她跟我讲说南师大门口有哪些地方可以免费晃悠;后来到了巴黎,我们就琢磨说哪家店的咖啡最不难喝,然后又便宜,你在里面可以坐得比较久;在外面溜达的时候就是图书馆、大学门口的自动售货机这种东西;还有就是去小公园嗦粉,小说里面也写到了那个小公园,确实便宜,而且她去那里赌博确实能赚到钱。

《飞行员的妻子》
如果永远选择支线任务
于是:我当时就在想小费是有多爱赌才能把这一段写得那么好。
费滢:一开始主要是发现那儿有好吃的,你花几欧元就能吃得很饱,而且能吃到很多肉,还有免费的饮料可以蹭一下,主要是越南速溶咖啡G7和晚上很差的Whisky。
后来发现了赌博这个事儿。我一开始还不太会赌,当时我也没有居留,巴黎警察局对待我们这种没有身份的人,“无纸人”,其实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因为我们需要大约凌晨六点钟去警察局门口排队去更新居留,每天只放五十来个号,我有一次六点钟起来浑身贴满了暖宝宝,在大约零下十度的露天中排三个半小时的队,然后放到第五十二个号的时候,他说今天不放号了,就在我的前一个。我就贴着这一身的暖宝宝回去了,回去之后把暖宝宝撕下来睡了一觉,到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诶,这个暖宝宝为什么还是热的?一看说这个新产品可以四十八个小时不间断发热,于是我又把这些东西贴在身上,又去排了一次队。
为了这个身份的事情跑了很多次警察局,至少有四五次,每一次都这样去排队,弄得人非常沮丧。当时我也就半放弃了,就想说算了,我也不要居留了,我也不要身份了,反正我也可以去听课,没有问题,我就不跟你打交道了。

《新桥恋人》
于是:听到现在我基本上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跟你小说中的人物都毕不了业。
见师:我觉得忙于赌博和吃饭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写论文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你剔除这些边角料的,你得找出一个主旋律,不光是得找出来,你还得相信,并且给你整个文章梳理出一个很精密的逻辑。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得出了什么结论,它得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像小费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整天在外面捡垃圾的人,你让她找出一个主线,并且相信这个主线,是很困难的,她整天在外面打一些支线,对吧?就像玩《巫师》,别人都在里面兢兢业业打怪,救自己的养女,把主线剧情打完,并且跟人谈恋爱,结果她进去以后,从头到尾就在那里打昆特牌,剧情没有任何进展。
有的人就是喜欢支线剧情,你让她去做主线其实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写论文的思维方式和捡垃圾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本雅明也是这样,他会总结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有主线剧情。“拱廊街计划”就是一个大型捡垃圾计划,它没有任何的主线,它的目的就是把大家的垃圾捡过来,然后也不加什么,就是整理一下堆在一起,以开头字母排序,就结束了。
费滢:就像你的论文大纲往往跟你搜集的材料完全不符合,一些所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现在很红的approach ,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你的素材相匹配的。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们总是说,你要先解决一个小问题,能把小问题解决就已经不错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只能去解释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见师:一方面人不能处理大的问题——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太能成功,因为要处理大的问题,并且找出这么大的一个主线来,那真的就只能靠编造了;还有就是,和书里的人物一样,费滢也喜欢把档案卡反过来,看它背面的内容,然后就完全被它带偏了,就像游戏里上一个支线还没做完,你就做下一个支线了,最后那些村民就只能站在原地等你回来。
“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
于是:所以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做大历史跟写小说其实是一个可以互补的行为。因为我看有一个采访当中,小费也提到过,说小说当中提到的这些素材,其实就是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边角料。
费滢: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做历史的时候,每一条引用素材都必须讲究出处,包括二手文献你必须要指出。但是在写小说的时候,就非常地自由,中间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是编的,它是一个很能给人快感的事情,就像你每天放学回来,你妈都要管你,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妈妈不在家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我研究珠子的时候去听了本校一个老师的讲座,他说在法国做论文,你使用的文物资料都必须是考古获得,他们不接受盗挖的,包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非认证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珠子都是印度河谷或者是东南亚生产的,一些珠子是在缅北盗挖的,他们在东南亚市场上买了很多这样的珠子进行研究,每个国家的学术规范还是很不一样,有些确实比较严格,因为他们会说:那你怎么能断定这些东西就是真的呢?
我们会面临很多次这样的质问。无论你是去做历史,还是做古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文字的,一切的素材,他们都会问: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或者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真事?
于是:证实和证伪这件事情在学术领域中会显得非常地绝对和必要,但是在写小说的时候,它其实反而增加了创作者的一种自由?
费滢:其实写小说的时候,这个这种质问是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小说写得不像真的”“这件事看起来不真”“ 像是一个假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责难。甚至还有那种要突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他杜撰的,或者是有意用一些素材引导大家去那么认为的。小说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你怎么能让故事真?小说中的真实,跟所谓历史叙事中的真实,或者跟放在你面前的一个物质、一个考古证据所提供的真实,是不是同一种真实?
你是怎么开始写小说的?其实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才会想,我可以动笔试试看怎么去处理这个真或者假的问题,我当然没有办法去回答,但是我可以去处理它。
每个时代都在追寻一种已经失去的东西
于是:好像造假这件事也就是在当代才会变得非常夸张。我看《天珠传奇》后面那一段讲到他们用糖来做这个假珠子,真是叹为观止。

《杀死了一只羊》
费滢:其实造假古已有之。你知道宋代的人仿造汉代的玉器,清代的人仿造宋代的玉器,采用的方法都是低温油炸,那怎么样去分辨?要看从古到今不同的低温油炸的表现,也就是看低温油炸上面会不会有其他的痕迹。比如说,宋代的低温油炸我们叫作“提油”,它是为了仿造汉代玉璧上的沁色,氧化铁离子进去以后的红色,或者是水银进去以后的黑色,用油炸的方式把它给炸进去。
那么现代的油炸和宋代的油炸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宋代的温度比较低,现代会心急一点,它的边缘就会出现一些细细的线,线上面会有锯齿般的痕迹,这就是现代的油炸制品。民国的油炸又有不同的风貌,它会把所有的玉都炸得非常红,就像我们叫作“老土大红”的一种宋代的沁色。所以就是每一个时代都在仿古,都在作假,都在追寻一种已经失去的东西。
包括《天珠传奇》最后一章讲到的用糖把珠子染成深色,其实就是古代印度河谷给所谓的红玉髓,也就是红玛瑙染色的一种方式,因为红玛瑙有缠丝的结构,所以要想要造出那种深色的、质地比较纯的玛瑙,就必须采用染色工艺,糖就是他们一直都使用的材料之一,也是用加热的方式把糖的颜色给煮进去。
文字中的游戏时空
于是:很多人在看小费的小说时,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时代的错觉,如果不是出现像手机、签证、量子鉴定仪、自动投稿机这一类关键词的话。所以我想问一下小费,你觉得小说家的语感可不可以不跟随时代的主流变化?
费滢:如果是从小说开始讲,这种写法其实来自于我跟豆瓣网友以及见师关于游戏设置的讨论。因为游戏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时间进程跟真实生命的时间进程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那么它怎么样去标注时间?你打到不同的地图才会进入不同的时间,它是一个地理性标志,放在写故事里面,其实我并不需要去标示它到底是什么时间,我进入了不同的地理性标志,它自然就会昭示用什么样的时间进程。
包括文中的语汇,其实也标示了它的时间。包括你在阅读时的体感和文本是怎么样去交替产生作用的,这个我也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也有意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有文有白的语汇,包括现代的网络用语,可能是我自认为先进但其实很古早、很土的网络用语,去让你觉得我是打到了一个不同的地图上,这其实是游戏里面一种非常常见的设置。
还有我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产生自我们经常讨论的一本经,叫作《梵网经》,它觉得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一张大网一样。但你不要去想它是平面的,它其实可能会有数个空间,或者是数个时间、数个维度之间的关联,然后是它当下所在的位置、那个点决定了它被其他的一些东西影响,同时它也影响了许许多多非常遥远的事物,它是共振的一个大网。其实就说明了这个东西是不可预言的,因为你无法计算出同时在振动的东西互相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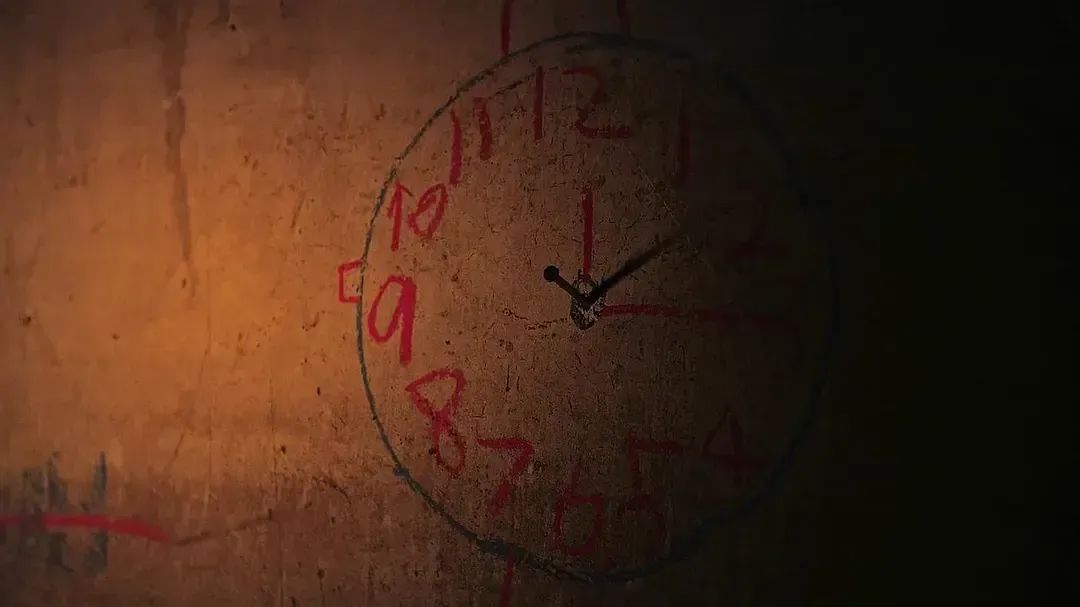
《路边野餐》
见师:只是说游戏这个媒介可以让我们更加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很多不同维度的时间在同时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游戏本身有一个游戏时间,还有一个叙事时间,然后你自己玩的时间,至少会有三层。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一关打不过你会一直死,就不停地旋转、循环,过了这关以后它又变回线性时间,会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发生。还有刚才说的时间是以地图的形式呈现,它有很多种把时间拧成空间的东西,所以会比较有意思。
《梵网经》是说,有很多平行的解释世上发生的不同事情之间联系的办法,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办法比另外一个办法更对,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一些捡珠子、穿珠子、捡垃圾的人,不一定能像历史学家,他们会有一套标准,可以证明材料是真的,比如他们会认为闲鱼上买的材料不是真的,但档案馆里的是真的。但是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不一定哪一个就比另外一个更真。
费滢:还有一点我也很感兴趣,你在游戏中死了以后,可以回到死的地方去捡回所有的东西,但是你的钱会丢,然后你又可以到村口去打牌赢钱或者装备。比如我只打过《暗黑破坏神》,就是这么设置的。
原创文学究竟有没有“原创性”
于是:刚才听你们讲,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创作者的叙事其实受到了很多层面的影响,但我觉得小费你找到了一个平台,就是“物”的平台,古玩也好,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也好,当你用叙事的手法去讲述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时,你去阐释它的真和假,或者去揣测它的来历和将来时,一个故事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你的小说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起点,就是人跟物的关系。
费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因为我也只能写我能写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恰好又是我比较熟悉的东西。我跟见师之前讨论过一些问题,例如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应该怎么样在小说里面去构造,就是游戏里面的叙事策略的问题,还有游戏里面为什么会设置一个“捡垃圾的人”之类的。我之前对游戏以及网文非常有兴趣,我非常想写一个网文,或者写一个地摊文学式的东西。
我先讲一下地摊文学和网文的不同之处。地摊文学是以男女私密之事,以秘闻、丑闻为主的。然后网文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它会有一个像数据库一样的东西,所有的梗、所有的套路都可以进入一个数据库,它是在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进行拼贴的一种游戏,区别只是我采取的是哪些素材罢了,网文一定要玩梗。
所以我当时想通过小说完成或者说实验的是,很多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原创性?因为在网文的时代去讨论网文的原创性,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包括当代所谓的中国原创的严肃文学,它跟网文之间到底有什么界线?其实没有界线。就算原创文学的作者已经进化到我们所说的“水准以上”的程度,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语汇,但其实他的套路,他的各种方式,包括他关注的角度,其实都已经是被现代的读者市场所定义的一种东西。包括作者的身份,包括我们今天录制节目,通过整个一个营销的流程,把这些东西送到读者面前,它具有它的原创性吗?其实我觉得未必。
所以我在小说里其实是有一些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意识,包括我在《行则涣》,特别是我的第二篇小说《反景》里面,用了很多很多前代文学或者当代的素材,很多文本其实都不能说是”典故”,就是“戏说”这样一种文本类型。比如说鲁迅写的绍兴戏、张爱玲写的绍兴戏,比如说唐鲁孙,比如说用了大量的废名。这对我来说就是所谓原创文学中的一种玩梗。为什么网文可以玩这样的梗,严肃的原创文学就不能呢?但我发现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是其实大家很多都识别不出,可能是我的读者不够多吧。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文学都是一样的,里面所有关于语言的游戏、形式、叙事策略,都是可以拿出来反复使用并且能够被读者认出、能够会心一笑的,这应该也算是我的一种游戏设置。
物质世界中的流转与关联
见师:你要不要说一说《行则涣》这篇是怎么回事?
费滢:其实《行则涣》这篇小说主要是探讨的是一种对于“时间”和所谓“实存物品”,以及“虚构”的概念解析。它并不是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是通过物品之间的共同之处,让它们自己去演说它们的意义。
其实《行则涣》里涉及太多的人和事。我写的其实是家乡附近一个小城市泰州发生的事情,书里的报恩寺其实是泰州的光孝寺,里面的南舟和尚其实是南亭和尚,当时是光孝寺的和尚去台湾的时候,把大量的寺中文物托给了静安寺,静安寺的住持去台湾之前又把这些文物托给了中国银行,放在静安寺的保险柜里。后来光孝寺在马来西亚开会的时候碰到了赵朴初他们,赵朴初提出,我们要重新发扬宗教传统,光孝寺是否可以重建?重建光孝寺的时候,他们就申请再把保险柜的东西拿回来……其实书里写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物的流转,不停地换手,但我觉得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把它说得那么明显。
见师:费滢写的东西都有点搞笑,这种流转就有点像留学生回国之前互相托付的那只大同电锅:一开始它在一个台湾学生手里,然后他要回国了,这个电锅怎么办?就可能托给一个大陆学生,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托给一个香港学生,最后这个台湾学生又回来了,问,我的电锅还在吗?你能还给我吗?
费滢:所以说,一个物品能承载多少意义,其实跟它的流通、跟人的变迁有关,我就是想写这样的事情。就像大同电锅,你说大同电锅它本身有什么意义?

《路边野餐》
文学的世界其实离我们很远
于是: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无纸人”的状态,在国内文坛还蛮少见到有人专门去写的,放到更大的时代背景当中的话,你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世界文学”“移民文学”这些标签的?
费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移民文学,作为当代外国文学中的一个门类,一般都是由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去写他们那个族群的生活。之前移民文学还有很多的政治重量在上面,现在还会有一些“少数族裔”“女性”“后殖民”这样的标签在上面,所以移民文学跟我的处理还不一样。
其实我这种叫作“流民文学”,确实没多少人写,因为华人去写海外生活,一般都会抱有一些虚荣心,会有一点“高华”气质,不会说我在国外混得很差。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回到国内,其实他们在国外是拿到文凭的,可能也会擦桌子、洗盘子这种打工经历,但是不至于像我一样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居留。
见师:你觉得你写的是啥?
费滢:我觉得我写的就是一种状态。
比如说,我马上要写一个新的小说,叫作《一九九〇年代的写作爱好者》,这个小说的开头其实还是在巴黎。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要请我吃饭,说,费滢,你会不会处理法律文书?我说,什么法律文书?他说,我打拳的时候有一个师兄捅了人,所有跟我一起打拳的人都没有居留,所以打拳的师父就问我们留学生能不能帮他处理法律文件。当时我还有身份呢,我才知道有一群所谓的“无纸人”在巴黎三区的一个教堂里,白天那个教堂做弥撒,晚上椅子挪开,所有人在那儿练太极拳。跟一个咏春师父练太极拳。为什么要练太极拳?因为他们要去参加法国的外籍军团,这是他们能够拿到居留的几种途径之一。
我想去调查,就说,那我也去打个拳。我爸就跟我讲,你要去学拳,就去找我的一个朋友,他也在巴黎,原来是南京监狱的一个警卫,他真的会打军体拳,如果你想学的话,就去找他学。于是我又去找到这个打军体拳的人,发现他都在跟我讨论文学,他是一个一九九〇年代的写作爱好者,但是跟他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方向的,因为我当时特别年轻,还是一个本科生,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人去诉说,那我们在说的这种东西叫“文学”吗?其实我不知道。我记得我跟他彻夜长谈三天,每天都要到他家去吃饭,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尽可能地招待我,做了很多很多菜,他有很多对文学的幻想,包括他来巴黎其实也是为了更加接近文学。
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文学”,它算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学”?如果你把他所有的经历都放在一起,把我后来真的没有居留了又晃膀子了又赌博了这种东西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去讨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流民文学。这个世界其实不属于我们,文学的世界其实离我们很远,哪怕是写出小说,也离这个中心很远,离我们所称的那个“文学”的名字,以及文学的本质,离所有的东西都太远太远了。包括我现在写的东西,其实也很远。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