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登:各位好,我是樊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教授。
丁奎岭:大家好,樊老师好。
樊登:请您来觉得特别忐忑,我虽然读了一些书,但是您这个专业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什么叫手性?
丁奎岭:这个概念的话,还是很有历史的。如果通俗地讲,就是我们的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关系。你看你的左手和右手,大概看上去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无论怎么摆,它没办法重合的。如果你把大拇指这样一放的话,它始终是一种镜子里边的图像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看似完全一样,但是本质上它是不一样的,这种对应的关系我们就叫做手性。化学里边的分子世界,它是有这种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在我们的人体里边,组成人体的最主要的分子有氨基酸、核酸、还有糖。氨基酸它是左手的,糖是右手的。
樊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您的意思是说,氨基酸的结构和糖的结构,看起来是很像的,但是两个不能重合在一起。
丁奎岭:不是,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氨基酸里头,它也有左手的分子、右手的分子,两只手都有,但是自然界选择,当它诞生这个生命的时候,只选择了左手,那么糖它就是右手的。氨基酸形成多肽以后,它又形成螺旋结构,实际上螺旋结构也是一种手性。举个例子说,你经常看到的植物攀缘的时候,它是螺旋的,而且你去仔细观察的话,绝大部分都是一种方向。你再去看海螺,你去把很多海螺收集在一起看一看,你会观察到99%以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这就是手性不仅在分子世界里头有,在它的集成体,或者是在更大的尺度里边,它都是手性的。
樊登:那这项研究的好处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
丁奎岭:刚才说到组成生命体系的三大物质,它是手性的,但是它只选择了一只手。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需要吃药的时候,刚才说了分子世界它也是手性的,那么这个药怎么发挥作用,它一定要跟生命体去作用,就像我们的手套。生命体里面,它本身就像一个手套,这个药物进来了,它进去了,相互作用了,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了,我人体是左手的手套,你来个右手的手往里头插。
樊登:插不进去。
丁奎岭:要么插不进去,要么插进去不舒服。其实药物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应该是非常精准的,只有精准了才能够不至于跟其他的部位去作用,所以这就是手性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你吃进去了另外一种手性的分子,它可能带来的是副作用,这种过去历史上也有悲剧发生的。就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欧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反应停事件”。很多孕妇怀孕的时候会有妊娠反应,需要吃一种镇静药,这个镇静药分子当时做出来它是很有效的,但是它是消旋的,也就是两只手都有的这种。其中分子的一个异构体有镇定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它会导致胎儿的畸形,所以就在欧洲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叫“海豹婴儿”:很短的胳膊、很小的手或者很短的腿。所以手性在药物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契合了,也就是说手和手套只有配合得很好了,才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而另外一只手,你给它也送进去,但是它跑其他地方搞破坏作用了,甚至产生副作用。所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FDA就要求,只要是涉及到手性的,那就有左手和右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把每一只手结构的分子,它的活性、毒性,都要做实验,最后成药的时候尽可能以一种异构体、一只手来上市,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地避免副作用。
樊登:每个人体内的那个手的方向都一样吗?
丁奎岭:都一样的,所有的人类都一样,人类生命世界为什么选择单一的手性,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自然界的生命的起源,一开始也没外界的因素去影响它,到最后进化成生命,怎么倾向于一只手的方向去走了呢?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刚才讲到了手性,单一手性药物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希望吃最有效的那个,而把那个无效的、甚至有副作用的除掉。因为我们对药物的要求,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以上。那么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手性的药物,左手右手你不把它分开的话,那就相当于一半的杂质在里边。另外从制造的过程来说,这两个分子我只想要这一个,而不要另外一个,那怎么办呢?就需要来控制反应的过程,就需要催化剂。我们常用的就是用手性催化剂来控制这个反应的过程,最后就会得到一种手性的分子,那么把原料也节省下来了,也不产生另外一种手的副产物了,所以手性催化,因为它对药物的研发、对药物的生产、对生命过程的认识这个重要性。所以20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授予了手性催化这个领域。
樊登:化学家真了不起。我觉得化学家扮演着相当于半个大自然的角色。
丁奎岭:化学家几乎可以创造万物。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你还能离开化学吗?甚至有人说“我要吃有机的东西,我要吃天然的”,天然的也是化学,植物里面那不都是化学分子吗?在化学家的眼里边都是化学。
樊登:看咱们节目的有很多中小学生朋友,我替他们问一个问题:您是从小就这么喜欢化学呢,还是后来到了博士、博士后阶段才爱上化学?
丁奎岭:选择的话,我觉得也有像当初生命体里,为什么选择左手,为什么选择右手,也很有关系,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想学习,学什么都可以。
樊登:报上了化学就就上了?
丁奎岭:是那一年高考,我化学比物理多两分,物理77分,化学大概79分,那么就觉得好像化学有一点点优势,那么就学化学吧,就这么简单。我的热爱是因为选择了,然后爱上了。我们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对某一个学科或者对某一个领域,没有这种热爱,没有兴趣,那是很难做好的。就化学领域来讲,我告诉大家,人类到今天为止所了解的,或者是说创造出来的,或者是发现的,这种分子也好、材料也好,只有1.5亿多一点,也就是10的8次方。那么按照元素周期表里面的主要的元素,按照500左右的分子量,如果你去排列组合,这个化学的空间是多少呢,是10的63次方。你可以想象,10的63次方和10的8次方,我们人类所未知的、或者可以探索的空间,和我们所认知的空间差了50多个数量级,也还是沧海一粟。所以化学这个领域,它可以探索或者是可以创造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所以要了解这些背景,你想创造一些影响、改变世界的东西,那我觉得,学化学是最好的选择了。
樊登:今天丁校长来,带来了一本书,叫《走出思维的泥潭》。这是您审校的书,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当年我上中学或者大学的时候读过这本书的话,我做科研肯定会更有意思。它教你怎么做科研。很多年轻朋友以为科研就是写论文,就是到处找文献综述。所以您能不能跟大家传授一下,科研到底怎么做,或者说科研一般分哪几步?也就是这个书大概的一个提炼。
丁奎岭:做科研跟学习是一样的,除了我说朝着哪个方向走、选择什么领域、兴趣很重要以外,就是你要能够发现问题。我觉得问题导向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做科学研究或者是做探索,不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我们做科研一定会问问题,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要找到你要解决的问题,觉得它是一个真问题,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入门的第一步。
樊登:我跟您坦诚一下一个普通本科生的想法。我们当年在选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通过答辩。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选什么样的命题容易通过答辩,什么样的命题容易找到资料,什么样的问题有师兄师姐可以带一下,都是实用主义的问题。
丁奎岭:其实要找到一个真的问题,哪怕你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你会有针对问题去设计不同的方案,也许所有的方案都失败,但我觉得你也是成功的。因为你学会了怎么去设计方案,你学会了怎么去实践你的方案。最后结论是没成功,那也是成功。至少你可以未来再去探索的时候,你不会再重复走这个老路了。
丁奎岭:所以第一步是找到问题,第二步是设计各式各样的方案,然后第三步就是用科学的实践去验证。这本书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找到它的可证伪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本书里边也讲到了,你得坚持。好的运气从哪里来,好的运气往往是因为你坚持,最后才成功,那么坚持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我觉得兴趣、还是兴趣,一定要有兴趣才能够坚持下来。
樊登:我觉得化学教授当校长能当好,我为什么这么想,做化学的人讲究基因,讲究内在的生命力,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推动力,这个推动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才能够给一个校园、甚至给一个社会带来内在的活力。
丁奎岭:化学还是一个最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它可以创造很多自然界里边不存在的,但是又具有非常好的功能的、能够造福人类的这些物质,我觉得这是无与伦比的神奇。比如说青蒿素,尽管获得的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化学分子,它是一个影响改变世界的分子。我们屠呦呦先生和其他国内的很多科学家,那个时候就从中国传统的医学、药学、中药里边,认识到了青蒿是一个对疟疾有作用的草药,那这里面一定得有有效的成分。屠呦呦当时就把这个有效的成分,给它提取分离出来,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的方法,通过合作,最后把这个结构确定出来。其实青蒿素最后没有成药,而是由青蒿素作为原料,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经过化学转化,也包括手性合成,通过转化,变成了蒿甲醚、蒿乙醚,琥珀酸酯、双氢青蒿素,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用上的抗疟药物,所以化学真的是很神奇。
樊登:化学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太大了,你想就一个青霉素的发明,救了多少人的命。
丁奎岭:青霉素的发明可以说,当年号称是比黄金还要贵的药物,其实细菌、或者是病菌,它也在不断地适应最早的这个药物,所以怎么办呢,你找到新的抗生素越来越难。化学家就有办法了,在青霉素那个基础上,不断地改造,它的性能越来越好。大家知道我们吃的头孢,有一代二代三代。这也是人类用化学的办法,来不断地保护自己。
樊登:我们事先收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咱们看看网友们问的什么问题,第一个网友说:丁校长,一般学生都要到初二、初三,才会在课堂里正式接触化学,但您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上了大学了,您觉得在哪个年龄段开始接触化学比较好?
丁奎岭:初中阶段,我觉得就应该去学习一些,初一就可以了。科学的教育,我是觉得,你只要把教材设置好,是可以早一点。
樊登:第二个网友说:请问目前我们国内对手性合成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水准?这可能是业内人士。
丁奎岭: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了,应该说我们国家在手性合成领域里边,应该是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可以从一些我们国家的自然科学一等奖里面,比如说南开大学周其林院士,他们做的手性催化剂,其实无论是在性能,无论是在应用这个方面,都是超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当年的那些催化剂。当然我们有后发优势了,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新冠期间用的帕克洛维德,它是两个组分,有一个组分,也是涉及到手性合成的。这些原料的制造都在中国,大部分都在中国。所以我们国内很多企业的合成能力,手性合成化学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樊登:明白了。第三个问题:丁校长、您是一个催化达人,从催化分子合成,到催化青年一代人才的培养,平时有这么多工作,您还有时间看书学习吗?您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丁奎岭:确实看书学习的时间比过去是少了。其实现在学习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多种的方式,看书、读书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有闲暇的时间,去选择一些好的书、静下心来去读,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学习,就是现在的信息技术的手段,让你随时都可以学习,所以只要有这种好奇心存在,你学习任何方式我觉得都可以。
樊登: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丁校长您知道您做了校长以后,每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大家都非常关注,您有一段话被大家传得比较多,说您告诉学生,做科研要有交叉融合的意识,打破边界、突破藩篱,这是您给年轻科研人才的忠告,您觉得为什么交叉这么重要?
丁奎岭:从创新的途径来讲的话,肯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么探索的方向在哪里,我大体上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深挖,在一个领域里边,你就沉下心、坐下来,不断地去挖,挖到别人没有挖到的那个深度,你才能有所发现,也许能够有金矿发现,也许失败。但是如果你没有到那个深度,或者没有去超越那个极限,那你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您刚才讲的,其实更多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交叉,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朝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要做一件事情,它不是靠一个学科一个领域,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讲到了生命科学里边三大物质,DNA。核酸是一个记录人类自身信息的载体,那么可以不可以用它来记录人类文明的信息,所有的数据用DNA来存储。
有人做过统计,全球的数据大概只要200公斤不到的DNA,就可以把它全部存储起来,当然这是一个梦想,从理论计算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做这件事情,DNA的合成要化学家、要生物学家,特别是需要合成生物学;合成了以后,这里面还有编码呢,还有软件,还有这种信息怎么跟当今的这些信息计算机,能够对接起来。你想一想如果要做这件事情,没有交叉能行吗,你一定要有软件的、有硬件的,有物理的、有化学的,有材料的、有信息的。
樊登:您提的这个建议,其实在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么一个规律,基本上这些大的变迁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水陆两栖,这些边缘地带才会出现变化。
丁奎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朝着那个交叉地带,无人区的交叉地带去探索。
樊登:我们来看下一个:您一直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您是院士、所长,同时也是老师、校长,这几个身份里,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丁奎岭:我觉得做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身份,其实我最早博士毕业以后,就在大学教书,在郑州大学教过八年书;然后到了中国科学院去工作,20年我也没有离开过讲台,尽管做所长还是比较忙。当然到大学里面,教书育人更加是我的责任,所以始终没变的。其他身份都变了,只有老师这个身份没有变,我觉得当老师还是我的最爱所在。
樊登:真是特别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领略到化学的魅力,也见到大化学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跟您说话,就是跟我们其他的老师说话是一样的,并没有那种化学家的神秘感。
丁奎岭:化学家没有神秘感,化学还是蛮神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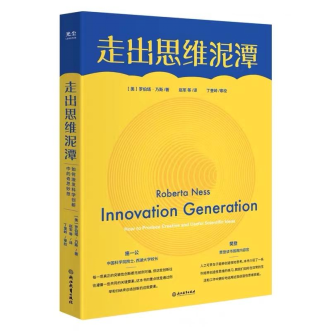
【帆书(原樊登读书)】栏目稿件,未经授权,禁止搬运。纸质图书,请关注【经观商城】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