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马向阳/文
当代学人里,高全喜是少见的、带有强烈的“问题主义”关怀的学者之一。由文学而哲学,由哲学而政治哲学,由政治哲学而关注中西近代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他的每一次学术转向,都与对当下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转型之现实关切相维系。
摆在案头上这本600多页的《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一书,就是高全喜过去30年来上下求索、苦苦追寻的一部关于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梳理的私人“读书笔记”,其中涉猎了博丹、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18位西方知名思想家,篇幅或短或长,内容或偏或全,完全取决于作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及主题,而非是一本体系严密的教科书式作品,无疑,这样的选择和设计,无不体现出独特的“作者关怀”。
本书故意忽略了古希腊罗马以及漫长中世纪的西方思想叙述,其实也正是为了对应作者自己“一辈子关于近现代中西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理论关怀”,也就是高全喜对于近代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思想演化和社会变迁的探究: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现代性”种子,是如何在中国这一异域文明中生根、开花、结果的。数百年来,这一进程充满了种种关于“古今之变”和“中西之辨”的激烈争论,如此喧嚣纷扰,它们又将如何穿越中国这一古老东方文明所标示出的某些特定时代和历史的“三峡时刻”,其思想源流激荡至今,依旧有着澎湃之巨大回响、幽深之无限迷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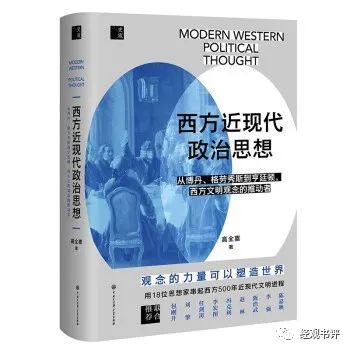
《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
高全喜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3年4月
陆地政权与海洋政权:
现代新世界的两种选择
《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篇,高全喜特别选择了荷兰16-17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并花了82页的篇幅来论述其思想,其篇幅几乎可以独立成一本小书,这也是作者在论及18位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们时着墨最多的一位。
早在2007年高全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研究生开设一门选修课程时,就特别注意到了格劳秀斯的“中国意义”。这一次,与格劳秀斯对标的人物是中国晚清的重要思想家魏源。在作者看来,魏源当年所处的时代,和格劳秀斯在荷兰16-17世纪的社会巨变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时刻,往往也是一个国家面临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情势大转型的关键时期。
本质上,魏源和比他早两个世纪的格劳秀斯曾面临同一个问题:新兴的海洋及海洋文明,而从个人际遇到国家选择,这两位不同时期的中西方思想家的命运却有着惊天差别。作者的浓墨重彩之处,也正是其不胜唏嘘和无限感慨之处。
1843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历时三年编译的煌煌巨作《海国图志》在扬州刻印出版,全书凡50卷,共计50余万字,这本书寄托了晚清维新图治之新派人物林则徐、魏源等渴望了解西方世界,急于融入海洋文明的殷殷期待。不曾料想的是,甫一面世,其在中国的境遇竟然是“举世讳言之”,因为它公然冒犯了清朝士大夫们的自尊和常识,因“犯诸公之忌”,而被束之高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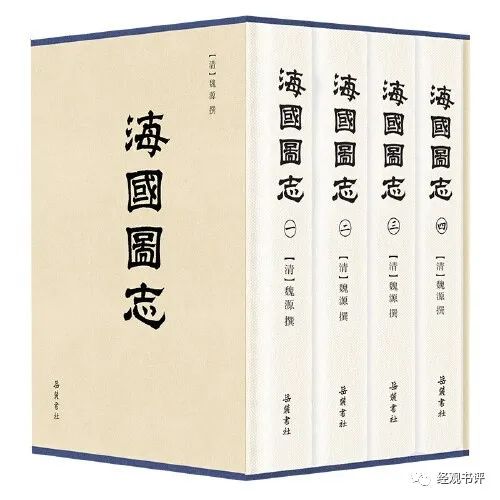
《海国图志(全四册)》
[清]魏源 /著
陈华 常绍温 黄庆云 张廷茂 陈文源 /点校注释
李金明 廖大珂 李一平 李长林 /审订补注
岳麓书社
2021年8月
8年后的1851年,日本人在港口查验中国商船时意外发现了《海国图志》一书,到1854年,中国商船相继将此书带至日本共计15部,日本知识界掀起了一波“海国图志热”,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两年间,各种不同版本在日翻刻高达二十余种,这本在晚清中国士林备受冷落的奇书,“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甚至“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
按照梁启超、钱基博的考证,《海国图志》的意外输入,为幕府末期的日本知识分子从事明治维新运动提供了及时而宝贵的思想资源,日本维新志士无不“读之而愤悱,攘臂而起”。先贤如林则徐魏源辈九泉有知,想来今天亦不能瞑目。
相比于魏源,格劳秀斯在当年荷兰的命运虽然算不上飞黄腾达,但作为一代思想巨擘,他关于国际法、个人财产权利和国家主权的诸多开创性理论,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启迪了洛克等西方思想家。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当年他回应海洋新文明的划时代作品《海洋自由论》。
15世纪,哥伦布和麦哲伦等冒险家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不仅是掠夺式资本主义的肇始,也掀开了海洋文明的新篇。荷兰、西班牙和更早的海外殖民先驱葡萄牙,为了争夺海上霸权,相互之间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争。1602年的一天,在马六甲海峡附近,隶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在经过一番悄悄武装之后,迅速捕获了一艘名为“凯瑟琳号”的葡萄牙商船。
此前,葡萄牙商船几乎垄断了欧洲对东方的海上航行和自由贸易。当时,这艘名为“凯瑟琳号”的葡萄牙籍商船上装载了60吨中国青花瓷和1200包中国生丝,正准备从马六甲运往欧洲。这些生产于万历年间的瓷器精美绝伦,在被掠走两年后的1604年,当这批瓷器在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时,整个欧洲为之轰动。当地人不知道这些瓷器的产地,加上这些青花瓷器是被荷兰人称为“克拉克”(Kraak,荷兰语,意思为葡萄牙战舰)的船运来的,欧洲人便称这批中国青花瓷器为“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
“荷兰人笑纳了他们缴获的大量战利品”,但并没有伤害船上的近700名船员。意想不到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中的门诺派教徒纷纷拒绝接受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凯瑟琳号”上的物品,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武装商船进行私掠的行为,属于武力抢夺。这些门诺派领袖在震惊之余,出售了自己在公司的股票,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并退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彼时,知名律师兼思想家格劳秀斯接受政府指派,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参加了在捕获法庭进行的诉讼。诉讼间隙之余和庭审结束之后,格劳秀斯还专门撰写了一本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的著作,这便是他的传世名作《捕获法》。有意思的是,格劳秀斯在1605年完成此作品后,并没有马上出版,200多年后的1868年,该书手稿在被一位大学教授意外发现后才正式付梓。但早在1609年,就有好事者将《捕获法》中的第十二章稍加修改,化名为一本《海洋自由论》的小册子在荷兰匿名出版。当时,除了格劳秀斯本人,没有人知道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
在《海洋自由论》中,格劳秀斯开天辟地地指出,海洋是自由流动之世界,广阔无垠的海洋,不应该属于某一国。而根据国际法,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航海到任何地方,包括葡萄牙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权以发现者或者教皇的赠予之特权来垄断航海权。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思想家如此详细解释海洋自由的所有权、航海权和贸易权等权益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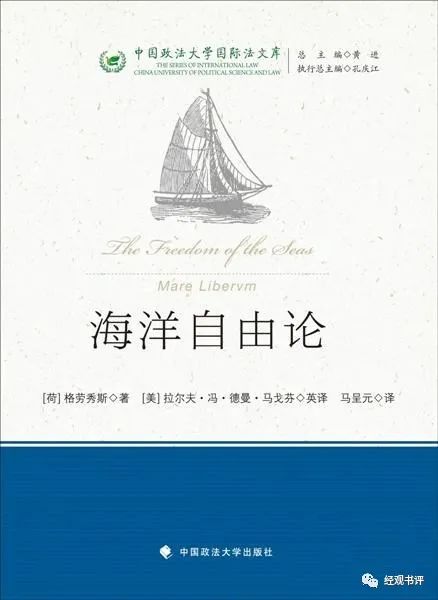
《海洋自由论》
[荷]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著
马呈元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基于《捕获法》,格劳秀斯在20年后又完成了他著名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开始,格劳秀斯率先提出了“正义战争”的概念——为保卫自己的财产或权利,取得属于自己的财产或利益,或者为惩罚对方的犯罪行为而进行的战争,这些都属于正义战争;在没有法庭对国家之间的争端做出裁决的情况下,战争作为实现正义的手段是合法有效的;战争实质上是因为缺乏能够处理争端的法庭而诉诸军事力量进行的法律诉讼。除此之外,即为“非正义的战争”。
20世纪的德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沿着格劳秀斯的这一路历史脉络,将近现代的西方政体分为两大源流:一是法国等欧陆国家代表的“陆地政体”,他们恪守《罗马法》,退守陆地;另一派是以荷兰、英国和美国等海洋国家代表的“海洋政体”,他们以《海洋法》为支点,主动出击,参与并控制海洋霸权。
大航海之后,陆地政体与海洋政体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对决中,后者最终几乎完胜。值得注意的是,施密特认为这不仅仅只是围绕陆权和海权的国家争雄,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观念之争,过去400年来的陆海争斗,本质上演变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围绕国际竞争(实际上是海洋权益竞争)而展开的一系列从主权建构、法律拟制、军事贸易、当公共政策的全方位变革,这些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几乎都和海洋这一全新的法权事务休戚相关。
在海洋权益这里,整个世界的历史意识变迁和空间革命几乎同时发生了惊人的重叠——海洋法、普通法、代议制民主、自由贸易和市场资本主义,所有这些新思想和新制度,都通通被打包纳入了海洋政体的宏大体系之中,一言以蔽之,过去400年间的一切重大变革,都和“海洋意识”有关。
在17世纪初的荷兰,激进的国家主义者格劳秀斯和保守的门诺派教徒围绕葡萄牙籍贯商船凯瑟琳上的货物权益所展开的争论,印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历史特征。“荷兰联省共和国”自1581年宣布独立后,海洋政体帮助荷兰在欧洲取得了第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当时,安特卫普等地的大批富商开始迁入阿姆斯特丹,164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第一家资本主义式的银行。荷兰不仅拥有当时欧洲最大的商船队,并于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1606年,荷兰舰队在马六甲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的海陆军,开始称霸海洋。而格劳秀斯当年关于海洋作为全人类所有成员的“共有财产”(community)、资本主义最灵魂核心的“私人财产”(private)、国家的“公共财产”(public)三者之间进行的严格区分,无疑充当了荷兰作为新兴的海洋政体急于满足海外扩张的舆论“先声”。
在一个新旧社会的政治大转型时代,格劳秀斯和魏源都各自基于自己的国家状况提出了全新的政治图景和社会构想。令人喟叹的是,当格劳秀斯的海洋法权学说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近现代思想领域之巨人,更转化为今天欧美各民族国家构建法政制度以及国际法秩序的思想资源,而魏源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了无回应,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转化为我们思考中国政法问题的活的精神”(高全喜语),这是时代之病痛呢,还是历史之顽疾?
洛克向左,穆勒向右:
如何勘察政府的“边界”?
如果说格劳秀斯是引导西方社会从中世纪思想观念进入现代社会的“破冰者”和领路人,那么随后出现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和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无疑是现代政治制度大厦的思想建构者,无论是洛克为17世纪英国经历光荣革命之后早期的现代政府的辩护之作《政府论》,还是穆勒为19世纪英国成熟时期的现代政府小心翼翼地勘察边界的《论自由》,对于当下的中国政治实践,都有着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
1903年,晚清思想家严复曾经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界限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事实上,严复从1899年就开始翻译这本小册子,期间经历庚子之乱,译稿在避难途中一度丢失,后又复得。考虑到中西文化之间巨大的观念鸿沟,严复在翻译时颇费心力,常常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与他5年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被热烈讨论的命运完全不同的是,《群己界限论》显然超越了当时国人的关注焦点,出版后少人问津。
在高全喜看来,从洛克到穆勒,正好是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走过了一个从早期现代阶段到成熟现代阶段的转折点。洛克作为当年英国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师,其《政府论》旨在为新生的英国政府权力提供正当性的理论来源,为此,他从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个人权利来提出契约型政府的合法性论据;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19世纪之后,穆勒已经看到了现代政府的权力危机——如何限制政府和社会的权力,避免“多数者暴政”,为真理的自由讨论和现代人的个性发展留下更多的空间,为人性的内涵向更丰富的拓展创造条件,进而为英国社会保全其更加活泼的生命力,成了一个迫切的议题。
在穆勒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尊重普通民众个性自由发展的社会,他在《论自由》的最后一章写道:“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洛克向左,穆勒向右,在高全喜看来,这些作品里尽管反映出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印记,但它们都“不仅仅是学问之作,而且是思想之作;不仅仅是历史之作,而且是现实之作”。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可逆转之命运过程中,如何借鉴、融合和创新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理论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更新,这才是重中之重,不管怎样,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无一不是处在一种更新的政治观念的观照下进行的。诚如涂尔干所形容的那样,人们眼中看到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世界之间的种种冲突,毋宁说是两种不同社会理想的冲突,是“昨日理想与今日理想的冲突”,是“传统权威之理想与未来希望之理想的冲突”。
一切伟大的社会实践,必须先基于一种伟大的社会构想。就此而论,《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堪称是一部“苦心孤诣”之作,它在每一处字里行间闪耀的思想火光都在提醒我们,中国当代社会如果要走出“古今之变”“中西之辨”的种种现代性困境,不仅需要放眼看世界,更要学习从世界角度重新审察中国的价值立场、思想变迁和社会实践,这一进程必然要期待一场更大范围且更加持久的思想启蒙,启蒙远未成功,同仁仍须努力。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