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姜昊骞/文
“一个大架仔”
作为一名译者,“信达雅”的衡量标准自然是时常挂在心头。严复原本讲得很简略,“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按照通常的理解,信就是“准确”,也就是译文与原文的意义应当一致,不能有增减移谬。对于大部分文本来说,一种朴素的符合论意义观就足够翻译之用了。美国数学家理查德·蒙塔古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普遍语法”,用逻辑学家的形式语言来构建自然语言的模型。对语言哲学家来说,蒙塔古语法往往用于解释某一个具体的语言现象,因此必须要做精确地定义和推导。
对译者来说,这套乍看起来过于简陋和刻意的模型恰恰是相当优雅地表达了我们的朴素直觉:世界由物体组成,词语指代单个物体、多个物体或者物体之间的关系。于是,一句话翻译得准不准,或者说信不信,就看译文里讲到的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是否与原文对应。以这个易用且明确的模型为中介,源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可以建立起一座座名为映射的桥梁。我知道这不是现在走通的AI翻译的模式,但对人工翻译来说,蒙塔古语法所代表的意义观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底层逻辑。
不过,《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这本书里讲述的内容却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在性质上类似于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惊醒:上一段描绘的优雅模型在一些情况下完全不适用。这种来自历史的厚重冲击是哲学理论难以匹敌的。哲学理论往往要么针尖绣花,要么九重云霄,要么绕场三周半,总之一个缺乏慧根的译者总可以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来打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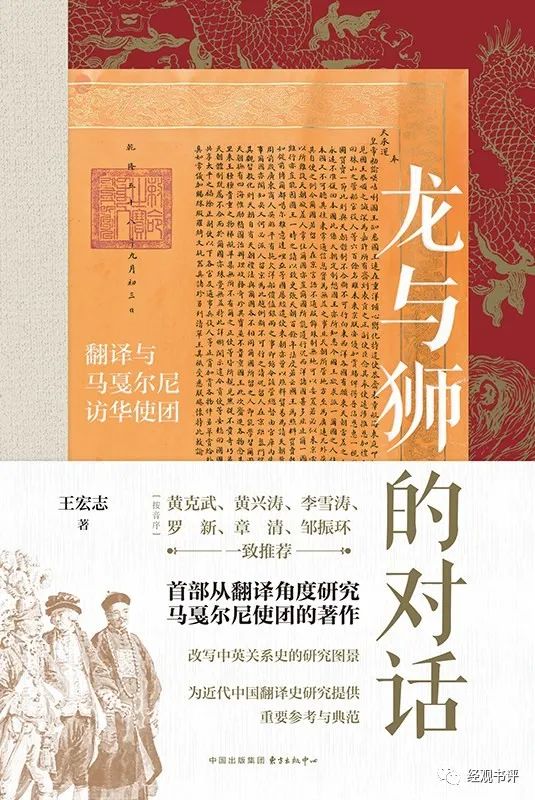
《龙与狮的对话:
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王宏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
但就算一个译者再愚钝,读到这句话时恐怕也不会没有触动:“对于‘布蜡尼大利翁大架’这样的译法,我们不应对译者过于苛责……但从效果上说,这件本来是英使最贵重且寄予厚望,以为一定可以打动乾隆的礼品,却因为翻译的问题而无法有效地传达重要讯息,从马戛尔尼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不理想的。”
我所受的触动主要不在于所谓外交无小事,毕竟我不是英国使团或者满清朝廷的人,而在于这种例子指出,翻译中采用的意义模型有时必须加入新的参数,而一旦加入这些参数,“信”,尤其是“达”的标准就会一下子变得混沌起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标准本身消失了,因为王宏志教授的分析恰恰指明了所需要补齐的短板——蒙塔古主义译者从此多了一项需要掌握的判断技能:何时用简单的符合论模型就够了,何时必须切换到复杂得多的意义模型。接下来,我要结合马戛尔尼礼单的例子来略作讲述。
马戛尔尼的目标是在平等交往的前提下为中英贸易争取便利,为此需要塑造英国强大,英王崇高的形象,这也正是使团抵京前呈交礼单的用意。于是,单子上第一项,也是最贵重的一项礼品是著名仪器工匠菲利普·马特乌斯·哈恩耗费30年建造的“哈氏天体仪”,拉丁文写作Plantarum,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布蜡尼大利翁”。有一台现藏于德国国家博物馆,乍看上去只是一个大架子上摆着三个表盘,周围有三个小的天文仪器,应该是能看到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之类。事实上,乾隆派去查验礼品的官员大体上就是这么回报的,只是像木匠一样把大架子高九尺八寸之类的信息记录甚详。若要理解天体仪的神奇之处,就必须明白它是当时欧洲最新的天文观测与理论的精确呈现,包括显示日食与月食、土星的光环和五颗卫星、月球环绕地球的椭圆不规则轨迹等。
为了给乾隆一点科学的震撼,马戛尔尼特地为天体仪补充了长篇的专业解释。可惜,不仅补充进去的话漏译了,礼单本身的译文也极其简陋,称得上将“简化”策略运用到了极致:“一座大架仔,西音布蜡尼大利翁,乃天上日月星辰及地裘[球]之全图,其上之地裘[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且不说礼品名称的不用心,后面笼统的描述自然很难让乾隆看到其中蕴含的奥妙,而只会让人觉得它是中国早就有的浑天仪之类物件。难怪乾隆会认定马戛尔尼“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
译者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欠缺天文学知识,更在于不了解马戛尔尼的意图和乾隆的知识面。简单来说,译文应当用不容更改的科学真理营造出不容置疑的权威光环,重点是让乾隆意识到,马戛尔尼背后是一个昌明强国,它拥有泱泱中国所无的知识和力量,但又愿意与大皇帝分享,以示交好之意。
“博学人里挑出来一个大博学人”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给出了一个更适合分析此类现象的框架。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12节的课程,讲稿结集为《如何以言事》,其中第八讲将言语行为分解成三个层面: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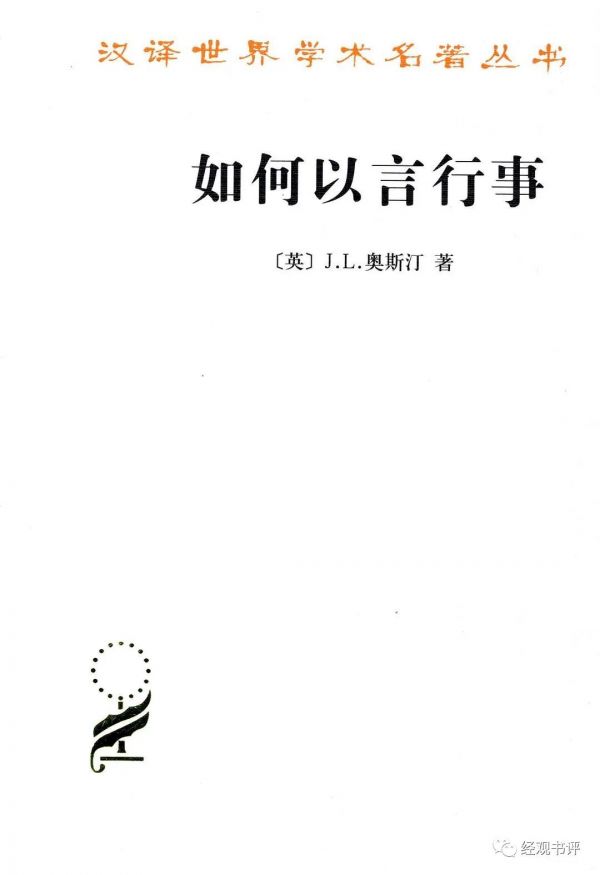 《如何以言事》
《如何以言事》
[英]J.L.奥斯汀/著
杨玉成 赵京超/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3月
话语行为就是发出属于一门语言的声音,略微推广的话,在纸面上写字也可以算。严格来说,似乎只有一个人明确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的时候,他写下的字才算得上是话语行为的结果。《龙与狮的对话》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名叫斯当东,时年13岁的斯当东的侄子也一同前往中国。小斯当东颇有语言天赋,在伦敦学过一年中文。上一节里提到的礼单中文译本就是他誊抄的,有人评价说,小斯当东“写中文比写英文还要工整”。不过,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译者,比如使团离京后,他将一份英文感谢信翻译成中文,用负责信件转交的时任广东巡抚朱珪的话说,“虽系中华字书,而文理桀错,难以句读”。无论是誊抄还是“翻译”,小斯当东的行为都难以算得上言语行为。相比之下,不管“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看上去如何诘屈聱牙,但元朝的硬译是符合言语行为的标准,只是需要读者略微习惯而已。
不过,真正给马戛尔尼使团带来沟通困难的地方显然不在于言语行为层面。毕竟,使团呈交的译文绝大部分都符合语法,所用也是正当的汉语词汇,中国官员和乾隆都能理解文书的字面含义。上一节中主要涉及的是奥斯汀三分法中的“话语施效行为”,也就是“[说话]后对听者、说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并且在说这些话时可能原本就有计划、有意图、有目的地创造这些影响。”
传统上,这主要是修辞学的研究范畴,有时哲学家会批判过分追求效率的做法是巧言令色,偏离真理,但对身怀外交使命的马戛尔尼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他就是想用语言和文字的力量打动清廷,只可惜被翻译坏了事,完全没能让乾隆感到自己与英王是同气连枝的大国君主,反而夯实了“红毛”是海外小邦,乔治三世是“海主”的固有印象,尽管海主对应的原文是LordofSeas,最起码也是个“王下七武海”或者“四皇”的境界。当然,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假如马戛尔尼果真让乾隆产生了他想要造成的印象和情绪,那使团大概就不只是徒劳无功,就连能不能平安离开中国都成问题了。这便涉及到了“话语施事行为”。
奥斯汀在讲座中的界定比较简单,就是“我们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言语”。从分析哲学的标准来看,这压根算不上一个定义,因为正如奥斯汀本人指出的那样,短短一句话里用到了“意义”和“使用”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含混词汇。不过,对应到这次龙与狮磕磕绊绊的对话中,这个概念就具体化成了一个问题:马戛尔尼交上去的文书是国书还是纳贡表文?
从马戛尔尼的立场来看,他自然是在递交国书,《龙与狮的对话》中对原文和译文做了精当的对照分析。比如,原文罗列了马戛尔尼的头衔、使命和履历,懂英文的读者会感受到一种类似《权力的游戏》里龙妈头衔的感觉:“乔治·马戛尔尼子爵阁下,利森诺尔男爵,大不列颠王国枢密院成员,最荣耀的巴斯骑士团骑士,最古老的皇家骑士团白鹰骑士团骑士……曾代表朕出使俄罗斯宫廷,曾治理朕在东方与西方的若干极大领地,曾任孟加拉总督……”纵使乾隆君臣不了解其中提到的部院、职位、地域都是什么意思,至少能够直观感受到对方在努力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在清廷看到的译文中,马戛尔尼却仿佛是一个跑腿的小官:“从许多博学人里挑出来一个大博学的人(指马戛尔尼入选伦敦皇家学会一事)。他从前办过多少大事,又到俄罗斯国出过差,又管过多少地方办事,又到过小西洋本噶蜡等处属国地方料理过事情。”译文的最大问题是完全扭曲了文书的性质。这篇文书的译者是广州行商通事,他是按照常见的进贡表文来翻译的,因此通篇都将英国置于番邦小国的定位。鄙俗含混不仅仅是译者水平有限,更受制于立场,所以对皇帝要极尽恭维之能事,对英国则要力言其卑微渺小,与国书原文可谓南辕北辙。
当然,在今天的绝大部分文本翻译中,如此极端的扭曲相当少见,更不会被提倡。但它以一种最激烈的形式传达了一个涉及译者主体性的普遍问题:我在做的是什么事?是劝告,是陈述,是讲解,还是宣布?在一切知识背景和文体考量之前,这永远是先决性的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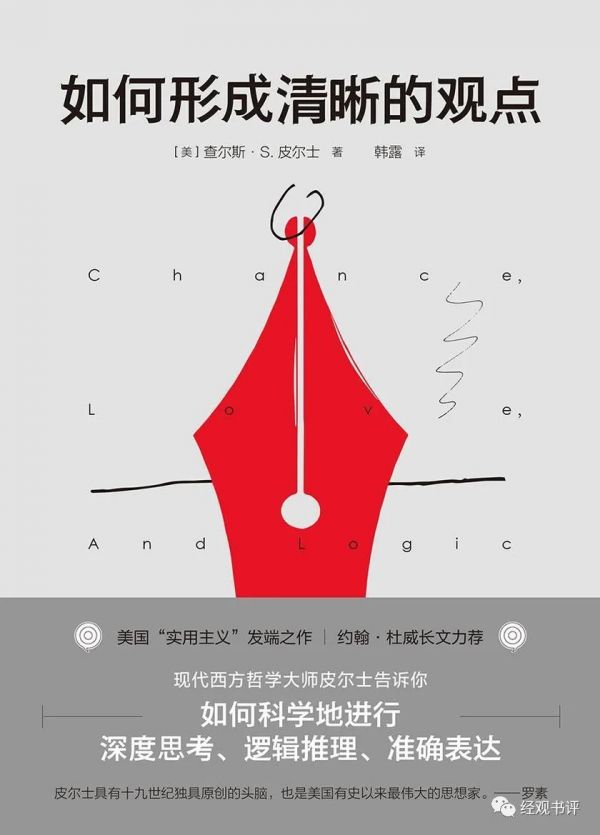
《如何形成清晰的观点》
[美]查尔斯·S. 皮尔士/著
韩露 /译
巴别塔文化|天地出版社
2019年11月
译者的立场
既然提到了立场,又是外交场合,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立场,尤其是忠诚问题。马戛尔尼最倚重的译员李自标出生于甘肃省,来华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所神学院(今中华书院)学习,已经取得神职人员身份,恰逢马戛尔尼寻访译员,便加入使团。李自标尽管不懂英语,文言文水平也比较一般,但用汉语与中国官员沟通不成问题,且熟练掌握拉丁文,能够与出身贵族的马戛尔尼等人交流,可以将拉丁语文书翻译成堪用的书面中文。使团大部分成员对他评价颇高,马戛尔尼认为他“是一个十分理智的人,意志坚定,具有良好的个性”。
然而,李自标来华的最主要动机其实是传教,这与马戛尔尼的通商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带来的最大风波是,李自标曾瞒着马戛尔尼,以口头方式向朝廷请求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待遇,结果立即引起乾隆的警惕,向使团下发了措辞严厉的敕谕:“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马戛尔尼自然一头雾水,但最终也没有怀疑到“诚实且能干”的李自标头上。虽然从上帝视角出发,我们知道马戛尔尼追求的通商目标也不可能获得清廷应允,但李自标的自作主张仍然对使团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
不过,“立场”一词的理解可以适当宽泛一些。立场,就是希望某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变得更好。李自标滥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译者身份,这无疑是自私的,充其量只是为了天主教徒这一个群体的利益,哪怕他真诚地坚信天主教是唯一的真理。这不是一名译者应当采取的心态。相比之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在1878年《大众科学月刊》上一篇题为“关于偶然的学说”的文章里的一句话颇得我心:“无限群体的利益、认同这种利益至高无上的可能、对思想活动无限延续的希望,这三个方面[是]逻辑不可或缺的要求。”
这本探讨逻辑学、数学、物理学、进化论等科学议题的小书里有一条贯穿的暗线,那就是理性思考不是单调僵死的观察、归纳和演绎,而必须至少相信自己是为未来将会出现的无数人类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信念本身是无理可循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早已在无数小说电影中见过人类毁灭或者濒临毁灭的21世纪网民来说。当然,在大多数翻译实践中,这样崇高的理想不会浮现在译者的意识里,有时甚至可能与眼前的利益相悖。但在我看来,皮尔士的表述恰恰表述了一位译者的理想立场。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