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陶力行/文
虽然中原农耕政权被外族侵占的情况不少,如拓跋鲜卑立国北魏、女真满族立国大清等,但这些入侵者多位居中原东北部的草原、平原与森林的混合地,且其入侵都发生于中原统一政权临危、松动或崩溃之时。就中原北部的草原游牧政权而言,他们鲜有入驻中原,虽然攻击中原是一种常态。从千年尺度看,草原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政权之间大致保持平衡。而且,两者还时常呈现出周期性共振。然而,历史总有意外。蒙古的横空出世破坏了游牧与定居之间的“平衡律”与“共振律”,其不仅将整个中原政权吞并,还建立起了前现代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放在草原政治框架下,蒙古是一个特例。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做出了解释,其观点可作如下概括:草原政权的基本单位是以血亲为基础的部落,由于血亲的先天性和不可跨越性,由部落组成的草原帝国多是行动能力有限、结构松散的联盟性帝国,但成吉思汗打破了血亲原则,其通过“重族伴轻家族”的做法建立了一支扩张性更强、效率更高的军事力量,其继承者又利用这一力量缔造出了横跨整个内亚的蒙元帝国。
Barfield得出结论的方式并非基于蒙古内部视角的历史回溯,而是跨时空的历史比较。他将上述观点嵌入在以下两个观点之中:(1)草原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是共存的,组织形式是共振的,即要么同时“合”,要么同时“分”;(2)蒙古是草原政治的偏离,一旦蒙元帝国垮台,草原政治与中原政治又会恢复至共存。
为论证上述内容,《危险的边疆》将考察尺度拓宽至两千年,依时间序列分析了不同的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包括匈奴与汉、突厥与隋、回鹘与唐、瓦剌和鞑靼与明等——的互动过程,并对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帝国之间的共存性、蒙古的崛起、草原政治的最终没落、外族占领中原等现象做出了描述和解释。虽然该作体量庞大,涉及政权对象甚多,但仔细阅读可发现,作者的核心落脚点是蒙古。
一
《危险的边疆》初版于1989年,在当时语境下,该作有多处创新,可归结为四点。第一,将考察视野延伸至游牧内部,平衡了过往研究中过强的“中原中心主义”。虽然游牧政权在军事方面很强大,但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均不如中原政权,因为经济与文化是累积性发展的产物,而游牧的流动性不利于累积。其结果是,根据材料说事的后世研究者会不期然地将中原立场作为叙事起点。
Barfield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将碎片化的游牧信息整合,提供了对冲中原视角的叙事。例如,他指出,在中原政权看来,所有游牧政权都是虎视眈眈的侵略者,但在游牧政权眼里,中原农耕政权只是一个合适的敲诈对象而非征服对象。Barfield认为,征服意味着管理,而对游牧政权而言,管理农耕政权是件吃力不讨好之事,与其杀鸡取卵地征服,不如百试不爽地敲诈。
第二,用共存观或相互依赖观代替对立观。传统观点从对立角度解读游牧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关系,但Barfield从战略角度否认了这一说法。他指出,游牧部落因为讲究血亲原则,相互之间通常会有较强的排他性,即便组成帝国联盟,各自依然会保留较强的自主性,这意味游牧政权虽然在军事实力方面胜于农耕政权,但不会将后者树立成“永恒的敌人”,因为游牧社会的内部张力会使任何一个游牧部落都有陷入两线作战的可能。
为说明两者的共存性,Barfield在解析游牧的国际政治战略时,区分了针对中原的“外部边界战略”以及针对草原的“内部边界战略”,并指出两种战略相互联动。例如,当游牧政权联盟成草原帝国时,帝国首领会敲诈中原政权以获取维系草原联盟的资源;当草原内战兴起时,各游牧政权又会尝试与中原政权结盟,以求重建草原联盟或制衡其他游牧政权。Barfield的意思是,“游牧帝国联盟只有能将自身与中原经济相联系时方能存在”。
第三,用三分法代替二分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想象。传统研究采用二分法,即将内亚国际关系叙述成游牧政权与农耕政权的拉锯。对中原政权来说,如此叙述合情合理,因为中原政权眼里的所有北方外族均是同质的“蛮夷”,但引入地理分析后会发现,外族内部其实也有差异,有些外族能够入驻中原,有些外族却只能止步于中原之外,且所有成功入驻中原的外族,除蒙古以外,均发轫于中原东北部。二分法无法解释这一差异。
Barfield重新区分了内亚政权类型,即位于中原地区的汉人政权、位于草原地区的游牧政权以及位于中原东北部地区的混合态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内亚国际关系的循环论以及蒙古例外论。所谓循环论,是指“中原农耕帝国和草原游牧帝国几乎同兴同衰,以及衰落之后,位于中原东北部的半游牧政权会立马乘虚而入进驻中原”的过程在两千年内亚历史中重复出现过三次。所谓的蒙古例外论,是指蒙古作为草原部落成功入驻中原,打破了外族入驻中原的东北惯例。
第四,行动者视角与结构视角相结合。结构论者通常假定历史结果是特定条件汇聚的结晶,叙事上采取还原论。例如,Lattimore注重文化条件,在解释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政权的不兼容时,提供的说法是草原游牧社会没有“文化英雄”;在解释蒙元政府为什么可以部分架空文人官僚时,说是蒙古吸收了喇嘛教文化,找到了替代品。但在Barfield看来,这些说法由于缺乏视野比较显得很不可靠。
结构会对个体起作用,但不会对所有个体起相同作用,一旦某一结构下的个体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分布时,结构论就会立马捉襟见肘。蒙古原本只是一个小部落,而且是草原诸多部落之一,但从十二世纪下开始不断壮大,不断吞并其他部落。从Barfield的眼光看,蒙古与草原其他部落的外部条件极为相似,如果只关注结构而不关注行动者,即成吉思汗本人的能动性,那就无法理解蒙古与其他部落的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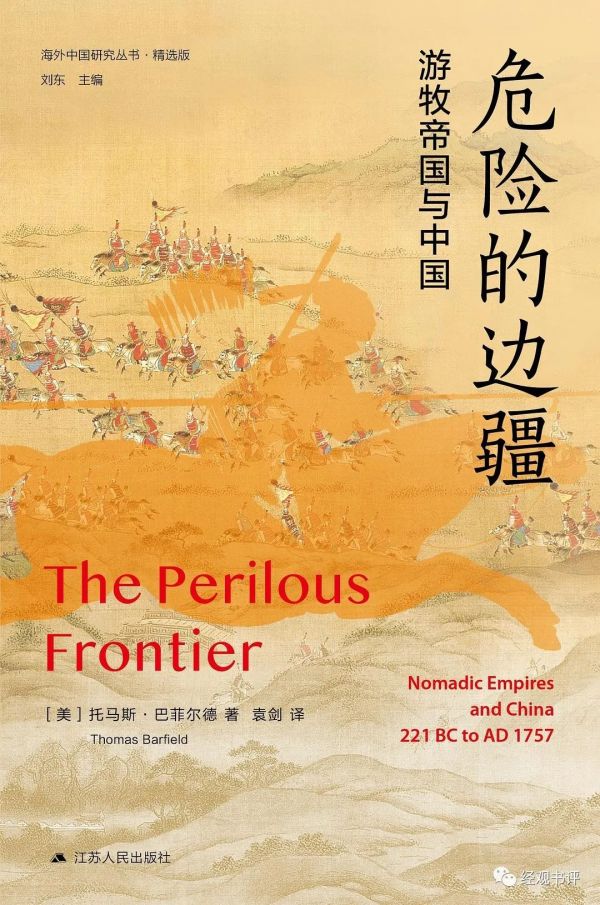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著
袁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
二
就上述四点而言,《危险的边疆》算得上是一部具备宏大视野且有理论指向的创新之作。但是,这不意味着该作没有改进空间。接下来,我将批判性地分析一下该作。
第一,“把游牧政权的攻击行为定性为敲诈而非征服”就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基于动机论的解读。研究者可以观测行为、猜测动机并根据猜测推理行为,但不能言说动机,原因有三:一、动机只是行动者证成行为的心理宣称,但所有心理宣称都不可考察;二、心理宣称和行为并不一一对应,一个动机可产生多种行为,不同动机也可促成同一行为;三、动机总是在变动,行动从启动至完成,行动者可以不断嵌入新的动机,以至于动机性表述即便由行动者本人坦白也会显得不那么可靠。
一个行为最初可能是为了敲诈,但如果攻击行为能够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那目的就有可能升级为征服。同样可能的是,一个行为最初是为征服,但久攻不下后,目的被降级至敲诈。这里值得讨论的并非如何定性攻击行为,而是如何描述及解释攻击行为的发生频率、发生方式和强度。如果游牧的攻击行为多止步于既定边界,那旁观者似乎只能假定:游牧政权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没有军事优势,即所谓的平衡律及共振律,只是两者军事实力相当的表征。
然而,Barfield没有对两者军事实力的对等做出解释。这种不解释不是Barfield独有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学者共有的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原政权相对于游牧政权的优势,只用“视觉直观”做出判断。关于农耕政权的军事优势,可参考赵鼎新《儒法国家》中的说明,即“相较于贫瘠的草原,农耕区的土地有更强的生态承载能力,这就使农耕者有发展打败对方的军事实力和有可能吸收同化对方的人口优势”。反之,游牧政权因为没有强大的物资储备能力,缺乏打持久战的能力,所以多有敲诈,鲜有征服。
第二,历史循环论是一种忽略细节的粗暴归纳,而非规范性表述。循环论的语法只适用于“刚体”行为的表述,如太阳绕着地球转,钟摆现象等。放在历史学不合适——无论是国家还是组织,都是有机体而非刚体。
相对于人的目光而言,刚体高度稳定,而有机体总是在变动。如果历史学研究者想引入循环论语法,就必须将非刚体说成是刚体,带来的结果就是简化甚至取消历史细节。Barfield在叙事游牧帝国与中原帝国的共时性时就以忽视历史细节为代价。他之所以会归纳出共振现象,是以漠视“不同政权以不同原因建立或以不同原因溃败”这一事实为代价的。
第三,错误的解读夸大了中原政权对于草原帝国稳定的意义。Barfield认为,游牧帝国之所以会敲诈中原但鲜有征服中原,是因为不征服可以令其持续性地从中原那里获取维系帝国完整性的资源。这一观点是从功能主义角度解读敲诈,并不可信,因为游牧帝国的形成总是发生于敲诈得手之前,研究者无法从时间序列上判定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
其实,草原帝国一旦形成,即便没有敲诈也未必会有帝国的崩溃。如Barfield自己所言,游牧帝国从中原帝国那里获取的物资通常只会被分配于帝国下的各部落精英。对于这些精英而言,获得分配是一种因接受联盟而获得的附加性奖励,但这些精英之所以愿意接受联盟,是因为联盟可以令其免于中原帝国给予的恐惧。在历史过程中,附加性奖励的意义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免于恐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也是难以测量的。
第四,认为“血亲原则是游牧部落的专属”以及“蒙古削弱血亲话语是成吉思汗个人意志的表达”存在问题。血亲原则是筛选个体的话语标准,由于血亲的先天性和不可超越性,血亲话语本身就意味着封闭性,即一个群体流动性越弱、同质性越高,其越会讲究血亲话语。但是,封闭性并非游牧社会的独有特征,而是所有小规模社会的共性,农耕社会规模小的时候也会讲究血亲,例如农耕社会的长子或嫡子继承制。
这里值得讨论的是:在何种情况下,血亲话语在统治阶级内部会被削弱?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当群体规模在短时期内因战争吞并或商业流动迅速扩大后,血亲话语逐渐削弱是一种常态性现象,就这点而言,成吉思汗削弱血亲话语本身,就是由其领导的部落不断扩张的附随物。
第五,夸大了成吉思汗的个人作用,将蒙古军队的组织性、效率以及战斗力解释为“成吉思汗因为在乎族伴而拥有更多的追随者”的结果存在问题。追随者之所以会持续追随某条路径,是因为这条路径能带来正向反馈,追随者一旦获取不了正向反馈,就会随之离去。因此,要说明蒙古军队的高战斗力需要提供更宏观的结构性理由。
其实,中原东北部的政权之所以比草原政权更容易入驻中原,是因为东北部是草原、平原以及森林的混合态,其多样的生产模式赋予了东北部政权比草原游牧政权更多的行动弹性。就这点而言,蒙古只需不断扩大自己的行动弹性,其入驻中原的概率就会提高。回溯历史可发现,蒙古的扩张确实是一个不断收编农业经济,不断扩展自身补给能力,不断摆脱草原性,不断积累与农耕政权作战经验的过程。
Barfield虽然是一名人类学家,但在写作时不断引入比较视野,所以读起来会有社会学之感。引入比较视野的好处在于能够有效屏蔽作者自身的价值偏好、快速剔除大量干扰因素、准确抓取关键变量,但其难度在于如何选取合适的事实进行比较以及如何准确地解读这些事实。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依旧会给对方辩友打开诘问的后门。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