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7日晚上,我对着《深圳旧志三种》一书发了一会呆,然后决定给校勘整理者张一兵打个电话。我对2006年海天出版社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充满好奇,前几天已经和责编之一于志斌联系上,了解到一些内情。欲知更多故事,我还需要和一兵大哥聊聊。

“一兵大哥”这个称呼,我是跟着挚友姜威叫的。张一兵和姜威是黑龙江大学的校友。南下闯深圳的“黑大”毕业众同学相互联系很热络,显得异常抱团,好像离家越远,同学这层关系就越珍贵。姜威酒局的发动原因,几乎有一半与“黑大”有关,他介绍过很多师兄师弟和我认识,初次见面的场合大都是酒桌。酒桌上认识的朋友,姓名容易记不准,要么是一方已经喝高,要么是两人争酒斗醉,再次见面时往往还是分不清谁是谁。从头再来!先罚一杯“加深印象”酒,一杯下肚,感情已经深似海,所以喝它个“一口闷”,再喝一搜“巡洋舰”,然后执手相看醉眼,痛心疾首,掏心掏肺,有难同当,海誓山盟。看起来就要抵达“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之境界,谁知换个日子换个酒桌再次相遇还是“似曾相识燕归来”。黑大之黑,频频举杯,先到者已醉,后来者可追。
身兼东北人与黑大校友,张一兵却不喝酒,任你山呼海劝,他自岿然不动杯,这让我印象深刻。印象更深刻乃至让我大吃一惊者,是他出版了一本《深圳古代简史》。记得那是1997年,姜威把大家招到一起,以庆贺新书出版为名,大喝其酒。我接过张一兵工工整整签名送我的新书,嘴上没说,心里有些不以为然:深圳还有古代史?硬编的吧?和洛阳、西安怎么比?那时候我正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发动各方高人讨论深圳文化。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当然不同意,但说深圳“历史悠久”,我那时也持保留意见。“大侠你不对,”一兵大哥认真地说,“你这看法不对。我原来也不熟悉深圳,我也认为深圳没历史。我是来了深圳,整这本书,才改变了看法。你看看我这本书就明明白儿白儿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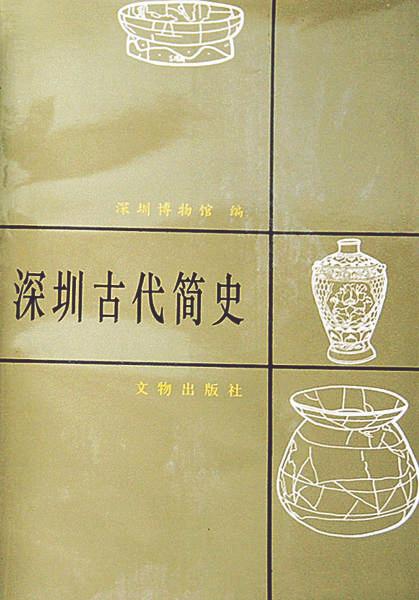
张一兵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常提到,来深圳之前他对此地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所知甚少,也以为这里不过是个落后的边陲小镇,至于古代,一片荒地吧。他来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偏偏就是在深圳博物馆研究深圳历史。接触到原始史料后,他的看法改变了:深圳不仅有历史,还有十分富有特色的古代历史,这些历史是跟当时中国发生的历史大事联系在一起的。他经常说,深圳地区的繁荣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那时候朝廷在各地设立盐官,第一个盐官就是南海郡的番禺盐官,汉代的番禺最东面的辖区就是深圳地区。至今考古界在现在的番禺都没有发现古代盐场,所以古盐场应该分布在深圳、东莞一带。由此看来,深圳地区是汉代主要的食盐产地之一。北宋初期,深圳、东莞地区的盐场每年大约产盐132万公斤……。
像这类表述,他脑子里装了太多模版。一旦话题有迹象转向此方向,他马上滔滔不绝,娓娓道来;然后话题会开枝散叶,但不管如何跑题,都跑不出深圳史范围。2月7日晚上我和他通话,因话题所限,我经常需要打断他自己衍生出来的讲述。我心里也清楚,如果时间充裕,听他古今中外地“满嘴跑深圳火车”,一定过瘾。
他太熟悉深圳的历史了,建筑、文献、地名等等,他都熟悉。电话里我们俩开聊不久,他就说到一个地名,说这个地名困扰了他很多年了,到现在也没解开,只有个猜测。“这是个村儿,村名,叫象角塘,就在坂雪岗大道一侧……”
“坂雪岗大道?”我赶紧截断他,“大哥,我就住在坂雪岗大道一侧啊,我怎么不知道象角塘?”
“大侠啊!你住坂田啊。”张一兵笑了几声,“我也住坂田啊。”
“嗨!”我叹了口气,“原来是邻居啊。那象角塘在哪里?”
他说了一堆村名,用来互相证明各自的方位。我哪里知道这村那村,所以我还是不知道象角塘在哪里。不管了。“这个村名有什么特别?”我问。
“你想啊,深圳有过大象吗?我找不到文献证明深圳有大象生活过。即使有,大象有角吗?你见过长角的大象吗?那么,象角塘这个村名是什么意思呢?”
我茫然。做梦我都梦不到这样的问题。
“我猜啊,”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在“猜”,“这个村子原来有一道石崖,东北叫石砬子,深圳这边叫嶂。这个村,就在这个嶂的脚下。现在已经见不到这个嶂了,我猜是采石给采平了。你听明白了吗大侠,嶂,象,在白话里是同一个读音。以讹传讹多年,嶂就成了象;而广东话里角和脚又同音,同音一再讹变,就转不回去了,就成了象角塘了。猜测,我这是猜测。找不到证明。”
我突然想起,他现在有个新职务,是深圳地名学会的会长。
【待续】
胡洪侠/文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