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1978年生于江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 Hart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曾任人大科研处副处长、国家发展与战略常务副院长。他主要研究政企关系、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等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他于2008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国家“万人计划”),2014年入选第七批“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 ,201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他向中央提交的反腐败、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僵尸企业和官员激励的多篇内参,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他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以及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社等中外重要媒体的采访。
林佳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博连读生。
1、很多人对您的传奇经历非常好奇,那么您当年是怎么选择了经济学研究之路呢?
聂辉华:我1978年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的一个贫困农村,在我之前全村没人考上大学。家里人口多,因此经常入不敷出。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是食物匮乏。最痛苦的是初中阶段,经常一个星期只能吃一罐干巴巴的豆子或者一罐很咸的萝卜干,青菜都是稀缺品。幸运的是,父母一直支持我读书。我小学成绩名列前茅,初中有点贪玩,成绩中上,第一次中考时没有考取高中,那年全班只有三个人考上高中。初三复读,幡然醒悟,成绩再次名列前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考取中专或师范学校(“中师”)的话,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因此成绩最好的农村学生为了“铁饭碗”会报考中专,而上大学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令人伤心的是,就在我第二次参加中考的1994年,国家规定复读生不能考中专,于是我的中专梦破碎了。更令人伤心的是,虽然我中考分数名列全乡第一,但是被分配到县二中。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而县二中是普通中学,一个高三文科班只有一两个人考上大学(当时全国高考录取人数是80万左右)。幸运的是,当时一中刚退休的老校长周德清被聘为二中校长,二中又有希望了。高二时我选择了文科班,成绩可谓一骑绝尘,甚至有一个学期五门功课全部第一。我1997年参加高考时,江西省实行考后估分报志愿,周校长问我选什么学校。我说选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最好的文科大学。校长建议我选人大法律专业,我说现在法制还不完善;校长又建议我选人大新闻专业,我说很多新闻太空洞。最后校长问我选了什么专业,我说“工业经济”。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前景肯定不会差。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我还选择了提前录取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过学校操场时,我碰到了校招生办主任。他说这个学校规模比较小,于是我删除了,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志愿了,我好像还选择了“不服从调剂”。
1997年8月,我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人大工商管理学院工业经济专业录取,这打破了过去十四年全县文理科状元被一中垄断的格局。但我一直坚信:聪明+勤奋+运气=成功。如果我考取了中专,如果没有周校长,如果招生办主任没有提醒我,如果抚州市其他排名前十的“高手”也删除了提前录取,我肯定不会被人大录取,那么人生将是另一个版本。老子说的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没有谁的人生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们要在悲观中寻找转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大学四年,我最自豪的事情是,除了大一那年拿了家里的钱,从此我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学费,并且每年还给家里寄几千块钱。我做过编辑,卖过教材,当过家教。烈日炎炎,风雨雷电,苦不堪言。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好好学习数学和英语,部分原因是课余时间都在打工挣钱。我后来考研和考博,分别因为数学和英语分数不高而破格录取,出国也受影响。最受益的事情是,听了樊纲、周国平、从维熙等很多名人的讲座,开拓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在上大学之前,我是应试教育的标准模板,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个字。
我最后之所以走上了经济学研究道路,是因为环境、兴趣和信心三个因素。一是穷则思变,希望通过经济学研究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经济学家茶座》上的文章《“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指出很多知名经济学者都是江西人,例如人大的吴晓求,北大的姚洋和周黎安,我想这可能跟江西比较贫穷有关。二是大学期间听了很多经济学的讲座,看了一些经济学的启蒙书籍,比如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经济学有浓厚的兴趣。三是我大二就在核心期刊《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需求不足,责任不在百姓》,增强了研究经济学的信心。
2、您早年是研究企业理论,后来研究矿难、腐败、僵尸企业和城市问题。请您谈谈你的研究进路、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基于您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的多篇论文,您有哪些研究体会和心得?
聂辉华:我读本科时(1997-2001年),从西方引入的博弈论、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风靡一时,那也是研究国企改革和制度变迁的黄金时期。我因此对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试图在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框架SCP范式下引入产权,构建一个SOCP框架。2001年,经任课教师引荐,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海舰研究员门下。社科院的研究生课程不多,于是我们2001级硕士生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会”,我是会长。我们每周讨论论文或著作,还辗转好几趟车去北大听课。一群人在一起奋斗,会使得“优秀成为一种习惯”。2002年春季,李老师带我去广东南海调研陶瓷产业。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调研。接待我们的乡镇党委书记说:“如果中国的企业都100%纳税,那么一半的企业要死掉!”我当时被这句话震惊了,这成为我后来坚持实地调研的动因之一。由于破格录取需要缴纳昂贵的学费,于是我提前一年从社科院毕业了,并于2003年考入人大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硕士论文探讨了一个纯理论问题,把企业理解为“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企业之所以有粘性,是因为所有者掌握了具有稀缺性和专用性的资源,未必是物质资本。这个观点与我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经历有关,可见实践出“真知”。硕士论文的核心内容2003年刊登于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这成为我坚定地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重要动力之一。
进入博士阶段,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契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读博士期间,我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等期刊上发表(含接受)了七篇论文,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难以超越的发表记录。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我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两篇综述文章,而影响最大的是我和李金波2006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我们在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三层代理框架中,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会同时出现高增长和多事故。这个“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可以广泛地解释矿难、土地违法、环境污染、偷税漏税和僵尸企业等现象。
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我才开始自学计量经济学。从零开始,不懂就问,边做边学。迄今为止,我们团队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表了十几篇经验文章。我们撰写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成为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必读文献,在中国期刊网上引用次数超过1000次。我们关于矿难的经验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JCE)和国际顶级期刊《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Stat)。2016年,我们团队发布了第一份完整的中国僵尸企业报告,它成为研究僵尸企业的必读文献。我们早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关注腐败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也成为热点,以至于国内外很多期刊都将这方面的文章发给我评审。近年来,我开始关注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我们2018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文章《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提出了一个鲜明观点:人跟资源走,而资源跟权力走。因此,要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和城市病,首先要疏解权力,让城市之间公平竞争,而不是仓促放开人口流动。2019年,我们在《比较经济学杂志》(JCE)上论文分析了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篇文章被美国NBER网站放在首页推荐。
总结起来,我的研究进路可以概括为:一个思路、两种方法、三个原则。一个思路是指,采取前沿的契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坚信,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所谓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与国家、政策、权力和制度有关的问题。两种方法是指,一方面坚持做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坚持做经验研究,并且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三个原则就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关于做一流研究的心得,我最推崇张五常提出的五个条件:(1)没有立场,分析问题时主要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避免“屁股决定脑袋”;(2)没有偏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各种可能正确的观点;(3)逻辑严密,分析问题环环相扣,没有漏洞;(4)观察敏锐,善于从新的角度发现问题;(5)品位独特,敢钓学术上的“大鱼”,不是为了发表而写作。除此之外,我没有废话可说。
3、大家总说中国是经济学研究的宝库,但从来没人教坐拥宝库如何识宝挖宝。您作为“土鳖”学者的杰出代表,能不能以您提出的“政企合谋”分析框架为例,谈谈如何从日常生活经验上升到研究问题,并且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
聂辉华:一些优秀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例如钱颖一、许成钢和宋铮教授。他们的成功经验更值得关注。当然,作为一个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土鳖”,我的经验也许对国内学者更有可复制性。学术研究就好比雕琢玉器。要雕琢出一件上好的玉器,至少需要四个环节。第一,你需要找到珍贵的矿石(原石);第二,根据矿石的形状和纹路使用切割机分割;第三,用工具雕琢出玉器(例如佛像或玉镯);第四,找权威专家或机构进行评级;第五,上市卖出好价钱。中国历史悠久,地区差异很大,又处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之中,因此中国大地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天然的好素材,例如官员晋升、地区竞争、劳动力流动问题。这些素材就相当于矿石,但只有行家才能在矿石切割之前判断其价值(因此玉石行业有“赌石”业务),否则就浪费了珍贵素材或者大材小用了。因此林毅夫教授说,中国学者有时是坐在金矿上挖煤。发掘出有价值的素材之后,就需要利用各种分析工具(例如博弈论和微观计量经济学)写出文章初稿。然后,在各种研讨会上报告论文,听取同行专家意见,并反复修改。最后,将修改稿投给学术期刊并进一步修改和发表。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第一步(找到有价值的现象或数据)不太难,第三步(掌握前沿的分析工具)比较容易,最难的是第二步(挖掘出素材的价值)和第四步(获得高水平专家认可)。
以我提出的政企合谋框架为例。2005年,我看了一部王宝强主演的电影《盲井》,它讲述了罪犯在矿井里将一些农民工陷害,然后与矿主进行合谋的故事。矿难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但是我从中悟出了“带血的GDP”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于是,我和李金波借鉴契约理论的合谋模型撰写了论文《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多事故并存的现象。文章发表之后,虽然很多人认可政企合谋框架,但无人引用,因为很难用数据检验合谋行为。于是,我指导自己的本科生蒋敏杰,收集了1995-2005年中国省级矿难数据,以“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是否本地人”作为合谋的主要代理变量,发现政企合谋会导致更多矿难。这篇中文文章后来启发了一些同行将政企合谋框架拓展到土地违法、环境污染和偷税漏税等领域。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到了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认识了从斯德哥尔摩大学到哈佛交流的博士生贾瑞雪。我向她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她认为素材很好,但是缺乏一个好的分析框架,也没有解决内生性问题。于是,我们从几个方面撰写了一篇英文论文。首先,从集权-分权的角度来解释合谋,并为此构建一个数学模型。这就相当于为矿石找到了恰当的切割路线,因为集权-分权问题是组织的核心问题。这是文章发生质变的关键。其次,利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解决内生性问题,相当于找到了更合适的切割工具。再次,增加了媒体和煤矿企业的数据,相当于挖掘了更多的矿石。最后,合作者利用参加学术会议和国际交流的机会,听取了很多专家的建议。这篇文章历经坎坷,先后被《美国经济评论》(AER)、《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等六个顶级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拒绝,最后才被《经济与统计评论》(REStat)接受。从初稿到最终刊印,耗时6年8个月,但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
最后,我总结一下。中国学者要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掌握有价值的数据,然后找高手合作,提升文章的理论价值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
4、伴随计量经济学的普及,国内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在做经验研究,极少数学者做理论研究。您早年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后来又做了经验研究。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关系呢?
聂辉华:通常认为,理论研究是提供理论框架的,而经验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检验已有理论,以及挑战已有理论从而推动理论发展。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只颁发给理论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计量理论学者。从比例上看,欧美只有5%左右的学者从事理论研究,但他们处于学术金字塔的顶端,为全世界学者提供理论框架和检验对象。国内绝大部分经济学者主要做经验研究,只有极少数学者做理论研究。相对而言,后者比较“孤立”。与欧美相比,我觉得中国的经验研究学者和理论研究学者都需要继续努力。一方面,大部分经验研究都停留在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理论的初级阶段。刻薄地说,有些经验研究只能称为“回归分析”,就是找一个大样本数据,跑一百次回归,然后找出十个显著的结果,最后编一个“性感的”故事。周黎安教授戏称这些人是“三星拜物教”,就是看到显著结果就很兴奋。这样的文章根本不考虑研究的制度背景、回归结果背后的逻辑以及对理论本身的价值。由于很多数据并不公开,同行专家对现实问题也缺乏了解,因此很多看上严谨的文章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精致的平庸”。另一方面,国内的理论研究学者原创性不足,尤其是概念化的能力欠缺。主要原因是,学者们缺乏对制度背景的深刻理解、对逻辑关系的高度提炼,以及提供的理论模型难以被经验研究支持。这跟一些理论研究者数学水平不够高和不懂计量经济学有关。
我自己刚出道时,试图钻研纯理论,后来发现国内没有这样的环境,于是很快转向应用研究与经验研究并行。相对而言,理论研究进入门槛更高、发表更慢。因此,我主张博士生不管是否做理论研究,都要先掌握一些基础理论。最好是先做理论研究,再做经验研究,而不能反过来。在熟悉中国制度背景之后,理论研究可以先从应用理论开始,即借助西方经济学的顶层框架(比如博弈论和契约理论),通过改变约束条件和研究场景,证明新的命题(而不是发明定理)。钱颖一教授等人关于中国地区竞争的系列论文是应用研究的典范,而科尔奈教授及其追随者关于软预算约束的研究,就是从应用理论上升到纯理论的典范。考虑到理论研究更加依赖于大师的指导,而且出成果较慢,因此我们应该对理论研究加大支持,同时鼓励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学者开展合作。
5、您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Oliver Hart 教授。这一海外学习经历给了您怎样的收获?您如何看待国际交流对学术研究的意义?
聂辉华:经济学本身是西方舶来品,经济学研究水平又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因此,欧美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要做出一流的经济学研究,出国攻读经济学博士无疑是最优路径。但每个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做出选择,有很多学生无法出国,此时通过“联合培养”方式去欧美一流大学进修就是一种次优选择。我对自己的博士生说,要做好研究,就一定要出国。实在不行,还可以想办法与海外一流学者合作研究。我有一个同事,派自己的博士生到海外一流大学交流,然后双方导师带着博士生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于世界顶级期刊。我甚至认为,国际交流或国际发表是国内经济学者最主要的短板。
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我2009-2010学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指导教授是哈特(Oliver Hart)。其实在读博士期间,我曾多次通过email向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哈特等学界权威请教问题,受益匪浅。哈特教授经过考察之后,同意接收我。在此之前,我从未出国,英语也不好,于是我向一个海外教授请教:我应该做哪些准备?对方说,你不必准备,因为对方根本没时间管你。他的意思是,很多访问学者或博士后在海外没有压力、进取心不足,于是海外教授就当“扶贫”了。没想到,我和哈特教授首次见面,他就告诉我,我要在他主持的seminar(小型研讨会)上报告一次论文。我当时吓坏了,直到第二年做完报告前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但是碰到这样认真的教授,我真是太幸运了!为了弥补研究视野和方法上的不足,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听课、参加研讨会、阅读和写作论文,只是在回国前夕自费参加了一次匆忙的跨州旅行。在哈佛的一年,我收获很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开阔了视野。哈佛所在的剑桥市是世界学术中心,还有MIT和NBER等顶级研究机构。这一年我听了很多高水平的讲座,了解到不少前沿的研究领域,比如十年前我就在哈佛的讲座上注意到关于运气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跟踪世界前沿更容易做出一流研究,而这是国内难以企及的。第二,培养了品位。学术研究最难传授的是品位,只能自己去体悟。国内顶级期刊论文和国外一流期刊论文的最主要差别,不是题材,更不是技术,而是研究者的品位。我很庆幸,到哈佛之后多次和一流学者交流,现在能判断出什么是有价值的研究。第三,提高了写作。过去我总认为,经济模型要比较复杂才好。但是哈特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时,一再要求简单、清楚、严谨,连讲故事都不能随便讲。他认为,好的学术研究就是做两件事:ask good questions(提出好问题),answer them clearly(清楚地回答问题)。我现在写中文论文,都会特别注意通俗易懂,并且前后逻辑连贯,绝不乱用连词。第四,认识了高手。哈佛高手如云,除了一些教授,我还结识了一些优秀的华人学者,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合作者。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五,提升了英语。出国前,我一句完整的英语都听不懂,毕竟好多年没学英语了。回国后,我就给本院的外国留学生用英语讲授专业课“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6、有人说“读博毁一生,科研穷三代”,您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青年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聂辉华:你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但也是很多青年学生或青年学者高度关心的敏感问题,因此我想利用《学术月刊》提供的这个宝贵机会来谈谈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学,可以说“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我们每个人做决策都要考虑自己的约束条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克逊(Matthew Jackson)2019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Human Network》(《人类网络》),它的副标题是“你的社会地位如何决定了你的权力、信念和行为”。显然,相对于富人,穷人在资金、信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各方面都面临更严重的约束条件,因此说实话干什么都不容易。因此,正确的问题是,如果穷人不做研究,做别的事情会更容易吗?我的回答是,恐怕不会。比如拿前几年流行的创业来说,穷人最缺的就是资本,因此相对于读博士和做研究,穷人在创业方面更加没有成功的机会。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如果不考虑兴趣和比较优势,要选择一个相对容易的行业,就要看一下整个社会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具体做法是,我们随机地从人群中抽出10个人,看他们的职业是什么,然后再看他们子女的职业是什么,最后看一下两者的相关性。如果相关性很高,就是代际流动性很低,通俗地说就是“拼爹”的概率比较高,那么这样的行业就恐怕不太适合穷人。按理说,这样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如果凭直觉,我会觉得有几个职业的代际流动性是非常低的,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商人,一个是艺术家。但学术研究这个职业的代际流动性还是相对较高的。
相对于其他行业,经济学界有三个特点。第一,进入门槛与财富或出身无关。虽然进大学或科研机构做研究一般都需要博士毕业,但目前博士毕业与财富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一个穷人成绩好,从大学本科到博士阶段,都有奖学金,至少不必因为贫困辍学。第二,游戏规则比较透明。判断一个人的才能主要是看他在国内外一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当然课题、奖励也很重要。第三,“租金”比较少。我从来没听说一个人靠做经济学研究发大财的。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就决定了这个行业比较公平,对穷人来说依然有机会。在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中,我很少听说他们的父母是经济学者。一个典型案例是,我的博士师兄周业安、博士师弟桂林和尹振东,都是农村出身。因此,如果一个穷人对经济学感兴趣,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比较优势,我觉得做经济学研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毕业后的收入来看,相对于我的硕士同学,我的收入是偏低的,但仍然属于全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
7、您参与创办了人大国发院这一国家高端智库,并且您撰写的内参曾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请问您如何看待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如何平衡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聂辉华:2013年5月,我有幸参与创办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并在之后的六年里主管核心业务。在那六年中,我撰写的内参得到了十几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从智库的角度讲,这是很不错的成绩。人大国发院在中央评估中名列高校智库第一名。担任智库的领导工作,给我带来了几方面的收益:一是对体制更了解,尤其是政策制定过程;二是现实问题意识更强,知道什么是全局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三是有更多机会调研政府和企业。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学术研究。事实上,如果找到合适的路径,那么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以我研究的腐败问题为例。通过分析大样本的腐败数据,我们撰写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将学术论文的核心观点通过内参形式上报,我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我们还发布了基于大样本腐败官员的政策报告,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外,我还多次在报纸上撰写时评或者接受采访。我们团队对僵尸企业的研究,也采用了这种“一条龙”产品拓展思路,效果很好。当然,凡事既有收益,必有成本。多数情况下,给定时间约束,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就像是跷跷板的两头,一头压下去,另一头翘起来。这种时间上的冲突是很难平衡的。跟2013年之前相比,过去的六年里我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所减少。学者的天职是做好研究。我还年轻,还能继续钻研,因此我在2019年6月份辞去了所有行政职务(人大国发院常务副院长和科研处副处长),专心学术研究,希望不负众望。
8、您非常强调“直面真实世界”,经常参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调研,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作为一个并非一味躲在书斋里的学者,您又是如何克服现实带来的无力感的?
聂辉华:我认为,在中国做学术研究,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必须参加适当的调研。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熟知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源于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很多具体命题不一定适合中国,因此不能实行“拿来主义”,而必须了解现实才能对接理论;第二,中国是一个“低文本”社会,很多政策、数据不公开,必须去政府部门或企业调研才能获得一些政策细节或数据;第三,中国的学术界和知识服务业缺乏明确的分工,没有人去专门整理一些学术研究必须的政策或数据,这时只能靠调研去获取一手资料,以免被数据误导。当然,其实大部分学院派学者都没有条件去经常调研。我的建议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研究问题所对应的部委,知道相关的制度背景和政策,这能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现实基础。其次,要尽可能联系一些本领域的企业,知道政策的落地情况和微观机理。再次,可以适当参与一些有相关部委或者企业参与的政策研讨会,或者参与一些政府课题,借机认识一些官员和企业主。最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朋友圈中总有一些官员或企业主,这也是了解现实的有利途径。说实话,我现在只要写到涉及政府的文章,一定会让政府的朋友帮忙把把关,防止犯一些低级错误。有些学者有机会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我们作为学者要防止一种倾向:研究什么喜欢什么,熟悉什么偏向什么。当然,一般来说,经常调研的学者,在观点上不容易走极端,因为他知道现实很复杂,理论很苍白。但我们千万不能陷入到事实中去。张五常说过,现象不能解释现象,只有理论才能解释现象。另外,很多人迷恋大数据,认为数据不会撒谎。但是,第一,数据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代表性不足、指标错误;第二,数据本身不会说话,它象经典统计学一样,只能显示相关关系,而不能判断因果关系,后者需要借助经济学理论才能做到。
最后,我想说,虽然理论相对于现实有时很苍白,甚至很无力,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就是,知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而且有助于我们改变世界。但改变世界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不仅需要信念,甚至需要一种信仰。我在甘肃省张掖市参观过著名的马蹄寺,它是在悬崖峭壁上深凿出来的石窟群。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十三天”,一共有五层,最狭隘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爬过。我估计这样的石窟群要花几十年时间建造,除了宗教般的信仰,还有哪种力量能做到呢?
本文发表于《学术月刊》。索引:聂辉华、林佳妮,2020,《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聂辉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第6期。
整体经济下行,企业利润微薄,更要通过管理苦练内功,降低成本。欢迎阅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的企业理论通俗读物《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中央电视台两次推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直播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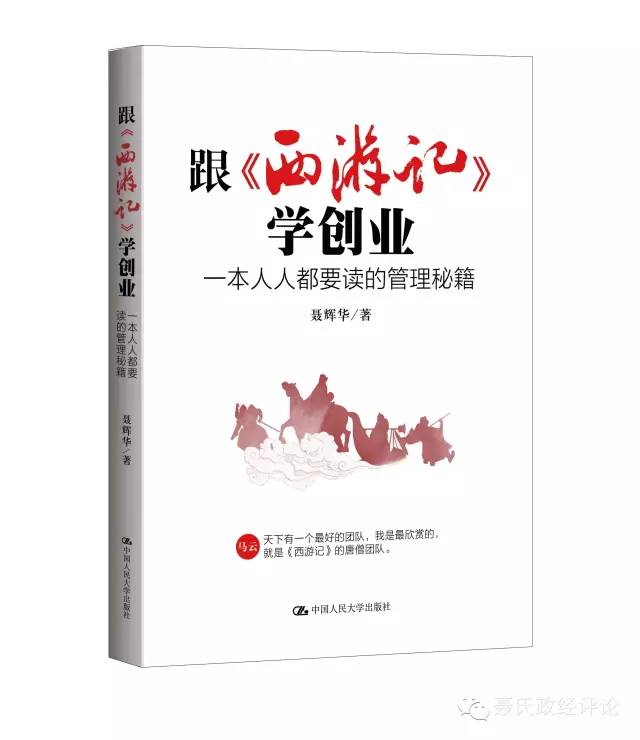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