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应坤/文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时代以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焦虑。尽管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杰出人士都给予了充分认识、充分解释这个社会的海量的理论思考,但现实社会的无限扩张仍然无情地把种种问题抛撒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顾此失彼,无从消解。即使是在边缘小镇,想听到一个清清朗朗、清明理性的声音也付之阙如。
崔莹的这本《访书记》,在与诸多学者、作家的深入追索式的对谈中,从对历史的新阐释、社会思潮的转向、文学作品的建构、世界史的动荡、流行文化的产生和消解等几个方向,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柔和的、有趣的、富含敏锐洞察力的话语,来回答“如何在人性和现代性之不可分割的张力中寻找到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这一重大而又关乎人心的命题。与此平行的还有区域身份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宏观认识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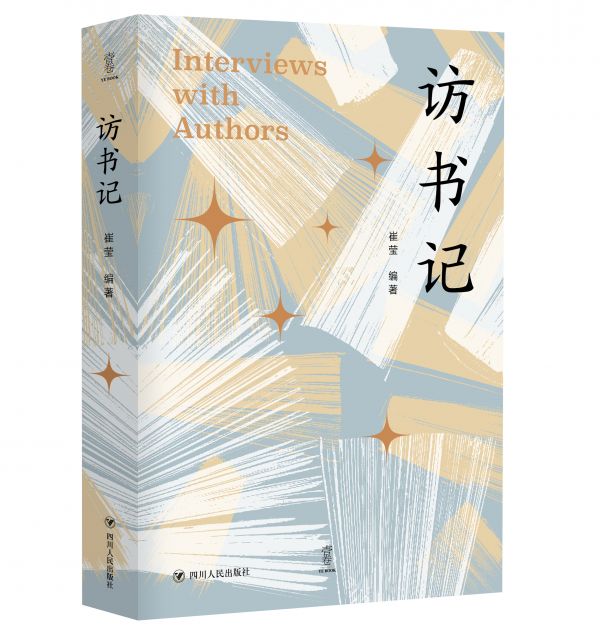
《访书记》
崔莹 /著
壹卷YeBook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11月
《访书记》的每一篇文章的标题都是提问式的,二级标题个个都是独立的论断,金句频出。每个段落的内容都充满了学术点,假若能将这些学术点敷衍成篇集结起来肯定能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精彩华章。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带着那种老学究式的眼光、不拿着学术八股文的标准去裁判,这本书就是一本上乘学术佳作。
崔莹具有一种罕见的综合力,这不仅体现在她对多个知识领域的熟悉、她的东西方兼具的观察视野,而且体现在她具有的不竭的精力和敏锐洞察力。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则动人故事,每一篇文章所散发的感召力都在促使看到这本书的人去克服不足、完善人性。第一篇中所涉及的有关近现代革命史的文章,《湖南为何出革命家?》《从1943年看蒋介石的败因》《炸开黄河后国军先救灾还是先抗日》摆脱了既往革命成败的叙述窠臼,从人的生存和发展、从身份认同的维度重新阐释了现代中国的诞生。
有一篇是崔莹与王德威的对话《评莫言、余华、王安忆》。其中一个二级标题是《中国当代小说:“启蒙”和“魅惑”并存》,内容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来归纳描述中国当代小说的特点。但认真品味起来,两人的对谈实质关涉的是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撕裂夹缝中给原初的人性一条出路。
在本书《马修·德安科纳/后真相时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开始不在意谎言》一文中,通过她与马修·德安科纳的交流,集中阐述了“后真相”对当今世界的巨大腐蚀和破坏力。“后真相时代的特征是:人们不评价某种主张是否真实,只评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尽管人们已经轻忽是否说谎的存在,但是谎言背后所带有的情感、主张、价值却是“真实”的。而且,人们容易被这种刻意为之的情绪化所困扰、所牵绊、所左右,结果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质疑、核查和问责制度被舍弃。进而,谎言与情绪合手颠倒黑白、搬弄是非、制造对立、兴风作浪,对社会发展、社会信任和团结形成共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这是迫切需要检讨、需要直面、需要反思的。
在很多篇文章记述的对话中,透漏出很多宏观大历史中的微观细节,而这些细节在及今天看来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比如在本书《印度如何深深卷入鸦片战争》一篇中,在揭示鸦片战争被印度人遗忘的时候,指出“大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的鸦片战争也和印度无关,他们甚至很少提及印度参与了鸦片战争”。事实是“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里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英国人,大多数士兵来自印度”。造成这种历史研究或者是历史记述的原因,据印度作家、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历史学者阿米塔夫·高希分析是“因为鸦片战争被中国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因此中国并不把印度当作主角”。
这些细节鲜有提及,如果类似的事实得不到持续披露和后续研究,历史的真实性往往在宏观的、意识形态意味的记述中被模糊化,甚至被掩盖。那么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反而并没有因此得到深化。
为避免这种状况,如何在今天寻找到一种平衡的写作即叙述路径?在本书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崔莹所揭示的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作法倒是值得借鉴。“提安哥指出文化相互影响的必要性。他认为,无论在历史作品中,还是自传中,反殖民写作者不仅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要试图理解殖民者的知识和文学,特别是他们强加于殖民地区的知识和文化。我们要努力去做的,是如何将这些创伤转变成财富”。
在本书《现实世界野蛮而残暴》一文中,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对于巴以冲突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自己写作的叙述方法也为此提供了一种参考。他说:“关于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各自的叙述,两种叙述都存在矛盾,我厌恶这些叙述。在书里面,我尽量梳理他们各自的叙述,将其变成有人性的故事,关于人的故事。”
对于越战,美国和越南也各有其完全不同的记忆建构。越裔美籍作家阮清越就此呼吁建立一种更加公正的记忆伦理。阮清越“提醒人们,在思考战争时,除了认识人类所共有的人性,还要认识那些不光彩的非人性——这是与对手、与自己和解的唯一方式。不这样做,战争的真相就不能被铭记,伤口也永远无法愈合”。
本书的“非虚构”部分所包含的九篇文章中,崔莹与之对话的写作者都是以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来完成他们了作品。这种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拉近了他们与叙述对象的距离,促进了情感交流,也更能引发有共同经历或者类似记忆的读者产生共鸣。如一度被模特工作的光鲜所吸引的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阿什利·米尔斯,在“采访他人”和“走进现场”这两种参与式观察方法以外,又进一步“我自己做模特,我成了我自己的研究对象……令我的研究获得更多的维度”。她对她角色的定位和再观察,实际上也完成了她自己对于自己身份的重构,也更加体味、触摸到了现代性加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分化的加深。
齐格蒙·鲍曼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创造者。崔莹与鲍曼的谈话以“后现代性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概念”这个议题切入,落脚点仍然放在探讨现代条件下人们如何建构自我。特别是讨论揭示出“流动的现代性”模式的邪恶发人深省。文中指出:“多数情况下,流动的邪恶都假装是助人为乐的朋友,但它并非真正的友善。……在今天,流动的邪恶正隐匿在某处。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它的迷惑性很强,它能够有效地掩饰自己,让人们不知不觉地信赖它,被它所吸引。它利用的正是人们的忧虑、人们内心的欲望。雪上加霜的是,很多人受其蛊惑而成为邪恶的联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鲍曼在回答崔莹“社会学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时,指出“社会学的职责是在变化的世界中提供一个方向”,“好社会是:一个不认为自己足够好并一直想成为更好的社会。那个社会随时期待变化”。而这句话正呼应了萧三匝在《访书记》篇首序言中所说的“对话就是平等主体之间以彼此完善为目的的观念互融行为”。
每一个人都处于一个小共同体之内,每一个国家都处于人类共同体之中。个人、国家和现代化都处于进行时的状态里,三者紧密联系而又无法抽身。崔莹的《访书记》站在全球的视野观察世界,体察人心。她与各位写作者探讨、对话、交流每一本书的写作过程,其实是她用平静的语气给人们讲述文明在宏观和微观进程中沁润心田的历程,是探讨人性在现代性大肆铺展中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如何立足立身提供内在力量。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助理研究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