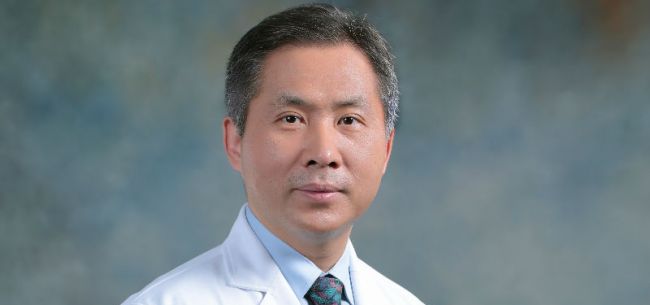
【编者按】医生,是链接一线临床需求和技术服务创新的枢纽。中国医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大医精诚的内涵也在时间浪潮中历久弥新。他们不应是困在论文、晋升等事务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医术致精微、修医德怀仁心的时代英雄,也是医疗服务这一囊括了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复杂体系的中枢环节,更是围绕提升医疗质量和普惠性目标所构建的创新链条上的核心主体。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健康事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将持续为读者呈现致力于医疗创新的大医生和他们的故事。
这是本专栏的第一篇,主角是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鸿祺。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编辑 陈哲 一个某西南偏远地区的山民,脑子里不幸长了动脉瘤。他被送进最近的医院,由一台精巧的机器人,为他测量出瘤体的精确大小,进而为他判定是否需要治疗、怎么治疗。手术时,医院只需要由技术员辅助和管理机器人。就这样,他不用舟车劳顿,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医问药,也能得到高质量的诊治。
这是想象中的场景,来自医生张鸿祺,他是全国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大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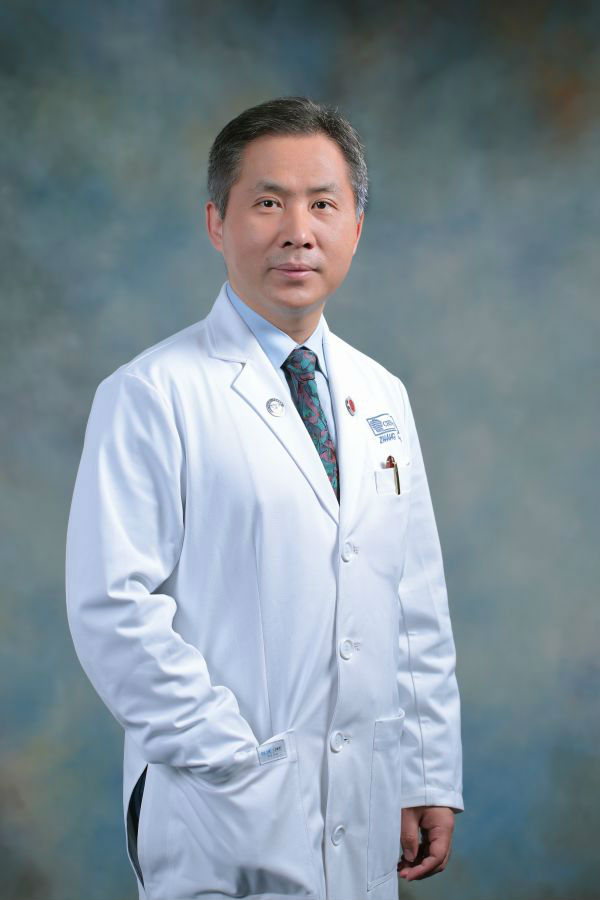 图片说明:受访者供图
图片说明:受访者供图
现实当然是骨感的。
神外是一个特殊的科室,手术难度大,临床要求高,工作强度在医院科室中首屈一指。在中国,如果要立志成为一名神外医生,在博士毕业后,大约还需要8年的高水平培训,才能独立完成各种手术。
宣武神外,一个被称之为中国神经外科黄埔军校的地方,聚集了最顶尖的神外医生。他们现在还常常受邀到山区、海外参与医疗援助,也总会赶往灾难一线。
大医精诚,张鸿祺和他的同事们,用满腔的热情和高超的医术来治疗病人,解除痛苦。在他的理念中,要想更多地惠及病人,达到医疗同质化的理想前景,需要在技术和热情之外,通过扎扎实实的科技创新,来提升全行业的水准,更大程度实现病有所医。
神外“坦克”
2008年5月12日,地动山摇的时刻,张鸿祺正在参加奥运医疗集训。汶川地震消息传来,他和宣武医院的9名同事被选为北京市医疗救援队的成员。当天深夜,家人一家家敲开商店的门,给他买好防滑鞋、雨衣、干粮。13日晨,他飞往成都。
在大雨中,张鸿祺被派往重灾区北川。去了之后才发现,当地没有手术条件,又随伤员到绵阳。
不惜时、不惜身,但求尽善尽美。两周时间,张鸿祺救治颅脑外伤的患者323例次,给许多发生颅骨骨折、头皮损伤、脊柱损伤的伤员做过手术。
除了震区救援、奥运会和残奥会医疗保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海外医疗援助这样的特殊任务,张鸿祺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宣武医院的门诊和手术室。
张鸿祺有一个特别的称号,“神经外科的坦克”。他曾经超过24小时不休息连续做手术。
由于同时擅长开刀和介入,将脑血管病的显微手术与介入治疗方法融会贯通,又有人叫他 “两栖坦克”。他做过的脊髓血管畸形(一种发病率低、研究者寥寥的疾病)手术累计超过3000例——全世界没人比他做得更多。
神外手术难度非常高。
同样是0.5毫米左右的血管,如果位于脑部,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造成失语、偏瘫等永久残疾。但是,如果在四肢、肠道甚至心脏等部位,更粗一些的血管断掉,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同样是出血,脑出血超过30毫升就危及生命,而在腹腔,出血几百毫升也不一定有大问题。
在神经外科,各种突发状况随时发生。
病人一旦出状况,抢救时机转瞬即逝。为了尽最大可能保证及时抢救,张鸿祺手机永远开机。
他不愿放弃每一个病人。
二十多年前,张鸿祺还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师。一个8岁的男孩在动脉瘤手术后严重脑干衰竭,多次濒临死亡,家属都想放弃了,张鸿祺和老师凌锋教授依然坚持,守在男孩病床前。术后第15天,男孩病情出现转机,一个月后出院,奇迹诞生。
人的大脑复杂,神秘,结构精妙,瞬息万变。极低的容错率,极高的手术难度,要求神外大夫必须精益求精。
张鸿祺说:“没有热情是不行的。”
“最强大脑”
张鸿祺一天的工作从7点开始,讨论手术预案、交班、查房、做手术或出门诊、开会、参加各类线上线下专业活动。
他尤其重视每周二7点的闭门会,和大夫们专门讨论上周出现严重问题的病例。
“万丈悬崖走钢丝”,人们这样形容神经外科手术。不成功或有并发症的病例,会让张鸿祺不思茶饭。
闭门会上,医生们打开心扉,去真实复盘、纠错、得出结论。他们讨论,甚至争吵,是出错了?是认知不到位?是当前的医疗技术无法避免?
撕开心里的伤口是件难事,张鸿祺定下的规矩是,在会上,什么话都可以说,会议后,决不允许在背后指责和抱怨。
闭门会制度,是张鸿祺引领下的宣武神外这支铁军的缩影。
张鸿祺拒绝制定只为了被服从的规则,允许向外向上去探索,允许“旁逸斜出”。
科室的核心小组明确了三条原则:第一,科内的每个人能否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二,科室是否为此提供了条件和氛围;第三,每个人的理想是否与神外的利益和发展的方向相契合。

图片说明:受访者供图
张鸿祺清楚,科室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很宽的,如果被限定窄了,规定动作越来越多,自由发挥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他希望给团队成员足够的包容和支持。
团队中每个人的探索常常会带来意外的惊喜。
科里一个叫李茗初的医生,痴迷于神经系统解剖知识,每天花大量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如果单纯用手术量来要求,他可能难以留在医院。
但在宣武神外,科室帮他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实验室,让他做得了最精妙的颅脑解剖。慢慢地,全国各地很多医生慕名前来学习,甚至张鸿祺遇到特殊的手术,也会请李茗初来帮忙。
团队里许多医生成了“网红”,包括张鸿祺在内,门急诊主任吴浩、儿童神外组组长曾高、主治医师陈思畅等都拥有10万以上的粉丝。在网络上,他们给人看病、科普,也传播科室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是张鸿祺的老师、宣武神外前任主任凌锋提出来的:技术不应该是冰冷的,应该充满人文关怀。
2019年,宣武神外搬进了被人们称为“大脑袋”的CHINA-IN新大楼。90名医生、206名护士、345张病床、每年超12000例手术,这些数字参与构成了这个科室在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巨大影响力。
人们走进“大脑袋”,会见到这些数字背后活生生的人,会看到摆在大厅的钢琴,还会读到宣武神外的科训,那是十六个金色的大字:
全力以赴,尽善尽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精诚之上
握起手术刀29年来,张鸿祺白发渐多,热情未减,除了做手术、带团队,他还想做成一件大事——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2021年9月,张鸿祺发起成立神经医学创新与转化联盟(CNIT),这是行业首个神经医学创新成果转化平台。
一年多的时间里,联盟把500多位医生、240多家企业、150多家高校院所工程专家、80多个投资机构、50多个产业园区聚到了一起。至今,联盟已实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想法的转化,有的已经成为了产品。
这样的成效和速度甚至让科委、卫健委的官员感到惊讶。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部门的数据统计,我国每年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仅为20%,其中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8%,而美国和日本该比率则接近70%。
包括北京在内,各地政府会给医院下达任务,医院一年得有多少转化额,作为绩效评估,但落地执行时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从想法到专利市场化,研发、注册、招标、医保、进院,每一步都不简单,法律保障、专利保护、产业对接,每一条都不可忽视,更需要医务人员、医院、企业、研究机构、资本、市场密切合作。
角色不同,思考的内容也会不同:
医生会认为,自己的想法企业只要去做就能有产品;
工程师会想,这个想法如何翻译成工程语言,技术能否实现;
企业会考虑,新产品市场会有多大,跟现有产品的差别是什么;
而投资方更多关注,是否能挣到钱,商业模式是什么。
张鸿祺发现,不同利益方的人如果能充分沟通,就会发现大夫眼中的好想法也许很难落地,而一些小小的改进也许前景广阔。这成了他组建联盟的初衷。
他记得联盟里诞生的第一款小小的产品。
介入手术时,血一旦倒灌,会导致血栓形成。护士不得不冒着射线一次次跑进手术室,给压力袋手动加压,用一定压力让液体缩回血管。久而久之,一名年纪稍大的护士都得了腱鞘炎。
她想,能不能有自动加压的东西?
联盟里一个做输液装置的厂家回应了她:“可以实现。”
几个月后,“神经介入电动加压输液装置”问世了。
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产品,虽然转化额不多,但这个护士心里很美。
张鸿祺在思考,如果每个护士都这么想问题,那工作起来热情将会有多高?
创新转化到底卡在哪里?它不是卡在宏大的愿景中,而是一个个小细节上。只有在真正的创新实践中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去反复探索,才能得出答案。
神经医学创新与转化联盟秘书长张宁告诉经济观察报,转化这件事太苦,太难,投入产出比不会那么高,真正愿意投入去做的人太少。
即使是在神经医学创新与转化联盟,能成功走到上市的项目也只有1/3-1/4。
尤其重要的是,能把各方聚在一起的灵魂人物可遇不可求。发起人必须真正理解和支持创新转化、相对亲力亲为,还得是所在专科领域排名前三的带头人。张鸿祺罕见地满足了这些条件。
在联盟,张鸿祺延续了“坦克”本色。一年多里,他几乎没有缺席联盟的每一次线上创新周话、每一场线下活动。
十月的一天,张鸿祺在晚上七点进入腾讯会议室,跟人们打招呼。
神经医学创新与转化联盟正在进行一周一次的“创新周话”。在这里,张鸿祺总能见到许多新朋友、老朋友。他说,十多年没见,剑锋一点没变,我是头发都白了。
陈剑锋是沛嘉医疗首席技术官,是这一周的主讲人,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创新想法是怎么从0到1实现的。
这样的云端谈话,总能让来自东部战区总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全国各地的神经医学领域的医生聚在一起。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NCU主任张猛就是这里的常客。他喜欢这样的讨论,打趣说:“打通了这第一公里,以后就一泻千里,一天几百公里。”
隔着屏幕,人们笑了,张鸿祺也笑了。联盟成立一周年那天,他在朋友圈写:“一年前,创新转化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年后,很多想法都已经成为现实。交流和互助,是理想飞翔的翅膀。”
以下摘自经济观察报与张鸿祺对话:
联盟把想法变成价值
经济观察报:神经医学创新与转化联盟的创立有什么契机?
张鸿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对原来的治疗设备、器械,常常有许多改进的想法。这些想法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变得有价值?
很多人都有创新的需求,但有隔阂。厂家的销售把医生抬得很高,不敢违背、得罪医生,甚至不敢跟医生交流真实的想法,最后变成互相防范。壁垒实际上是人自己造成的。
我的初衷是让创新想法能实现转化,真正用在病人身上。在国外,企业跟医生结合密切,转化路径清晰,企业、医生都能获益。
几个有这样想法的朋友讨论,说咱们可以组建一个联盟,把企业、投资方、医生、科研单位的人聚在一块,来聊这个事。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创新转化的最终价值是促进医学发展,更好地服务病人,每个人从中理所当然地获得一些回报。
我们也在摸索,怎么让这个平台不断完善。必须要尊重人的本性,必须有利益的分配和获得,才可能持续。
经济观察报:在联盟内,国内厂家有哪些努力?
张鸿祺:中国人做事认真,产品不比国外的差。有的虽然不是原始创新,只是改良,但也能让手术变得简单、安全、更容易普及。
我们接触的很多国产器械厂家都不只用简单的商业行为去获得利益,做事非常严谨。在良性的环境和政策的导向下,中国人一定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技术进步给医学带来无限可能
经济观察报:在神经外科,数字医疗对医生的临床治疗能有多大帮助?
张鸿祺:帮助很大,但现在还处于初期。
比如,动脉瘤手术属于中高难度以上的手术,随着技术发展,普及性变广了,但远远不够。动脉瘤手术会让3%的人致死或致残,风险很高。不够成熟的医生来操作,风险会更高。
以前,急诊患者被迫在当地救治时,我们会经常出去会诊,很累,把身体累垮了,也救不了多少病人。所以,需要严格培训更多的大夫,也需要把治疗简单化和规范化。
我想象过一个场景,一个人得了动脉瘤,机器自动测量出来,把结果直接展现给大夫。机器人还会根据专家意见、指南去分析风险。如果机器判断需要治疗,大夫也这样判断的话,就减少了判断的失误。是选择开刀还是介入,选择什么介入方式,机器也能根据经验给出方案。随访时,机器也能客观呈现病人情况。
这样一来,医疗就可以实现同质化。这是我的理想。
经济观察报:能否介绍一下宣武医院联合天坛医院、柏惠维康等单位研发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
张鸿祺:现在这款手术机器人主要用于一些立体定向的手术,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更精准,可以远程操控等。只要产品能做出来,尽管应用场景还有限,但已经很好了。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步开发改进,应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经济观察报:今年3月,宣武医院完成了中国第一例“脑机接口”临床植入手术。通过“脑机接口”能达到什么样的治疗效果?
张鸿祺:“脑机接口”现在还处在临床研究试验,有极个别应用在病人身上。
最终,没有创伤的(接口)是最有生命力的,但目前,非侵入式(接口)获得信号和分析还是很困难的,应用在临床中的场景还不太多,主要是在研究,但是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只是目前的探测器探不到、分析不了那些信号。
侵入式的,扎到脑子里,获得信号更直接,但它的侵入性非一般人能接受,应用范围也比较窄。所以还在不断地开发,最终肯定是无创,有创只是应用在一些特殊患者身上。目前,侵入式的大部分也是在做科研。
像DBS(脑深部电刺激,俗称“脑起搏器”),也是一种广义的脑机接口,用发生的一些电波来抑制一些异常的电波,消除震颤或改善其他问题。人们想象的“脑机接口”可能是能获得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或者指挥人运动,这个离现实和应用还有一段距离。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医疗?
张鸿祺:医患之间,信任非常重要,互联网医疗解决现有门诊、病房和物理空间没法解决的医患沟通问题。
我鼓励科室所有医生,积极地投入到互联网医疗,跟互联网医疗深度合作,表达自己的需求,去开发一些新功能。我想,互联网医疗企业,也希望得到这些信息。
好政策鼓励创新
经济观察报:北京市在做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付费改革,对科室日常管理有什么影响?
张鸿祺:我们早上还在讨论DRG。DRG是一种用经济手段来规范、管理医疗行为的方式。它是持续监控,动态调整,使社会资源能更好地应用在病人身上,不至于浪费。
对医疗的影响很大。
创新涉及到很多疗法、设备、耗材,企业要靠盈利来生存,卖力不挣钱就持续不下去。在DRG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创新,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现在,创新产品在一段时间内不纳入DRG,鼓励创新,这是一个补充。
什么是创新产品?就是具有原创性,不能完全复制别人的成果。好处是鼓励大家发挥智慧、能力,去创新,为社会、为医学作贡献。不好之处是,习惯于躺平、买办、复制别人的,就会受到抑制。当然,现在临床医学、科研或者学术活动里有很多还需要支撑,会造成很大影响。
对医学的普及和促进来说,这种影响是长痛?短痛?是好?是坏?我认为,长远来说还是好事情,鼓励创新。
经济观察报:在医疗器械和耗材领域,国家近期开展了好几次专项集采,也出了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你怎么看待这几次集采对医生的具体影响?
张鸿祺:我觉得所谓高值耗材集采,慢慢会趋于理性。
一个产品从想法、设计、定型,最后成为产品,再到销售,整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原料是几块钱,产品就应该是几块钱。
中国的服务体系里,把人的价值弱化了,大家都避讳谈服务。应该鼓励人的价值,才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出来。
集采要考虑到原始智慧的付出、设计人员、流通人员、管理人员的付出,才是比较合理的。
为什么我们主张医事服务与耗材和药品分开,这能体现大夫的价值。原来都不去谈这个事情,用药品或耗材的加成来弥补。实际上,大夫做手术,就应该值很多钱。
趋势还是越来越好,意识越来越强。集采理性化和对于创新产品的保护,在某种形式上体现了人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有声音认为,集采会加速国产替代,你怎么看?
张鸿祺:不能夹杂民族情结,不能贸易保护,要放眼世界,去高水平的环境中成长,要去市场上竞争。小孩不会走路才需要父母保护。
要敢于拿出来跟人作比较,敢于把人吸引进来,来把水给搅活了。绝对不能用民族主义的大棒,把国外企业赶出去,应该用合理的措施来促进民族企业的成长,进入世界舞台。
所以,理性地、科学地进行集采,有促进作用;搞得不好,会对医学、对产业会造成致命的损害。
宣武神外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当前,中国神经外科领域面临哪些普遍性挑战?
张鸿祺:第一是培训不够。在以往神外专科医生的培养中,对人的训练不够,书本、实验室、临床的学习都不够。在小医院,年轻医生可能没条件做大手术,常规手术也做不精。这是很突出的问题。
第二是知识储备和视野不够。
中国的医学教育体制在不断调整。单从神经外科来说,博士毕业才能当医生,之后还要经过7-8年的培训,才能在指导下做手术。我们在把合理的培养体系向全国来推广,我们参与了中国医师协会和卫健委的专科医师培训试点的方案制定和推广。
经济观察报:谈一谈宣武神外在人文关怀方面的努力。
张鸿祺:人文关怀不是表面上把患者糊弄舒服,最大的人文关怀是满足患者的根本需求。能治疗的就要争取治愈,无法治疗就争取有质量地延长生命。
经济观察报:宣武神外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目标是什么?
张鸿祺:我们是三家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别人治不了的病你得能治,深入研究,想办法攻克不治之症,这是首要任务。
第二是规范和普及。除了攻关克难,还得形成规范,向全国普及。
第三是要为社会经济作出贡献。比如通过创新转化来减少国家的医疗投入,推动医学发展。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