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2-10-09 21:4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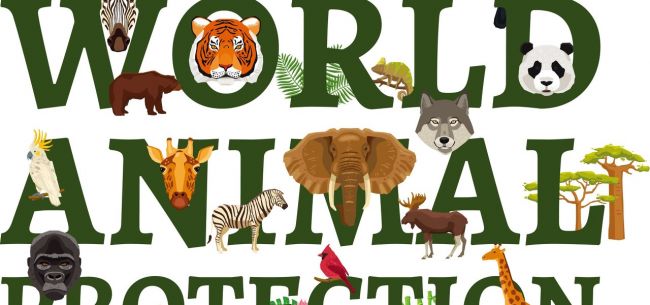
苏婉/文
在对待动物的问题上,人类一直很分裂。人类爱动物,又吃动物;鄙夷动物,也崇拜动物。动物的抽象存在对人类的认知幸福感至关重要,从孩童起人们就乐于被符号化为各种理想形象的动物所包围;人类不断向动物索取,以实现更好的物质生活,然而只要陷入疫病的恐慌,动物又成为怀疑的对象,或被“献祭”,或被“处理”。
换个角度来看,人类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史也是动物被严重去生存化和去感受化的苦难史。尤其是近十年间,在宠物类短视频拍不到的地方,人与动物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对经济动物和实验动物的暴力,因工业化生产和高涨的动物产品消费而更加泛滥。然而每当与无言的动物对视,人们都会意识到,自居于主宰的“我们”的与同为地球之子的“它们”,二者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其实从未被习以为常,尤其是在动物生命被极度商品化的时代,几千年来人类与动物的传统关系其实已经发生质的改变。
关心动物,无问西东
《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的作者黄宗洁是当代动物议题的追问者和行动者。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动物伦理议题的文学系教授,她不仅关注城市中动物与人的关系及与动物相关的文学书写,也将研究付诸于十几年来的动物保护行动。“它乡何处”的表述呼应了著名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的回忆录《乡关何处》,以提示动物因剧烈的现代化、都市化变迁无处安生,从而遭受到与殖民地国家弱势族裔类似的,被剥夺与被驱逐的边缘化对待。
从1824年第一个反虐待动物协会在英国成立到现代为止的200年之中,尽管犹太-基督的宗教传统更强烈地主张人类生命优越于其他存在的神圣性,然而西方社会在动物权利、动物福利方面的推动已经在不间断的论争中走得很远。很多人将动物福利视为发达国家的“专利”,认为在我国讨论动物福利是一种“奢侈”,其实相较于西方人,更懂得天人合一、万物共生哲学的中国,儒、释、道传统中都有关照动物生灵的论述,尤其是佛教传统给予众生以平等地位的考量,成为我们主张爱护自然的观念之源。相较于西方,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才是中国的传统,《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东方健康膳食模式”,推荐人们为了健康而回归这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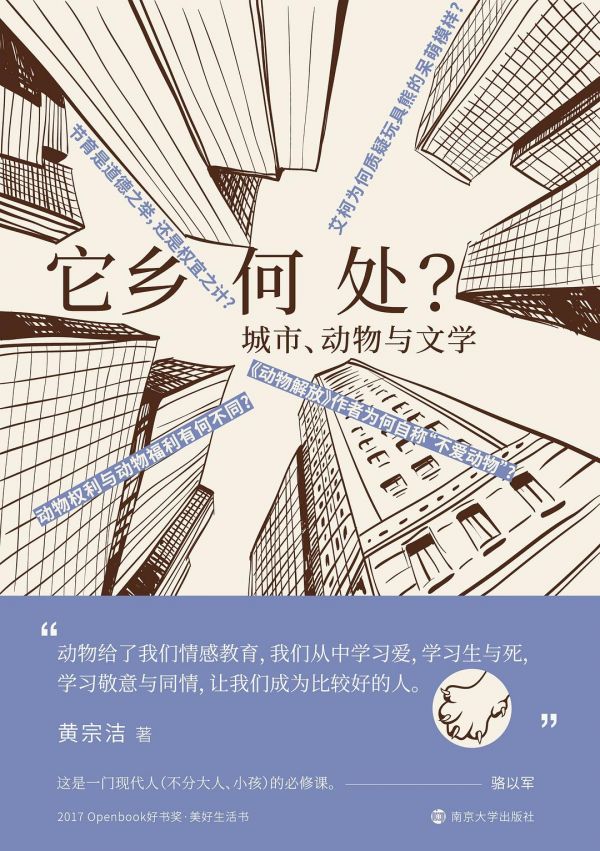
《它乡何处: 城市、动物与文学》
黄宗洁 /著
三辉图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所谓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在有着仁爱传统的中国社会讨论动物苦难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宗洁的书写把理论的长焦拉镜头向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与社会,她认为:“动物非但不是少数爱好者才需要关心的对象,更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连结,且早己被人类毫无节制与远见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与伤害。动物与自然不是只电视机里那看似遥远到与我们无关的沙漠或草原,而是就在我们的日常之中。”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仍是未能完全解决“人的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去关心动物的问题。从立法状况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忽视动物处境的正当理由,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会认为自己解决好了“人的问题”。据法学研究者的统计,全球已至少有10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体现动物福利的法律规范,其中不乏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如马拉维、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等,埃及还将人性化地对待动物写入宪法。很多国家在立法中承认动物是具有感知的生命。自2009年开始就被提起的动物保护、反虐待动物的相关立法仍未在我国2022年的立法计划中排上日程,也许从国家部委“加强动物保护执法,积累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经验”的回复意见来看,我国也正在动物议题上加快步伐。
动物:人类真的很难相处
通过对海明威、J.K.罗琳、骆以军、朱天心等作家动物书写的解析,结合伦理学、法理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主张,《它乡何处》为关心动物议题的读者提供了兼具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知识的入口,在对展演动物、野生动物、同伴动物、经济动物、被符号化的动物以及艺术与文学中的动物进行的分类书写中,黄宗洁试图以事实说明,为什么改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生存处境,是在城市化、工业化时代追求文明进步和良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出于有闲阶层可有可无的玻璃心,为什么反思性地修补“它们”与“我们”的关系,就是在水泥丛林的城市世界中修补人类与自我、与自然的关系。
关注具体的动物困境意味着必须扫兴地打破一些美好的幻象。《它乡何处》中不乏这样的“扫兴”:城市里的动物园本来应该是起到教育作用的动物博物馆,而不当饲养可能会让这个人类的乐园变成动物的监狱;让城市街道变“整洁”的动物收容所并非流浪动物的安身之处,而是停留十二夜就要面临处决的屠宰场。如果再将视野拉近,我们会看到,因为缺乏动物保护的相关规范,一些企业将皮草生意、大批在国外不能被接受的动物实验转移到中国,像曾经倾倒洋垃圾一样倾倒他们不愿承受的罪恶。
如果说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那么围绕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却总是引起最激烈的争论。猫狗在情感和道德的“差序格局”中离我们最近。“狗的自然就是人类社会”,黄宗洁描述了在人与狗漫长的互动史中,狗如何同时具有备受疼爱的宠物、被人厌弃的流浪动物以及可以上桌的食物等多重身份。她同时思考人身为“猫奴”背后的可能原因,以及当代城市生活中,猫介于驯养与野性之间的特质,如何让它们在“猫猎人”与“生态杀手”这两个标签之间成为人们又爱又恨的对象。
在诠释伴侣动物与人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之后,她也追问了一个“地方性”问题:食用狗肉真的能以尊重多元文化为依据吗?黄宗洁提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所谓的“传统文化”也可能是商业营销所塑造出的结果,或是因商业营销而质变,比如广西玉林的狗肉节。贵州同样有食用狗肉的悠久历史,但“花江狗肉”已不在当地民俗推荐之列,用贵州媒体人孙中汉的话来说,“古老的也好、传统的也罢,都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人类共识。就吃狗肉而言,能不吃尽量不吃;退一万步讲,你尽可以吃,但将它当成节日甚至包装成产业这就难免引起众怒。”地方性文化建构的过程正是一个有意识的扬弃过程,更符合普世道德追求的民俗才会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保留下来。
农业部曾多次在拒绝反虐待动物立法建议的回复中写道:“中西方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包括动物保护方面。我国在动物利用方面历史悠久,从事动物生产、加工利用的行业较多。”实际上,多学科的研究表明,中国动物保护观念曾一度领先于西方,传承下来的一些思想至今仍具有先进性。况且,只从“利用动物”的角度来看待传统的思路有失偏颇,地方性文化中,比如西北、西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宇宙观主张的普度众生、万物有灵等观念都限制了随意的虐杀行为,如果说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良善文化不能代表中国,就更没有理由让食用狗肉等传统糟粕来损毁中国的文化形象了。
食用狗肉如果是不合时宜的,那么为什么吃其他动物就可以?的确,相较其他动物议题,经济动物是最难被理性讨论,也最容易引起激烈反对,以至于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吃肉、卖肉的权利而反对反虐待动物立法。黄宗洁认为,素食被视为具有道德谴责意味,与肉食带来的不安和罪恶感乃是一体两面,要真实理解从“产地”到餐桌之间,发生在经济动物身上的遭遇,并且认真看待改变的可能,我们或许必领先放下素食与肉食二选一的道德是非题,反身审视经济动物的处境如何与为何触动我们不安的感受。唯有放下防卫心理之后,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必要之恶”的对待方式,才有可能重新被检视与松动。
人类作为杂食性动物有着吃肉的习惯,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吃肉,而是在于人类不曾像今天这样毁灭性的吃肉。基于养殖与屠宰的工业化,这种毁灭性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动物残酷暴力的泛滥,也体现在对人类自身健康的破坏,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威胁。
在商品化的逻辑中,“动物生命被定义成蛋白质制造机”,小公鸡一出生就被碾碎、母猪被囚禁在无法翻身的狭笼、为了保持小牛肉质鲜嫩而刻意使其贫血,为了提高贩售时的重量,在送去屠宰前强行灌泥浆。一些集约化养殖的环境拥挤、肮脏,为了省去麻烦,动物们大量食用抗生素,即便是作为商品,这样的肉食大概也不能多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肉类消费的总量逐年上涨,过量食肉已经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转变为三高、糖尿病、癌症、痛风等疾病的直接诱因之一,因此营养学家才推荐人们回归以植物性膳食为主的传统模式。而饲料的加工、畜牧业的大量碳排放也正在加重环境压力。因此,无论是出于道德考量还是利益考量,我们都有理由改善动物饲养、肉类消费的现状。
归根结底不是去争论要不要全民吃素的问题,而是在讨论如何在一种合理饮食方案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物痛苦,同时也缓解人类自身命运的慢性痛苦。
人类:动物的痛苦重要吗?
动物的议题会引起不安,似乎是因为其中暗含着一种潜在的道德指责。其实通过《它乡何处》,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较为主流的动物保护主张,也许并未对普通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而恰好相反,是顺应我们正在进步的伦理观念。
在这种进步的观念中,人与动物逐渐失去积极意义的关系正在被重建。有人会说,人是比动物高级的物种,高级物种可以永无节制地利用和牺牲低级物种。其实人与动物的绝对区隔早就被打破,林奈开创的现代生物学分类法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告诉我们,不可能从纯粹的生物学上将人与动物彻底分开。各个社会的进步,总体上都是在克服根深蒂固的等级性思维的过程中改善伦理和经济环境。封建等级社会的贵族、领主,黑人解放运动之前的白人,都曾毫不怀疑既存的等级观念。对待动物的方法通常预示了对待人类的方法,因为相似的原因,动物现在的处境被类比于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处境。约翰·伯格曾在《为何凝视动物》中提到,对动物工作能力所采取的机械式观点就被应用在工人身上,流水线上的“泰勒主义”主张工作必须简化到“愚蠢”与“迟钝”的地步,把“工人的心智当成牛一般的状态”。
正是因为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天然牵绊,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无法忍受对于动物不必要的残忍,“君子远庖厨”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动物解放》的作者彼得·辛格在对待动物问题上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痛苦(suffer)。从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视角出发,保护动物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减轻对它们直接造成的痛苦。科学研究表明,所有高等脊椎动物感受疼痛的构造和生理机制都是相同的,不论是我们的伴侣宠物猫和狗,还是经济动物猪和鸡,飞禽走兽,人类喜欢或不喜欢的,对疼痛的感觉至少与我们一样强烈,其实它们的许多感觉,如视觉、听觉、触觉等等,甚至都比人类敏锐得多,它们能够感受到自由活动的快乐,目睹同伴死亡时同样会感到恐惧。
正如《忠犬八公》的故事让无数人潸然泪下,呈现人与动物之间美好关系的视频能够让人感到最直接的善意与温暖,而动物被虐杀的画面、新闻总是具有传染性,它在人类的直觉与情感中引起强烈的不适与同情。法国哲学家蒙田将残忍视为首恶,而且认为动物一直是人之残忍的最大受害者。除了对虐待动物的普遍义愤,经济学研究显示,大部分消费者其实都愿意为动物福利提升的那一部分成本支付一定的溢价。同情的延伸总是历史上迈向平等、尊重、和平的第一步。对动物残忍的放纵,会引起普遍的厌世,如法学学者罗翔所说:对动物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人的尊重就可以衍生出对动物的尊重,如果可以虐待动物的话,人的心灵会毒化,而人的心灵一旦毒化,就会激发大量的恶性事件。
基于动物能够感受到痛苦,那么很多问题不是在争论如何二选一:停止对动物不必要的残忍,不意味全民吃素,而是提倡给养殖动物以可以活动的空间,更为人道地减轻实验动物所承受的折磨,减少它们死亡时的痛苦;防止流浪动物伤人,不意味着像山西运城学院一样把与学生已经建立起感情的狗残酷虐杀,而是可以为其打好疫苗,寻找可以领养的家。
黄宗洁在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很令人感动,“动物之于人,是露珠里的光,绝望里的力量。是我们对于爱这个词所能动员的,所有想象的可能。”《它乡何处》给了无言的动物一次表达的机会,你听见它们的呼救声了吗?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