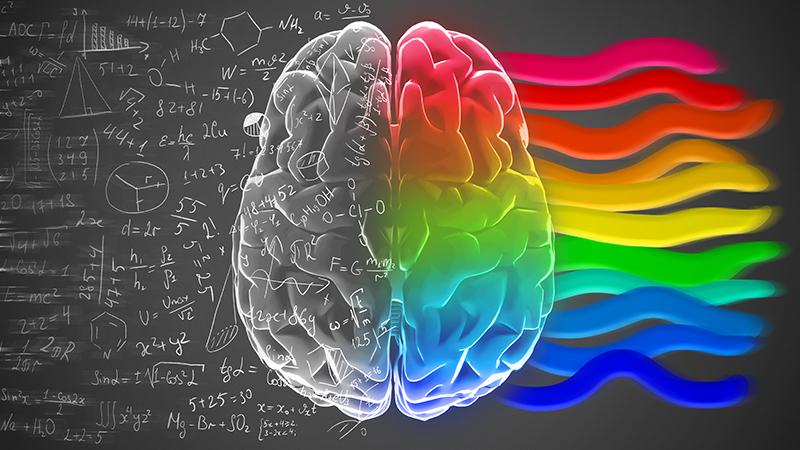
最近在多种报刊上,一再看到有学者提及张木生先生的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 在书中,作者反复揣摩了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的著作,将他读李文时觉得“憋得慌的地方”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大家看到李零关于国家命运以及文化立场的思考,以此为基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者自言“逢左必右,逢右必左,超越左右”,对“欧洲中心论”、“中华老大论”、“中国模式”等命题都有所反思与批判。
该书于今年4月出版后,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里,思想界的讨论都是围绕这本书而起的。” 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观点,一时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刘源、吴思、杨帆、萧功秦等都曾对此发言,进行论争。甚至有论者认为,该书所凸显的思潮走向很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走向,不可忽视,云云。
这些颇为高调的推崇,使笔者对该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但展读不过数页,却大失所望。暂不论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诊断是否准确,也不论其开出的“新民主主义观”的药方是否可行。仅就《改》的行文逻辑来说,就毛病多多:前后矛盾、以偏概全、浮泛空论等等举不胜举,再加上诸多枉顾常识的判断,令人几有不忍卒读之感。现举数例如下:
“在欧美,除了少数汉学家,其他各种学家都不了解中国”(第9页)“另外有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出现的?许多人都很关心,现有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观察的正确与否,决定性的还是文化立场。”(第14页)。“其实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人种不是那个人种,文明不是那个文明”(第145页)“专制与民主都有相通性,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150页)
这种不留余地、绝对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犯了过度推断、以偏概全的错误,只要一个反例,即可不攻而破。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非是一个汉学家,但他的很多著作都对中国进行了研究,不少中国政要都接受过他的采访,你能说他一点不了解中国吗?欧美的汉学家、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作者都了解吗?评判的标准又何在?再比如作者说现有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书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成说,据笔者了解,《改》中引证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即是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著作。至于作者说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专制与民主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简直就是枉顾常识,不值一驳了。
除了上述这般武断、不留余地的说法之外,《改》书前后矛盾、相互抵触之处也甚多。有时数行之间,甚至一句话之中,概念、观点就南辕北辙。比如:“1949年后,海峡两岸,判若两界,新东西发现在大陆,研究也是大陆学者的贡献大,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探讨,但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第47页)既然作者认为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讨论,那么所谓的大陆学者研究贡献更大这一结论又是从何得出?
再比如,作者认为“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第128页)但就在同一页,仅隔数行,作者又称“其实,虽然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但不能否认马克思已把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约定俗成”,再隔数行又认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马克思是德国人,自然属于西方学术界一份子。作者既然认为西方学术界还无人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那么又怎能说不能否认马克思已经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约定俗成”了呢?既“约定俗成”,又“说不清”,令读者无所适从。
上述错误较为明显,读者只要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此外,书中还有大量较为隐晦的逻辑谬误,值得分析。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中日甲午海战,胜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也成了东亚的后抢者,二战后期吃原子弹就不是日本人”(第148页)这种论证手法,是典型的滑坡谬误,作者不合理地使用了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推出了想要的结论。因为即使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也不一定就会成为东亚的后抢者。即使真的成为了后抢者,也不一定会吃原子弹。
再如“现在贬郭沫若抬钱穆,郭的学问,钱不可比,他们的不满说白了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第39页。)作者隐含的逻辑是,凡是认为钱穆学问比郭沫若强的,都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这是一种两难推论法,将问题简单化,只提供非黑即白的答案。
类似的还有“资本主义如同基因变异而产生的新物种,发展的极致就是今天的美国,不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难受,占尽全世界的便宜就更难受”。(第59页)等等。再如“美国人的人权观念是双重标准。美国人在‘9.11’之前最反对见义勇为,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野蛮,上层特别高雅,下层特别愚昧,对内看似很文明,对外是变着方杀人”(第21页)内是谁?外是谁?上层是什么上层,下层是什么下层,作者没有给出一个起码的标准,浮泛空论,就好像“上面有多高”一样,都是无意义,没有凭据的推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笔者从书中顺手抽取的,是否断章取义,吹毛求疵,读者可自行验证。除了其他诸如类比不当、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外,该书给笔者另一个最大的印象是在概念运用上的极度不严谨。书中屡次提到“现代化”“资本主义”“西方”“左派”“右派”等概念,但作者基本上没有明确地交代它们的具体指称,即使在具体语境之中,也常常一变再变。
从作者的行文看,虽然对这些概念的复杂程度有所意识,但在实际行文中却明显 “化繁就简”了。比如作者一再批判的所谓“西方”,就值得细细考量,究竟是哪个西方?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甚至东欧、日本?我们常常笼统地将这些国家称为西方,似乎他们是雌雄同体,不分你我。美国学者史华慈曾敏锐地意识到将“西方”当作一个清楚、明晰的已知量是异常可疑的。他说,“我认为,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数,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 这提醒我们在运用任何概念时,一定要注意到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脉络,万万不能削足适履,大而化之地拿来主义。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此书并非毫无价值。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观点就值得充分重视,目前思想界对于该观点的反应亦可证明。我无意在此陷入关于“回到新民主主义”、“欧洲中心论”、“中国模式”这样的争论之中,而是想以此书为例,着重指出一点:当下中国思想界在公共写作、理性交流上存有很大问题。大概念、大判断、大帽子满天飞,观点多于论证,感情多于事实,行文措辞缺乏基本的逻辑素养。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当前思想界争论的有效展开,既是作者智力上的极大浪费,也是对读者智商的极大侮辱。套用这本书的书名,倘若我们不能“改造我们的逻辑修养”,讨论再有价值的问题,恐怕都难以达到想要的初衷了。
殷海光曾经说过:一本著作要能发挥它最大可能的效果,必须著者和读者双方密切合作。在著者这方面,他必须尽力之所及写得清楚明白。……如果一本著作发生阅读困难的问题,那么我认为首先需要检讨的是著者自己,不要动不动说读者程度不够。请问问你自己想清楚了没有?写清楚了没有?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