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军/文
近二十年来,印度经济后来居上、“印度制造”有可能替代“中国制造”的说法一直存在。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战加剧、美国对华制衡和遏制的加强,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的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印度象”取代“中国龙”,似乎也越来越成了现实隐忧。
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究竟是“龙象共舞”,还是“龙象相争”?我们结合近年来中国、印度政治经济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中印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潜力和前景、问题及挑战等,进行一个概览。
一
印度经济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按照购买力平价和汇率衡量,印度经济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六(2017年数据),并且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中美两国,并且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从1947年独立到1980年代初期,印度经济整体上保持增长,但却饱受“印度式增长速度”的困扰。这一时期,印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很大,波动区间在-8%到9%。这一时期,GDP的平均增速只有3.5%,人均GDP增速只有1.5%。1980年代,在初步的经济改革政策指导下,印度经济取得了连续10年的增长,在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中终止。
1991年,拉奥政府在经济危机中上台,开始了印度的“改革开放”进程。印度沿着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目标,推行经济改革,调整产业政策、推进开放型经济,逐渐开放国内市场,实行对外经济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印度政府致力于发展服务业经济。2000年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了使印度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力图抓住“新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造就的机遇,使印度成为提供外包服务的世界性知识经济大国。印度的IT软件产业、医药和生物科技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2004年,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辛格执政后,印度致力于沿着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促进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业发展。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国际社会关于“印度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的观点逐渐获得关注。
今天的印度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外贸出口,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依赖高端技术产品而非贴牌加工品。印度被称为“印度大脑”、“世界办公室”,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服务业经济模式的典范。
二
三十多年来,与中国、印度经济发展的现实相伴,关于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比较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一著中,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森指出,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把注意力集中在开放经济和拓展市场上,但缺乏对于社会政策包括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进行根本性变革,是其重大缺陷。而中国、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进行重大经济变革时,在提供社会机会方面,比印度做得好得多。
森赞扬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中的历史性成就。他认为中国与印度命运相似,曾经同样贫困而不幸。而中国寻求社会变革和改造的方法,曾经对印度产生多深远影响。中国在1978年开启的市场经济改革、融入世界经济的政策,也在印度获得了广泛反响。中国在改革前在教育、卫生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改革后的绩效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保持了高预期寿命、高识字率等成就,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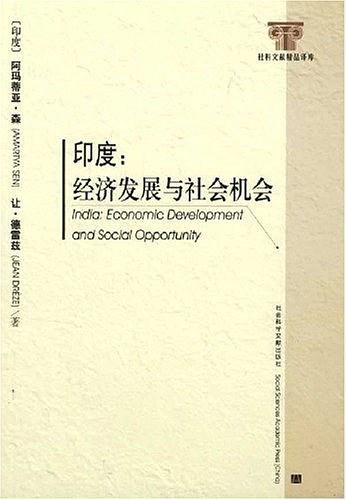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
[印度]阿玛蒂亚·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12月
不过森也指出,向中国学习,也要注意分析其“负面的经验”,印度要有鉴别地向中国学习。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印度裔经济学者普拉纳布·巴丹在《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经济崛起评估》一著中,也剖析了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揭示了两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制度性问题。
巴丹指出,相对于印度,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斐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印度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性冲突,在于民粹主义民主逻辑对于民主治理形成了威胁。在印度,任何有争议的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大量的辩论、煽动、街头动乱和冲突,惊人的延宕后,得出的结果往往却是不完美的妥协。
在印度,如果大量穷人身处一个独断专行的选区内,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地让政客实施旨在大规模减贫的政府计划,或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像印度这样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泛滥且冲突不断的多元化社会,很难组织起集体行动以推动长期的持续变革,同时给长期投资带来了民粹主义障碍——而这样的长期投资,可以缓解印度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这种竞争性民粹主义,通过短期的迎合和施舍以赢得选举,却会伤害长期投资,特别是物质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正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同时巴丹也指出,这种混乱及妥协,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软弱无能的印度行政当局的合法性。而对多元化和异议的容忍,是印度这个极度异质化社会的安全阀。印度的民主体制也面临更大的压力,让人民享受发展的好处,减低动荡带来的民众损害,使发展更为持续。同时,印度的民主也为反对资本家暴行和工业化副产品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此外,民主也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机会,来缓解社会不平等。
巴丹总结说,中印两国自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得相当好,展示出了卓越的适应能力,但是要高瞻远瞩地关注可能阻碍中印未来发展的结构脆弱性及社会和政治不确定性。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如何难以预测,尚需观察。
三
印度学者普勒姆·尚卡·贾在《卧虎藏龙:中国和印度能否主导21世纪?》一著中,系统全面地比较了中国和印度“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印在21世纪面对的挑战。此著虽然写于2009年,但论点新颖,分析细致,很多结论至今仍然有启发性。
贾在该著中,回顾了中印两国经济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印度的改革比中国晚了13年,1991年才决定废除指令性计划。英迪拉甘地政府早在1980年就有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设想,但限于印度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势,而未能实行。
不过贾认为,中印两国在进行改革时都显的犹豫不决,中国政府在开启改革后,曾匆忙收手以缩小强烈的社会反应。在印度,由于1980-1981年国内通货膨胀以及外汇危机,迫使印度走上了改革的道理。

《卧虎藏龙:中国和印度能否主导21世纪》
[印度]普勒姆·尚卡·贾 /著
文汇出版社
2012年12月
贾指出,中印的经济改革,都回避了休克疗法,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中印政治经济发展的相似之处,同样蔓延到了政治领域。中印都试图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但都需要竭力缓解工业化快速发展对贫穷阶层的影响和伤害,依赖再分配途径达到社会公正,并试图利用政府税收为穷人提供安全保障。
结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既有着时间、历程上相似之处,也有着结构性、制度性的根本差异。正如贾在其著作中总结的,在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过程中,需要看到,两国经历的不仅是经济变革,而且是政治变革。这种政治经济巨变,在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蕴育着矛盾。两国的未来充满变数,需要成功地协调“赢家与输家的利益”。
中印两国都意识到了这种需求。在贾看来,中国需要建立能够履行这一任务的制度,而印度虽然具备这样的制度,但需要加强政治意愿或治理能力,以免使制度沦丧或堕落,不能完全行使职责。现在看来,要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直到今天,对中印两国都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四
印度学者桑加拉林加·拉梅什(SangaralingamRamesh)2017年的著作《中国给印度的教训》,全面总结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印度的“经验与教训”,数据比较新,观点也更为综合。
拉梅什指出,印度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宗教,而中国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文明。在英国崛起之前,两国都通过贸易统治着已知的世界。几个世纪后,两个国家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混合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了经济转型,1978年开始了逐步的自由市场改革。印度在1991年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后,正式开始了经济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但最近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开始超过中国。

[印度]桑加拉林加·拉梅什 /著
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2017年版
拉梅什认为,印度经济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但独立后其领导人的错误政策扩大了这些问题。印度决策者可以从中国决策者的政策和战略中获益,以促进印度作为一个经济、技术和最终军事超级大国的崛起。
拉梅什在第一卷《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1949年以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英国统治带来的不利因素的阻碍,而中央计划经济又加剧了这种不利因素。首先,印度的基础设施以服务英国经济的需求为导向。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方便从印度到英国的原材料运输。其次,英国的统治削弱了印度的创业活动,以至于后代发现创业并不容易,在微观经济层面。第三,农业用地分配不公,大地主和小佃农差距显著。第四,金融体系不发达,高利贷盛行,导致了金融奴役。最后,印度继承下来的政治、文化、社会和语言阶层让位于制度上的僵化。中央计划、私人投资管制和经济许可证制度,又加剧了这些因素,导致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经济的不发达。
拉梅什认为,印度在1991年经济“改革开放”后,在模仿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道路上取得了进步,但仍然需要克服微观经济层面的制度僵化,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进而经济变革导致制度变革。
拉梅什在第二卷《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印度如何学习中国的经验?”一节中明确指出,印度应该专注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创新、促进微观经济层面的创业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促进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活力、适应性和灵活性。重要的政策建议有如下一些。
(1)加大力度促进创业,特别是在低种姓和女性中;(2)废除使公司和企业家雇用工人成本高昂的严厉的劳工法;(3)促进和加强平等立法,加强赋予妇女权利,减少歧视,使其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4)增加政府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的资助,以便开展创新项目;(5)在大学设立高新技术区和初创企业孵化器,促进研究中心和商业公司之间的横向联系;(6)通过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研究人员,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创新中获益。(7)学习中国经验,指定孟买、钦奈和加尔各答为沿海开放城市,为国内和海外公司提供优惠的经济和商业政策;(8)在泰米尔纳德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港口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由政府资助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跨国公司参与制造业;(9)加强改善印度境内所有类型的有形基础设施,以及连接印度与其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基础设施,以整合印度国内市场、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市场。
在这些政策建议中,我们多多少少看到了拉梅什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认真体察和分析。
不过,拉梅什观察到,中国的市场整合并不均衡,经济增长导致中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市场一体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了通过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正式联盟等欧盟市场一体化形式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拉梅什乐观地预期,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超过26亿,如果两国能够形成一个单一货币、统一法律法规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免税区,两国经济将受益于统一市场和消费者规模,而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将带来“亚洲崛起”!
这当然是个非常乐观的构想了。从当前中印关系的现实看,这个“龙象共舞”和“亚洲崛起”愿景,在国际政治经济风云波谲的当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未来,是一个不好下定论的问题。不过,中国和印度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相互对标和竞逐,毫无疑问是长期的!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