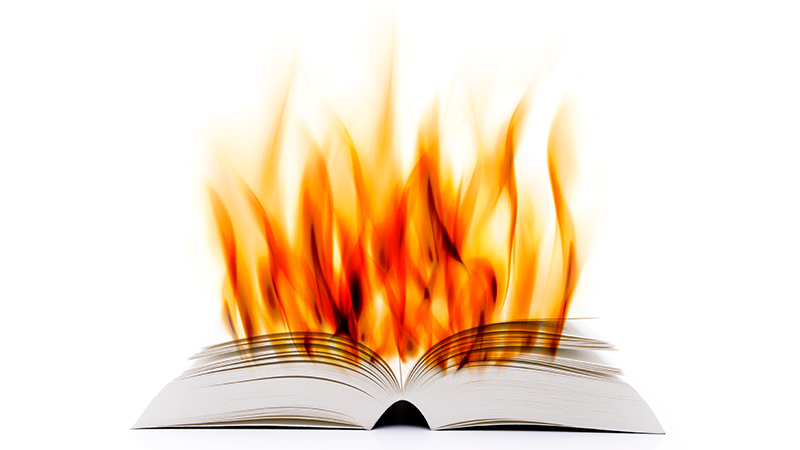
倘若我们要给知识分子加上一种义务,那么其义务就应该是通过批判——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行进行批判——来见证社会的发展。——翁贝托·埃科
不必热诚地坚持任何一种主张。没有人会热诚地坚持7乘8等于56,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事实。只有在推崇一种可疑的或者可以证明其错误的主张时,热诚才是必需的。——柏特兰·罗素

《密涅瓦火柴盒》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翁贝托·埃科的自选集,文章选自他每周发表在《快报》上的专栏,题材林林总总,不限于时政。“密涅瓦火柴盒”也是他专栏的名称,原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作者常把临时想到的灵感或念头,顺手记录在盒子的封皮背面上,便于回家后坐在打字机前将其扩充成一篇专栏。如你所知,“密涅瓦”也是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的名号,对应于古希腊的雅典娜,作者双关命名,定然含有智性上的期许。
埃科在前言里写道:“读者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即使我采取的是一种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却总是一种愤怒之情。我不谈让自己高兴的东西,却总是针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写下自己的想法。”——不愧是“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拒绝把责任之笔绽放成一朵悦己愉人的向日葵,只在愤怒时执笔。用“调侃的笔调”来调剂愤怒,也是一种高端的优雅,它并非意在修饰或稀释愤怒,而是通过适度的从容机智,矫正激情,避免偏激,使结论更加站得住脚,避免将论证过程投付滔滔湍流。
人很容易在愤怒中体验正义,正义很容易在愤怒中滑向反面。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提到自己认可的两类知识分子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后一种人同样重要,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且略过。前一种人,与埃科的“夫子自道”正相吻合。“仇恨”与“愤怒”往往是知识分子生涯的起点,但只要他们足够优秀,就会在抵达终点时,将怒气和恨意渐始消弭,唯以一派无懈可击的理据示人。愤怒之于知识分子,顶多起到药引之功,言论品质还得靠强悍的理性来压阵。
不过,读完《密涅瓦火柴盒》,重温埃科置于卷首的那句真诚告白,我差点笑出声来。诚然,就像伏尔泰说“希罗多德并不总是说谎”一样,埃科也并不总是缺乏愤怒,但让我归纳这本集子的性情特征,我数到五十都未必想到“愤怒”,位居前列的,皆与“愤怒”相去太远。
《一本〈牙签论〉》,开篇就兴致高昂地吊足读者胃口:“或许你们从未体验过查询古书目录是一件多么有滋有味的乐事。”接着,仗着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埃科向读者罗列了各种趣书,除《论牙签及其不便之处》外,还包括如下名目:《棍棒的功能》——“其中列举了大量遭到棍棒击打的著名艺术家或作家(包括布瓦洛、伏尔泰和莫扎特)”;《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作者在书中称“一个普通德国人排出的粪便比法国人更多,且气味更加难闻”;《改革派绿帽子协会》——该书“把‘戴绿帽子’的起源追溯到了巴别塔时代”,等等。我读得乐不可支,阅读过程中既不曾想到“愤怒”,也绝不认为作者“调侃的笔调”下藏着“愤怒”。
《海岛度假小记》写的是自称“并非一位富豪”的作者“有幸到大开曼岛一游”的见闻,那里是“一个免税天堂”,“似乎置身于迪斯尼童话世界”则是作者的主要感受。当然,那里还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一座避税者的天堂,试图在规避税款方面有所追求的全球富豪都喜欢在那里注册公司,中国的富豪企业家也不例外。这早已不是秘闻,埃科在沐浴海风、饱览比基尼女郎和品尝海鲜之余对此略加评论,不过装点笔墨,应付文债,和“愤怒”无甚关系。因为,对一件与自己远隔千山万水、且根本上超出己力的事情表示愤怒,委实有点杞人忧天。相形之下,堂·吉诃德向风车发火,倒还更合理些。
《罪恶一夜纪事》是说作者某个夜晚寻访网络色情岛的经历,写作时间是1995年。就互联网纪年而论,大概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我就是在那年拥有了第一台386电脑,无法上网,也不知互联网为何物。大作家埃科先生不仅早早上网,还着手寻觅“大量超清晰的色情图片”,真是先驱。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那台386电脑的屏幕分辨率是640*480,也就是区区30万像素,与“清晰”压根不沾边。在该文里,作者的确遇到了愤怒的事,他亢奋过头,着了某个网络钓鱼客的道:美国犹他州“一名极其严肃的道德主义者”许诺提供“超清晰色情图片”,骗取了埃科的信任和邮箱,却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埃科严词训导,说他“有心理疾患,没有朋友(更没有女朋友)”,还说,“如果我(埃科)的祖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因为动脉瘤发作而被我活活气死”。这事猝不及防,埃科看上去有理由“愤怒”一下,但他没有,他只是觉得好玩。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此刻已是凌晨三点了。整夜的色情大餐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我终于睡下,并梦见了成群的绵羊、天使和温顺的独角兽。”
不管作者打算暗示什么,“愤怒”总不在其中。实际上,埃科在本书里展示得最充分的,就是俏皮和贪玩,以及无与伦比的机智。在《糟糕的〈第五交响曲〉》里,他以更加盎然的兴致,介绍了一本“有趣的集子——《退稿信》”,该书“专门收录文学巨著遭到出版社拒绝的评语和回信”。作者以某种涉嫌骗取稿费的作风,大做文抄公,整页整页摘抄例句。他显然洞悉读者的兴奋点,即,幸灾乐祸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人之常情,再纯粹的文学爱好者也愿意了解成名英雄的倒霉经历;倘读者幸灾乐祸之余还能萌生励志之情,则作者善莫大焉。受到埃科鼓舞,我且摘抄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也许是我生性愚钝,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位先生怎能将长达三十页的篇幅耗费在描写自己如何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场景上。”——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
“关于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根本卖不出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很遗憾,美国的读者不会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感兴趣。”——赛珍珠《大地》
“先生,您的整部小说都被埋葬在您设计的一堆华而不实的细节描写之下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真令人费解。所有的韵脚都有问题。”——艾米莉·狄金森的第一部诗歌
作者的玩兴并未至此结束,在另一本文集里,我凑巧读到埃科创作的几封退稿信,收信人包括荷马、《圣经》的作者、但丁和康德。针对康德的退稿信是这样结尾的:“德方代理人告诉我,我社还必须同时出版这位康德仁兄的其他次要著作,共有一大堆,其中甚至包括天文学。建议切勿与这样的人扯上关系,否则仓库里积压的书会堆积如山。”针对萨德侯爵的情色名著《朱斯蒂娜》,埃科轻快地表示:“这就够了。我们不是要寻觅一部哲学著作。今日读者要的是色情、色情、更多的色情,任何形态或形式的色情。”

我提及愤怒的缺席,当然不是讽刺埃科言不由衷。因为,埃科乍看上去有点搞笑的表白,漏泄了一个情有可原的隐忧。
通常,在无需担心被喝破行藏之时,人们倾向于狠拍胸脯,声称自己具备与从事职业相关的核心美德。因此,教师总会表达热爱学生之情,企业家总会表白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会计师总会夸口自己的诚实,政客总会侈言自己充满民主意识,黑道人物也总会强调自己遵守道上规矩,属于“盗亦有道”那一类。反正,文字一划拉,美德就到账,比电子转账还方便,如此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呢?
埃科提及愤怒,亦可作如是观。知识分子的即兴表态,也是一道常见景致,在这种场合,只有傻瓜才不会把那些切合自身角色需求的东西视如囊中之物。既然他有志于成为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就必须让读者相信,自己正是这样一位整天与正义耳鬓厮磨的人。而愤怒,恰是正义的配套装束。
休谟说过:“看来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幸福的状态中,每一种其他社会性的德性都会兴旺发达并获得十倍增长,而正义这一警戒性和防备性的德性则绝不曾被梦想到。”就是说,天堂无关正义,一个相对民主、富庶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正义感”缺乏用武之地的环境。我们在自然界也能看到类似情况,丰美草原上的牛羊,总是悠哉游哉地吃草,互不相扰,而实施食物配给制的猪圈和鸡棚,则永远在哄抢争食。
埃科置身的意大利,虽非一流民主国家,但还算民生安宁,富裕祥和。“羞耻啊,我们居然没有敌人!”这是他另一篇文章的标题,笔调仍充满调侃,说的却是实话。一个没有敌人、自身也不愿寻找外敌的国家,不易孳生民族主义情绪,不易滋生深刻的社会危机。
这样的国家虽也难免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笔者作为资深球迷,很早就耳闻过该国的足球腐败,而在英、德等国,类似腐败罕有听闻——但不管怎么说,矛盾或问题总还处于可控之中。无论知识分子或记者如何危言耸听,他们揭露出的问题一般不会全方位地激发出读者的正义之心。发发牢骚是一回事,形成民族性的同仇敌忾又是一回事,只要后者阙如,就会反过来制约知识分子的言词格局。
“一旦我不再愤怒,我也就不再有正义之怒所必需的那些结论了: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乔纳森·海特语)知识分子的愤怒会诱导民众的正义感,民众的愤怒会怂恿知识分子展示正义,但假如民众处于懒散状态,这类互动就无从生发。绝望中的人民才是正义的最大客户,我们可以想象,位居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前列的冰岛等国之所以不易产生伟大的知识分子,实是由于当地的贤明政治和富裕生活,无法匹配知识分子的正义需求。一位北欧作家倘表现得过于愤激,或会予人“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
埃科有篇文章叫《民主如何摧毁民主》,虽不乏调侃,但生活在次一级舆论环境下的读者,读来会大感苦涩。文章大概是对时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媒体遭遇,有感而发。埃科撰写此文的1998年,意大利正由贝氏主政。贝氏是位明星相十足的领导人,像我这种对国际政治并未多加关注的人,也风闻过他不少丑闻和绯闻,后者好像更多些。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位富豪,意甲豪门AC米兰俱乐部的老板。当然,今天的贝氏正在监狱里呆着,罪名是行贿议员。对贝氏,我有过一个鲁莽判断:意大利人选择他,主要是看中其娱乐价值,选他就为了嘲笑他。读埃科文章,我发现这个判断或许不算离谱。
埃科先是提到秘鲁同行巴尔加斯·略萨的一篇妙文,该文“赞扬‘性丑闻’是民主的积极表现”,理由是,政治领袖“越是声名狼藉,就意味着民众的监督越是有效”。埃科没有直接否定略萨,但他提醒读者注意当前的舆论现状:“这种 (针对政治人物的)揭露通常都带有恶意,其对象往往是病痛和缺陷、过度瘦削的身材、不光彩的家世、不文明的行为举止等等”。接着,作者又要求读者将心比心:“如果你每天都听到(或看到)其他人对你身体上的缺陷或你的某个荒谬之举指手画脚,说你性无能,说你是个小偷等等,……无论你的意志多么坚定,你都将无法容忍。”于是,埃科亮出了观点:
“你会怎样做呢?你会让自己躲藏在忠诚于你的那个小圈子里,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会安慰你,让你别去理会可恶的造谣者,同时再次向你表示他们对你的忠诚及爱戴。自然而然地,你会认为这个忠诚的圈子构成了你政治生命的心理依靠,同时把重要的职位交给这个圈子里的人,从而形成一个极为坚固的互助圈。”
该观点呼应了文章开头的结论:“如此一来,那些对世界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物往往对于现实世界一无所知。”媒体任性而残忍的揭露,使选出的政治人物日益低能,民众到头来却得承受这番低能的代价,因为,那个笨蛋依旧高高在上。此即“民主摧毁民主”。
这个观点不乏趣味,但未必高明。埃科所指,乃是一种民主制度走向滥熟阶段的富贵病,对于置身该种制度下的民众,不失为一种居安思危;对于远未达到该阶段的人,就像流浪汉听富婆介绍减肥妙用,难免嘴巴大张,颇为尴尬。饱汉不知饿汉饥,诚然;反之则不成立,因为饿汉总还知道些饱汉感觉,谁也不会倒霉到平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同时,我们对于埃科为什么无法兑现“愤怒之情”,也就有了“同情的理解”。

置身滥熟的民主制度下,批评政府和政党领袖固然依旧重要,但的确不容易给知识分子增光添彩了。正因为政府和政党领袖始终处于媒体的凶暴监督之下,长此以往,他们真正值得批评的地方也会逐渐减少,恶性度也会日益减弱。雷蒙·阿隆说:“公众更愿意在报纸上找到可以证明他们不满或要求的论据,而不是找到理由承认:在一些特定环境中,政府的行为不可能会和它原来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批判,人们可以逃避对某一措施引起的令人讨厌的结果的责任,即使这一措施大体上说是令人满意的。”
在此情形下,如埃科所说,通过“对自己的同行进行批判”,倒可能更有效些。不管该种批评能否“见证社会的发展”,它至少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活性,起到某种维护枪膛的功能,避免批判力卡壳生锈。所以,在《密涅瓦火柴盒》里我们不时读到埃科针对知识界同行的商榷和批评,它们通常总是有力和有趣的。在同类相残方面,知识分子从不不亚于蟋蟀,好在,这类厮杀有益于文明机体的健康。
此外,当社会面临大规模不义或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知识分子的声音固然会被无限放大,但也会变得生硬糙砺,动荡年代的民众本能地期待简单结论,他们更期待给心灵带来安抚、而非给大脑增加负荷的观点。休谟说过:“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和同情感,而让不义与仇恨来代替它们。”我曾提到奥威尔和加缪的例子,奥威尔在二战期间执意反对英军虐待战俘,强调“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加缪则在法国被纳粹占领期间,在“致德国友人的信”里,坚持“为务虚细微的思想而战斗”,避免与纳粹在思想上同流合污。他们的见解非常高明,但也非常不合时宜,当时就被淹没了。
那么,在一种政治相对清明的制度环境中,知识分子无需营造慷慨、撩拨正义,倒是有条件“为务虚细微的思想而战斗”,埃科在这方面体现了伟大。闲着也是闲着,密涅瓦牌火柴盒的封皮背面上不适宜发表高屋建瓴的谠论宏议,但不妨把笔弄成柳叶刀,实施精确的外科手术式批评。
比如,关于隐私权,埃科注意到“如今的服装却要刻意露出肚脐、臀部曲线、多毛胸部上的项练、凸起的阴囊”,遂郑重提议:“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并不在于向那些注重隐私权的人士(在所有公民中,他们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提供保障,而在于教育那些自愿放弃它的人,让他们懂得去珍惜这种相当宝贵的权利——隐私权。”
关于现代战争,埃科发现,“在新型战争中,双方不急于消灭敌人,因为面对敌人的伤亡,胜利的一方会遭到媒体攻击。……在新型战争中,一切战略部署都要以‘博取同情’为原则。”极为辛辣。
说到政党的组织偏见,在《清一色右派》里,埃科发明“焦距的长短”概念,提醒人们留意此类现象:“对于某些作家,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在他二十岁左右,那么他看上去的确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但如果我们再看五十岁的他,则又成了共产主义者。”结论是:“一张把人划为某组织成员的清单和一张把人开除出某组织的清单是同样危险的。”
针对人们在诉讼中经常行使“道义上的信任感”,埃科像一位真正的哲人那样提出告诫:“‘理性的偏见’并不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人们经常从考察某件事物出发,制定出一种推理模式,之后就会觉得应该按照这种模式而不是其他模式假设和思考。”
在埃科的文字世界,批评人民远比批评执政者危险。批评执政者,玩儿似的,批评人民,则意味着玩完。因此,埃科若要显示知识分子胆识,就得在这个领域有所尝试。他果然这么做了,埃科对于当时意大利电视台频频播放庭审直播,极为愤慨,民众却对此类节目欢迎不迭。埃科表示,他的专栏发表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全是误解和反对。一位学生模样的读者愤愤不平地质问他:“对于阿尔马尼尼的无耻行径,你难道无动于衷吗?”天下愤青都一样,他们不是缺乏正义,而是徒剩正义。埃科莞尔一笑,迎难而上,甚至还用一种夸张的绘声绘色,故意激惹反对者。他这样恶心他们:
“观众必须坐在餐桌边观看绞刑直播的场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犯人脖子的断裂声、腹部的抽搐声以及双腿的踢腾声必须与观众咀嚼食物的声音相融合;如果是电椅,则要让罪犯吱吱呀呀地尖叫几秒,最好与炉子上煎黄油鸡蛋时所发出的噼啪声相呼应。”
笔调是“调侃”的,内含的“愤怒”则不失庄重。实际上,埃科真正担心的是,个体权利会在庭审过程中遭到漠视和剥夺。他为这个主题写了多篇专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移驾一观。
总之,这位以畅销小说和大量以博学见长的著作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作家,有着难得的悠闲;即便在悠闲中,即便被迫在一个“报纸越来越幼稚”的环境下生存,他也无意把笔锋投闲置散。他试图证明,天堂里也可以有知识分子;在不存在政治迫害的地方,敢于无惧冷落,见微知著,发表逆人民虎须的异议,同时又并不自以为正确,也是一种非凡。至于“愤怒”云云,付之一哂可矣。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