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图虫网)
每当危机发生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会重提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我深知接下来我要谈论的内容会冒犯很多人,所以我应当事先声明我的立场:信息公开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围绕着信息公开所涉及的问题,还真的和信息本身无关。为什么这样讲?我想先讲个故事。
信息、谣言和公共治理,这几个词汇放在一起,许多学者会立刻提及一本书——孔飞力的《叫魂》。(此书每逢封城,必火)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本,史景迁的《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史景迁的这部在国内不那么有名的著作,讲述的是《大义觉迷录》的来龙去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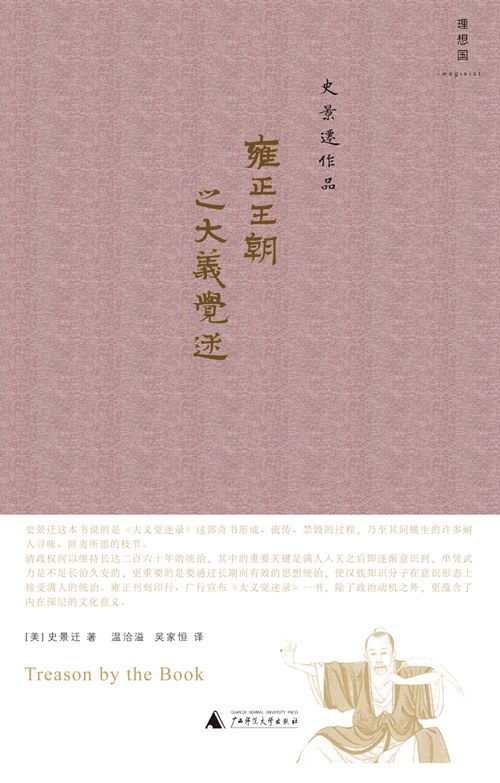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美] 史景迁 著
温洽溢 / 吴家恒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3月
《大义觉迷录》是一本神奇的书,我们都知道清朝皇帝的文字狱很有名,这本书正是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的产物,由雍正帝亲自耗费极大心力编撰的御制国书,到了乾隆朝时却成为一本禁书,停刊销毁。没错,清朝皇帝大兴文字狱最终竟然办到了自己头上。
事件的起因是曾静谋反案。曾静,湖南郴州永兴县人,一个被革除功名的落魄秀才。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1728年10月28日),其徒张熙向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投书策反。这封逆书原件已佚,不过好在有雍正帝的上谕,所以我们能知道其中内容梗概。大体就是中原沉沦,夷狄窃据神器,乾坤反复;践祚者雍正弑兄屠弟、谋父逼母,与禽兽无异,致使天地震怒,鬼哭狼嚎;敦促“天吏大元帅”承先祖(据说岳钟琪乃岳飞后裔)遗志,趁时反叛,为宋明复雠。
按理来说,这样一封荒诞不羁的反书对于见过大风大浪、富甲一方、权倾一时的川陕总督而言,不过就是山野刁民的一场小闹剧罢了,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鸡毛蒜皮之事。但岳钟琪却表现出格外的谨慎小心,严查此事,短短六日之内,先后三次向皇帝急递密折,汇报案件的最新进展。
而雍正这边呢,也出乎意料地非常重视。先是命人将案件材料誊抄记录,然后要求岳钟琪继续彻查,最后还动用了“廷寄”(雍正发明的一种秘密沟通信息的方式),令湖南巡抚王国栋、两江总督范时绎和浙江总督李卫协查岳钟琪递交的谋逆名单中所涉之人。
就这样,一件普普通通的秀才造反案向着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张熙供出了曾静,曾静又牵出了吕留良——一位早在四十五年前便已作古的文人。案子从雍正六年一直查到雍正十年,最终变成了天字号谋反大案,涉案百余人,吕氏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男子,皆斩立决。
但这还不是本案最奇特的地方,最奇特的地方在于雍正对早先的两位主角——曾静和他的弟子张熙——的“出奇料理”。他不仅力排众议,免二人一死,还不惜躬身亲问,逐一反驳曾静在反书中对他的指控;让审讯官员为曾静详细解释朝廷运作方式;允许曾静翻阅岳钟琪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将一堆刑案抄本交由曾静阅读,让其知道自己是如何秉公断案。雍正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平息围绕曾静案产生的各种“谣言”,而且雍正颇有些当代经济学家的“眼光”,他认为平息谣言的最佳方式就是信息透明,所以他要让曾静尽可能地了解“事实”。
果然,经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曾静真心悔过,写下了认罪书——《归仁录》。但仅仅教化曾静一个人还是不够的,雍正还要斩断天下的谣言,让天下人“觉迷”。于是他将这桩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案所涉的全部谕旨、审讯和口供记录集中在一起,再附上曾静的认罪书,汇编成了本文开篇提到的这部奇书:《大义觉迷录》。这还不算完,雍正从新科进士中遴选出四十人,远赴全国各州县,宣谕此书;并令各州县学官,必须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就是曾静案的结局吗?不是。当乾隆坐上帝皇宝座四十三天之后,案件再次发生了反转,乾隆降旨:“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以蔽其辜。”
殊不知,乾隆这道圣旨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因为雍正对曾静案生前有谕:“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但不管怎样,曾静、张熙立刻再度下狱,两个月后凌迟处死。《大义觉迷录》也尽数收缴销毁,凡私藏者,杀头灭身。
《大义觉迷录》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它展现了在真实社会制度下,信息、谣言和公共治理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
在经济学中,研究信息问题有一门专门的分支学科:信息经济学。不过在我看来,信息经济学更像是一门玄学。比方说,为了应对信息不确定问题,信息经济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有关信息的所有可能性都表述出来,并且指定每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分布。什么意思?例如我不知道明天我要吃什么,那么我就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写下来,然后还要指定每一样东西我会吃的概率是多少,最后设计函数进行最优化计算,找到那个我几乎、可能、大概会吃的玩意。也就是说,我要解决我的“无知”问题,我首先要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可既然我已经全知全能了,我还要学信息经济学作甚?这是一门高智低能人士发明出来的“扮演上帝”的智力游戏,和当下许多所谓的前沿理论一样。
其实在信息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学界早已讨论过相关问题,最有名的大概应该算哈耶克那篇叫好不叫座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使用了一个核心概念:分立的知识(divided knowledge),复杂点的用语就是“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在哈耶克看来,良好社会秩序的关键就是处理好每个人所掌握的分立的知识。
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应该都没看明白这个“分立的知识”指的是什么,否则也就不会有后世的二流经济学家把“知识”问题简化为了“信息”问题。其实哈耶克的这个概念来自于奥地利学派的知识论:首先他说的“知识”绝对不是单纯的信息,否则的话我们手里的智能手机肯定比我们更有“知识”,因为它连接着互联网,储存着海量的信息;其次,这个“知识”也不是通过教育或者技能培训所能获得的——能够传授的知识不是知识。
那么“知识”为何物?很简单,它指的是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能力,和基于这种理解能力基础上的对外在世界的控制能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就是知识进步的过程。
举个例子,人类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接触到了石油,但是并不清楚这是什么物质——这就是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能力,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我们开始用它作为防水材料,照明材料,甚至还用作军事武器;一直到19世纪中期,我们真正清楚了这种物质,并成功发明出提炼方法,但它还是没有成为一种主要能源来使用——因为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控这种物质;20世纪中期以后,我们终于能够掌控它,石油也最终成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动力引擎。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进步的过程。
所以,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包括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大义觉迷录》的整个事件,就是围绕着信息的获取、传递和扩散展开的,但是信息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各人的知识。岳钟琪的格外慎重是基于他的“知识”:对于雍正帝的了解,特别是仅仅十五个月前,他在成都府也陷入过类似事件,外加他作为川陕总督的敏感身份;而雍正帝则面临更多的“知识”:一是大清立国以来一直受到挑衅的“正统”问题;二是川陕作为战略要地,刚刚经历过年羹尧事件的动荡,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雍正精神紧张;三是一直以来对江浙文士的不满,在曾静案发生之前,雍正就已经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门整顿浙江民风。
同样,各方所为也是根据各自“知识”希望尽可能地掌控事件。岳钟琪想的是向皇帝传达自己的忠心,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引起雍正疑心,差点断送性命。雍正则相信以自己九五之尊的身份,应当能够控制事态发展;而要平息天下人的猜忌,必须“诛心”。所以最终决定全案透明化处理,“或者百千亿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
《大义觉迷录》的确是做到了信息公开、透明,但事件绝非按照雍正所希望的样子发展,因为民众也是按照自己“知识”行事:新的谣言又再度出现。而这又是乾隆帝所获得的“知识”,最终促使他一反雍正的“诛心”之策,改用“杀身”,便捷了事。
因此,当斯蒂格利茨们在宣扬信息公开的种种好处时,我们真的应该再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不是说信息公开不好,只是那些公开的信息转变为民众分立的知识,进而发挥实际的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而其中的运作逻辑,说实话,至今我们的专业人士仍然没有搞清楚。所以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极其难以预料的。
如何处理个人只拥有“分立的知识”?这还真不是看看微信朋友圈的消息,或者宅在家里多读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流量为王、大数据横行霸道的时代,信息大爆炸反而加剧了知识的困境,进一步分立了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和掌控:因为我们不是依据信息而行动,是依据信息的意义而行动。同样的信息,我们每个人的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我们的能力、经验和信念。
不过哈耶克至少有一点是对的,良好的信息交流沟通机制,是我们目前能够解决知识难题的最佳方法,即我们需要一个良序的信息市场。否则,就会像《大义觉迷录》那样,在扭曲的皇权体制下,无论信息如何透明和公开,雍正的“屠龙术”最终也会变成乾隆的“杀猪刀”。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