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向阳/文 在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也有人称之为“中间阶级”,对应英文的“themiddleclass”)?在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指标特征,学者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社会终究存在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幻象”,是不容置疑的。
之所以说是“生活幻象”,是因为这个阶级的确短暂地存在过。根据经济史学者黄英伟和袁为鹏的《民国中产阶级账本》,关于民国时期江南乡绅董士沅的私人生活研究,结合许多学者关于鲁迅日记中大量账本式私人生活的研究,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过,中产阶级作为当年西方思想的舶来品,的确成为了民国时期从文化领袖到普通乡绅的个人生活追求和自我形象定位。
鲁迅对身属“中产阶级”的自我界定,一直要等到他正式定居上海之后的41岁那一年。他在1932年4月30日夜编写的《二心集·序》中写道:“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诚然,鲁迅对自身“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定,并非基于更重要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定,更是关于一种社会形象的自我身份认同——即一种介于权贵阶层和底层大众之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夹心饼”式的“中间阶级”。
中产阶级的痛苦大抵也源于此。在鲁迅自我意识到中产阶级定位的四个月前——1931年12月,鲁迅被从“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上裁撤掉,这是他个人生活中的最后一个公务员身份,从此之后,他彻底转换成为一个靠码字为生的自由人。
在此四年前的1927年10月,鲁迅刚刚结束在厦大和中大的不满一年的南下动荡岁月,四顾茫然,生计无着,漂泊无依,不得已情形下,向同乡兼伯乐蔡元培求援,再表葵霍向阳之意。早在1912年2月,鲁迅经好友许寿裳推荐结识蔡元培,后者推荐他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在“社会教育司”当了14年科长,并一度聘请他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讲师。
当时蔡元培新任刚成立的“国民党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以爱才之举,蔡公再施援手,首批聘请吴稚辉、李石曾、马夷初、周豫才、江绍原五人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月奉300银圆“编辑费”,让他们可以从事自由创作。一直到1931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任教育部部长之命裁撤该编辑费,鲁迅领取了4年又1个月的“编辑费”,共计14700银圆(折合2009年人民币103万元)。
时局艰难,生计难继,鲁迅自己认定的“中产阶级”不免带有一点点自嘲。从1932年跻身“自由的中产阶级”开始,鲁迅为了谋取这点自由,开始了焚膏继晷的卖字生涯,不到5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八部作品合集(包括编辑出版了后来获得大卖的鲁迅、许广平通信集《两地书》)。一直到临终前的1936年10月17日,鲁迅还在伏案写作他最后终究没有完成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相比鲁迅,乡绅董士沅的中产阶级自由生活更没有好到那里去。根据学者黄英伟对《董士账本(1936-1942)》的研究,江南乡绅董士沅的活动区域多为南京、上海、宿县和武进县一带,1937年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后,这位商界主人不仅失去了月薪46元的工作机会,标志其生活水准的恩格尔指数,迅速从1936年的0.25(富裕水平)飙升到1938年的0.605(贫困水平),而且不得不通过改换住房、出售字画和减少洗澡修发等服务性消费,来维持生计。
动荡时代里,战争、疾病、以及任何一场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都会将中产阶级所允诺的自由击碎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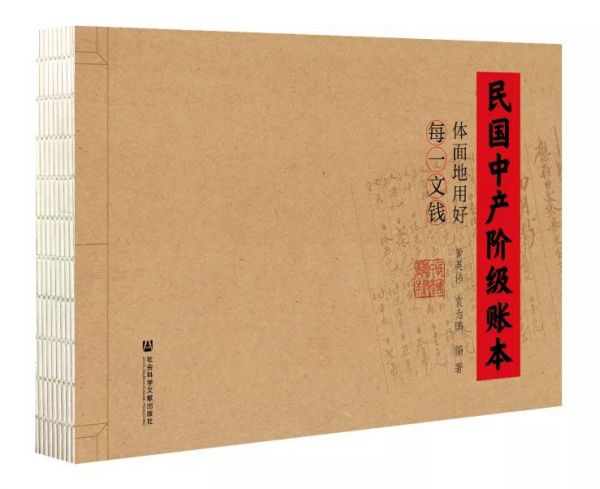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副标题: 体面地用好每一文钱
黄英伟 袁为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月
爱自由,还是“伪自由”?
《董士账本(1936-1942)》的主人董士沅,是一位民国时期的乡绅,他是江苏武进人,经营着一家和粮食贸易相关的商号,位于安徽宿州市符离集镇,因商号总部在上海,他不得不常年奔波于上海、南京和符离集。如果仔细研读《董士账本(1936-1942)》中的每一笔花销记录和每一个数字,可窥见一位地方乡绅私人生活中的欲望和情感、社会交往和精神世界。
董士账本记录的时间始于1936年1月,止于1942年2月。从翻开第一页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位中年中产阶级生活的忙碌和哀痛。1936年2月14日,是账本主人母亲去世两周年忌日,他花费5元钱举行了一场佛事(大祥)。到了三月底(清明前后),他又专程回乡为母亲举行隆重的葬礼,安葬的直接花费为50元。
除此之外,其他相关的费用包括:路途往返车费11元5角、橘子、点心、香烟及黄包车费用等共1元3角,洗浴及车力费6角,回宿县车力、行李搬运费及茶水费8角,堪舆费用8元(付给刘博溪先生),晚间请刘先生用饭2元,以及这一年的十月十三日(阴历),为母亲举行除灵仪式花费了6元5角。
对于董士沅来说,这一年祸不单行。在专门回乡为母亲举行除灵的第二日夜里,1936年十月十四日(阴历),其父亲因与二弟发生口角(可能与除灵费用分摊等家中琐事相关),引发中风,第二日即去医院请许乐山大夫医治,花去医费2元、“车力、挂号、病原课”检查等费用1元,药费1元5角。主人感觉不妙,还在当时就购买了寿衣料和棉布,分别花去16元8角和1元5角。后来十六日(阴历)再请许大夫看病,花费2元,然而,其父最后还是未能治愈,于十月三十日(阴历)午时病逝,死后第三日即举行大殓。
账本主人写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其心情可见一斑。
真是哀中年之多艰。账本主人在1937年的账本上,还特别记录了一段在回老家参加岳父葬礼后坐火车返回符离集的所见所闻及心情:“源因岳父举殡,回里办理安葬一切之事,事毕回符栈供职。由家至车站,天时阴霾,至站后不意大雪纷飞,一路之上,至南京下关时风雪未住,渡江至浦口站上车之后,雪略小。至天明时至蚌站,风雪已止,气候甚寒。至固镇站,天际红云朵朵,旭日高照,精神为之一振。源旅行往返,逢大学纷飞,为第一次也。”
短短一二百字,写雪后初霁的景象万千,写作者悲欣之际的心情转换,大有明清性灵散文的神韵妙笔,而人生如寄寓、悲喜化大浪,账本主人精神境界的自由意识和审美态度也毕现其中。
按照哈贝马斯在其开创性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变革》中的说法,18世纪报纸和小说等代表的印刷文化的流行,为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身份塑造的可能性:通过他们所喜欢的书面文化,才得以构建他们独特的社会身份和自我形象。
如果说十八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典范读本是都市报纸、《旁观者》杂志、《约翰逊字典》和《圣经》等这样的流行读物,那么19世纪则换成了《简·爱》和简·奥斯汀的小说,而在21世纪初中国中产阶级的橱窗里,一定会少不了《哈佛女孩刘亦婷》和《文化苦旅》,前者代表了这一阶层的焦虑和梦想,后者则是他们的精神“面子”。而在董士沅那里,则是他大量购置的书籍和字画。其搜罗内容之广,品类之丰,从当时流行的西学书籍如《法律质疑会刊》《算书》《英语词典》,到《诗经集对》《左传》《史记》《王荆公文集》《官场现形记》,乃至包括《心经》《金刚经》和美术史、铁道史等各类书籍。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和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来说,阅读趣味和阅读代表的生活方式,不仅标识了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个性追求,更是和下层划清界限和抵御粗鄙生活的一种形象姿态。养家糊口之余,如何安身立命,超然于物质生活之上,才是他们构建人生自由的第二重维度。
当然,董士沅作为中产阶级的趣味和生活态度还不止于此。他用精致典雅、游龙戏凤般的老道小楷记录个人生活,他迷信风水又酷爱个人卫生(战争发生前相当频繁洗浴理发搓澡扦脚),同时又钟爱宜兴紫砂壶和品茶,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甚至热爱字画艺术和创作,这些都标识了其超脱物质欲望之上、怡然自足的精神追求。
相比于乡绅董士沅的中产风范,大文豪鲁迅自然走得更远。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旧时代风雨飘摇,鲁迅和林语堂也赫然出现在北洋军阀的暗杀名单上,这一年7月,鲁迅收到林语堂南下赴厦门大学的邀请,他知道,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机会来了。
虽然鲁迅对在厦大和中大的教书生涯并不满意,但是自从有了“女友许小姐”的陪伴(林语堂语),鲁迅在个人生活中第一次享受到了自由恋爱的滋味。南方不像北平那样沉闷,空气里到处都是革命和自由的新气息。
《两地书》里浓浓的甜蜜爱意,甚至进一步拓宽了鲁迅的理想生活的边界,他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自由中产的生活图景:“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
中产阶级最爱自由,更明白自由身外处处皆是枷锁。内心的一面,鲁迅其实也非常挣扎,比如他还是希望在民国政府的中央研究员能够谋得一个职位,这样可以确保这个小小的自由爱巢有更扎实的物质支撑。事实上,等到他1932年真的恢复了完全的“自由之身”,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卖文为生时,他才发现,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统一思想”的文化统制政策之下,他的中产生活已经面临危机。从1934年开始,鲁迅和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受到查禁。
最是文人不自由。1933年10月,鲁迅将他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一系列批评时局的文章,结集为《伪自由书》,由北新书局化名青光书局出版。从那时开始,鲁迅最担忧的自由毒手出现了。

鲁迅日记(全三册)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
中产之忧:自由的毒手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这一阶层的体面生活和个人形象之尊严,无时无刻不遵循如下法则:“体面指数=社会形象的成本-个人欲望的成本”
这里的社会形象,是指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理想生活方式/自我的社会形象期许,个人欲望是指维持生计所采用的生活标准。两者相减所得,就是其人生自由度/体面生活/个人尊严的范围区间。
在这个公式面前,维持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最大危机,无一不是来自外部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战争、动乱、疾病(常常体现为外部生活环境强烈变化之后的后果)等所带来的巨大剥夺感。
甚至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时期,中产阶级的命运在名士鲁迅和乡绅董士沅那里存在着某种传承和交汇。鲁迅日记中的中产阶级账本,从1912年5月记录到了1936年10月,整整24年又5个月,而《董士账本》里的账本记录,始于1936年1月止于1942年2月。我们无法假想,1936年鲁迅如果能继续活下来,他的中产生活该如何继续,当然也难预知董士沅们的中产阶级之梦,还能否依旧维持做得下去。
事实上,鲁迅1928年偕许广平定居上海后,蔡元培的再度援手,为鲁迅当时青黄不接的中产生活提供了最重要的自由保障。教育部当时每月300银圆的“编辑费”,占据了鲁迅这一年总收入(共5971.52圆)的55%以上。到了1929年,鲁迅开始为捍卫著作权向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也是鲁迅的学生)提出版权诉讼,追回其应得的累计2万银圆(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140万元)的版税收入,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两年内分两次还清。
从1934年开始,受到国民党查禁书籍的影响,鲁迅的写作收入明显下降,1934年和1935年的月均收入都在470圆左右,而每个月的花费也至少需要四百圆(其中购书也需要100圆左右,平均占据年收入的10%以上)。鲁迅也成了“月光族”,时局动荡,加上忧思愤懑和积劳成疾,55岁就因肺病去世。
和鲁迅晚年的生活情形相似,乡绅董士沅的战后中产生活,同样处处面临危机。物价飞涨,失去工作,节流(减少消费次数)和开源(出租自有房屋并承租廉价房屋获得差价)并行,依然使这位绅士的日常生活陷入贫困。
家庭账本作为中产阶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通过量入为出,从而时时刻刻可以维持一种更为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从鲁迅日记到董士账本,中产阶级的家庭账本,不像会计簿记账本那样专业严格,也不是底层阶级的无账可录(来源和花费一样稀少),它更象征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态度,闪现了对自由的珍惜和有趣味的生活温度,就像鲁迅1923年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所描述的那样: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鲁迅先生的忠告言犹在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所爱和所怕,其实是同一枚钱币的两个面向而已:如果自由和财富可以被随时或随意剥夺,中产阶级的生活恐怕只能剩下一地的碎梦,成为一种幻象罢了。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