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展雄/文 沙俄时代,俄罗斯压路机强悍快速的军事推进能力跟缓慢的国族认同感建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自1426年脱离蒙古统治以来,莫斯科公国以每天17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一战前其领土面积已经达到2300余万平方公里。然而新征服的地区生活着众多少数族裔,主体民族甚至不到总人口的一半,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俄族仅占全国人口的44%。
沙皇无法整合被征服者的语言习俗,使他们团结一心。甚至可以说,俄国本身就是希腊和法国文化上的殖民地,更不可能去同化别人了。
国内关于俄罗斯和斯拉夫文化的出版物,近年来有后浪图书《拜占庭的赠礼》、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圣彼得堡》,再远一点有东欧问题专家金雁的扛鼎之作《倒转红轮》。如果想深入了解这方面,不仅要懂得今天的美俄争霸,欧盟扩张的国际格局,还要追寻文化上的根源。
俄国的希腊化变革
沙皇俄国共经历了两轮文化变革,18-19世纪法国文化输入了一轮。彼得大帝把西式的首都(圣彼得堡)和西式生活,一并带到了落后的祖国。沙俄的王孙子弟开始受法国家庭教师教育,学习凡尔赛宫廷的礼节文化。
沙俄上流社会的西化程度极其高,在剧院等公开场合,以法语为标准的社交语言。精英阶层有的人甚至不会讲俄语,《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的家庭环境完全西化,直到1906年中学阶段才开始从头学俄语。大概是因为1905年革命震动了上流社会,贵族们才匆忙了解祖国的语言文化,而给纳博科夫当俄语老师的正是社会革命党领袖日诺谢科夫。
其实在法国之前,俄国社会已经接受过拜占庭文化的洗礼。1653-1666年,莫斯科的东正教领袖尼康,引入希腊礼仪和希腊语《圣经》,革除斯拉夫本土传统,史称“尼康改革”。
尼康以冠冕堂皇名义,驱逐基辅罗斯时代留下的异端性质的多神教、万物有灵崇拜残留,强行把希腊正教的规矩施加给本国,圣书、颂词、祈祷等全部按照希腊文本进行校订。然而俄国文化的精华正是夹杂在多神教、万物有灵崇拜里面。
一部分神甫承接斯拉夫本土特色的教会传统,是之为“旧礼仪派”,官方教会则攻讦他们是“分裂者”,双方捉对厮杀,斗得热火朝天。世俗政府蛰伏待机,沙皇阿列克塞先是默许支持尼康,然后再借着民怨废掉尼康,但他并没有废掉整个新政策,而是把宗教力量化为己用,为王权服务。旧礼仪派从此逃亡,躲避莫斯科中央的迫害,直到1905年革命,尼古拉二世迫于立宪潮流,承认宗教宽容的现代理念,他们才光明正大地现身。
索尔仁尼琴以抗拒现代化和工商业资本主义而闻名,然而他对东正教会并无好感,多次拒绝教会伸过来的橄榄枝,因为现存的官方教会经过了尼康和阿列克塞的阉割,真正的传统体现于旧礼仪派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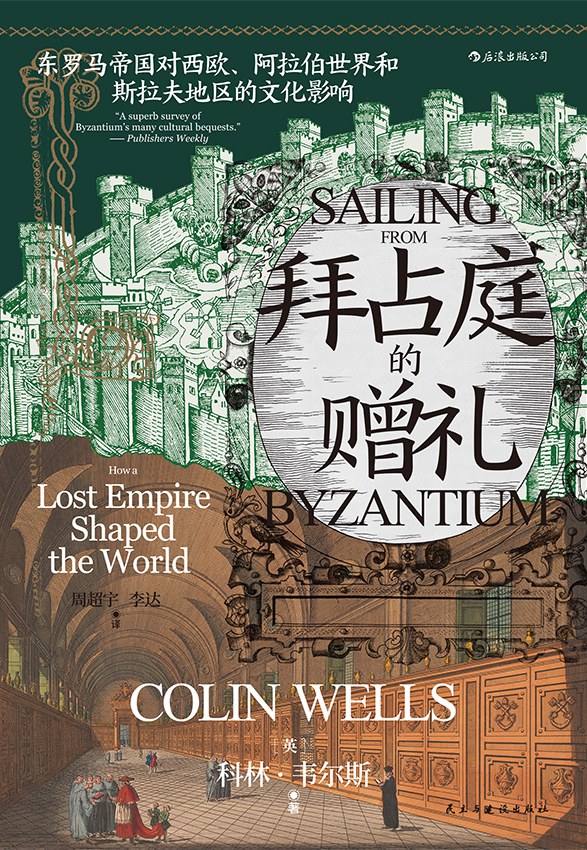
拜占庭的赠礼
[英] 科林·韦尔斯/著
周超宇 李达/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2年1月
双头鹰的扩张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俄国的希腊化是注定的,之前的基辅罗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走上了相近的道路。
在亚伯拉罕宗教的各分支中,新教和犹太教比天主教朴素,而天主教又比东正教朴素,擅长宫廷礼节的拜占庭人把繁文缛节移植到教堂里。点有油灯的昏暗教堂内,马赛克壁画和圣像的色彩鲜艳,焚香的气味缭绕,复杂繁琐的敬拜仪轨,塑造了一种迷宫般的景象,令信徒沉浸于神秘之美,于是有了基辅受洗的宗教盛事。
半开化的保加利亚人接触到高级文明后,立即陷入皈依者狂热。十三世纪初期,保加利亚王国学习君士坦丁堡的城市规划,来营建自己的首都,这座城市还被人称作第三罗马,承接此前的旧罗马与新罗马。西米恩登基后,坚持不懈地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拜占庭的赠礼》解释道,这并非代表着西米恩憎恨东罗马,恰好相反,他热爱并崇拜着东罗马,他从小在那里接受教育,被他们同化,因此萌发出旧邦新造的理念。
维也纳以西的雄主,莫不惦记着拜占庭,并立下“彼可取而代之”的誓言。后来,异教的奥斯曼也加入到逐鹿问鼎的行列。通常来说,一个政权最重要的时刻是开国立朝,然而在奥斯曼的历史上,攻克敌国首都的意义更为重大。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土耳其人已经横跨欧亚大陆,东罗马帝国的土地丧失殆尽,只剩下首都一隅。如果穆罕默德二世仅仅想割据一方,他尽可让拜占庭苟延残喘,做自己的附庸国,但若想成为正统王朝,必须得拿下帝都。战略学者明克勒把大国建立霸权的关键一环称作“奥古斯都门槛”。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窃据了凯撒的头衔。希腊的历史学家把苏丹比作亚历山大大帝,特拉布宗(拜占庭皇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向他朝贡觐拜,一些欧洲人把奥斯曼的领土称为“罗姆”,即土耳其方言的罗马一词。而拜占庭皇帝的侄女则流亡远方,嫁给了伊凡三世。紧接着,尼康改革以拜占庭为样板国,进行大改造。从此半开化的俄国人跨级升格为帝国继承者,莫斯科大公自命为罗斯诸部族的最高主宰,莫斯科主教为全体东正教徒的最高牧首。
罗曼诺夫王朝有过许多外敌,瑞典、波兰、满清、日本,但没有一个能和土耳其相比。海峡(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海峡)和帝都(君士坦丁堡)是历代沙皇最渴望的战利品。夺回拜占庭是庄严圣洁的事业,能够荣耀主耶稣的权柄,索菲亚大教堂必将归还给它的合法所有人,在俄国的民间俚语里,“沙皇格勒”指的不是莫斯科、圣彼得堡,而是君士坦丁堡。
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三世,哥萨克铁骑向南方发起了十一次征服战争,其兵锋最尖锐所达,距离敌国首都仅仅三十公里。如果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干预,苏丹早就被赶回草原。
俄国双头鹰一面朝向西方,一面朝向东方。数百年来伊斯兰和基督教拉锯的亚洲高加索山区,天平出现了明显的倾斜,1828年,尼古拉一世出兵攻打车臣人。沙皇施展分而治之的手腕,联络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教友,遏制穆斯林族群。
自柔然突厥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总趋势为:亚洲的游牧部落向西迁徙,一路摧枯拉朽。莫斯科大公好不容易赶跑金帐大汗,西迁的蒙古卫拉特部落,正好乘虚而入——1613年,4000名卫拉特骑兵渡过乌拉尔河,杀入到乱局,当地人称呼他们为卡尔梅克人。
为了抵挡蛮族,俄罗斯人修筑了简易版长城,开挖壕沟、木栅栏,哨兵在堡垒警戒。这条名为别尔哥罗德的防线,绵延上千公里,只是知名度低于明朝的长城。
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反攻。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逼迫下,一部分卡尔梅克人回到亚洲老家,这也就是乾隆时期的土尔扈特部东归。从1864年至1865年,沙俄征服了浩罕汗国;从1866年至1868年征服了布哈拉汗国;1873年征服了希瓦汗国。哥萨克的铁骑夷平了中亚大大小小的汗国,一些部落首领改而效忠沙皇和耶稣,成为了保卫俄国的盾牌,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就是蒙古后裔。
基督教同时开辟高加索、中亚、巴尔干三条战线,亚洲的伊斯兰教、萨满教和佛教各民族,纷纷拜倒在第三罗马的面前。
俄国灵魂的萎缩
然而,俄国的文化征服远远不及军事上的铁血征服。
沙皇中央政府花费巨资在哈萨克人中宣传基督教,皈依者寥寥无几。在吉尔吉斯,到1900年为止,教会花费了2.7万卢布,却只吸纳了58个信徒。
不仅如此,还发生了反向的文化输出。19世纪50年代,殖民者首领米哈伊尔·沃尔孔斯基在攻克布里亚部落(蒙古民族的一个分支部落)后,特地派了一个哥萨克小分队来村子里教俄语,一年后沃尔孔斯基回来检验工作成果,情况是:没有一个布里亚人能够用俄语交流,但是200个哥萨克人都会讲一口流利的布里亚语。
直到工业革命后,俄罗斯凭借更先进的工业文明勉强占了上风,俄国人盖起欧洲式的歌剧院和音乐厅,100多万俄国人应募开垦哈萨克草原。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俄农民向东迁徙,带来了西里尔文字、儒略历和东正教。游牧部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在罗曼诺夫王朝倒台的前夕,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占人口比重下降了14%-15%。
后来的苏联,一手延续老沙皇的俄化政策,输入俄罗斯移民人口,推广俄语;另一手给甜头,大力增加对异族的财政扶助。斯大林实行的五年计划,“一五”至“二五”期间,中亚地区的财政经费大部均来自苏维埃中央。
二战的军备需求,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斯大林逐步把欧俄地区的产业链迁至远离苏德边界线的后方,共有308个大型企业疏散到中亚。冷战期间,中亚继续享受克里姆林宫的援助,拥有低息贷款、不上缴利润、免税等优惠政策。直到今天,中亚人脑子里仍保留各民族一体的苏联空间意识。哈萨克斯坦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出去闯荡往往优先选择纽约,伦敦,柏林。但是在上一辈和广大农村的哈萨克人的世界观里,莫斯科才是庄严的天下中心。
总体而言,旧沙俄的民族政策无法同化西方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民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对落后的中亚草原部落,也仅仅稍微有一点优势。而归根结底,传统的斯拉夫文脉在尼康和阿列克塞的改革后被拦腰截断,俄国本身的文化向心力不足。
莫斯科很早就接纳了东正教,但长期以来,这种宗教只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成分,自行发展,也不受官方控制,跟拜占庭式高级成熟的东正教有着天壤之别。
基辅洞穴修道院是斯拉夫人的学术中心,东罗马的政教合一意识以基辅为中转站向北方传播,一条通向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一条通向莫斯科大公国。17世纪20年代,乌克兰的文化精英用帝国蓝图来劝诱华沙的统治者,试图再建东正教天堂,然而拜占庭式的王权至尊观念与波兰-立陶宛分散的联邦制度、天主教徒占多数比例的人口格局无法契合。
于是,基辅的教士们折向东北方的莫斯科,为尼康和阿列克塞的改革提供了大力支援。他们把沙皇塑造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基辅都主教区几乎失去了自主的独立权,尼康改革实行十多年后,俄国强行夺下基辅的教会管辖权。
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是东正教知识分子的叙拉古之旅。原先的莫斯科教会,上不臣天子,下不敬诸侯,有权向君主提出谏言,按照拜占庭的模板改造后,教会成了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当东正教在尘世疆土不断扩张,实现东罗马帝国使命的时候,其灵魂却在萎缩。
因此,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斯拉夫主义者,极力抨击改革后的东正教,如同中国黄宗羲等原教旨儒家人士,反感汉代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
神学学生成了民粹分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延续东正教核心理念的却是近代的左翼青年。
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不到20%的人是非贵族出身,到1875年,大学生总数的46%由神甫子弟构成。
跟优雅、悠哉悠哉的贵族博雅教育不同,神甫子弟自小要在神学院里接受严厉训练,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睡“钉子床”,这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写照。当他们离开封闭保守的家乡,来到大都会圣彼得堡后,便惊讶于贵族知识分子的放荡浮华。
贵族们坐而论道地谈哲学,在太太们的客厅里谈论国外的时髦艺术,这一切都令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厌。最可憎的是,这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精英大谈自由人权,抵抗沙皇专制,装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模样。
民粹派群体里,神甫子弟比例奇高,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都属于这个群体。这倒不难理解,在文盲遍地的村镇,神甫属于极少数的读书人阶层。比赤贫农民的孩子领先在起跑线,但是在贵族子弟面前,他们又显得卑微。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境遇,足以酝酿出不满社会的叛逆意识。
当经济大环境恶化,平民知识分子普遍下滑,从事低端的工作岗位。1882年,莫斯科6319个僧侣后代,只有40%的人子承父业,其他的成为下级文秘人员、医生、教师和演员,甚至失业。 他们普遍有怀才不遇的愤慨,除了革命运动,再无别的地方能吸纳这些怒气冲冲的灵魂。于是,迷惘的羔羊转向民粹运动,试图建立左翼的人间天国,宗教学校里养成的禁欲主义转化为革命禁欲主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转化为打倒沙皇贵族的革命平等主义,上帝崇拜转化成了“人民”崇拜。
1905年革命前,各路反抗沙皇的组织无论纲领主张分歧多大,组织成分都很相似——几乎离不开神学院背景。仇恨作为燃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革命动力。原本温和的气氛,骤然火药味十足。自由主义运动在新一代知识青年的领导下,朝向激进化。
沙皇政权的另一个敌人,是拒不服从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信徒。他们对沙皇的仇恨程度,不亚于左翼革命者。旧礼仪派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庇护收留通缉犯,尽管不赞成唯物主义无神论,但乐于为任何朝廷的敌人提供援助。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轻工业企业家、“纺织大王”莫罗佐夫,他的遗产资金经过复杂的渠道,汇聚到列宁手里。
如果把目光放长远,就会发现东正教过去不乏相似的案例,地下异端派系被打压、开除教籍,他们视拜占庭官方为“敌基督”,锲而不舍地发起暴动。
终于,宗教战争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中,以全新另类的面貌出现。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三罗马,在各路反对派的联合打击下,轰然倒塌。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