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2-02-26 10:03

![]()

马向阳/文 1937年春天,27岁的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拎着一只手提箱登陆纽约码头时,还是一个满怀新希望的年轻人。这一路他从英国辗转来到美国,新工作是担任英格兰和苏格兰几家报社的驻美记者,并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几家欧洲金融机构提供财经咨询服务。在他身后,是被这位年轻人遗弃的“瘫痪”欧洲大陆。
此时的德鲁克还没有暴得日后的显赫声名。早在1933年,希特勒还没有在德国真正掌权之时,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敏锐观察记者,就在构想一本关于“集权主义的起源”的作品,这本书后来他取名为“经济人的末日”,并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
《经济人的末日》是德鲁克著作等身的系列作品中的处女作,在该书中,德鲁克使用他最擅长的“旁观者”视角,全面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纳粹集权主义出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商业土壤,甚至准确预言了纳粹最后的“社会解决之道”——计划屠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来的妥协,这本随处闪现着思想火花的小册子,显现了德鲁克式样的社会洞察力。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末日》里的基本判断,你都不能不惊诧于德鲁克的社会分析能力和哲学思辨深度。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回望和理解上世纪初深陷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的欧洲大陆,还能如果用它来透视剖析我们今天所处的混乱而又危机四伏的后疫情世界,虽然时过境迁,然而它依旧没有过时,依旧还是那样睿智翩翩而又生动栩栩。
如何理解“群众的绝望”
作为一个最富洞察力的记者,德鲁克的写作特点就是喜用社会史的全盘系统分析方法。《经济人的末日》关注集权主义在上世纪欧洲的起源,和同时期同类题材比较,这本小册子既不是奥威尔笔下《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中的寓言小说式的隐晦批判,也非汉娜·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那种掉书袋式的、唯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架构。德鲁克之所以是德鲁克,是因为他始终以“社会”的眼光来观察、思考和记录社会——特定时期的商业、历史和思想等领域的社会变迁。
在德鲁克看来,一个社会之所以具体、生动和真实,是因为每一个社会都奠基于某种概念之上,这种概念会用来“涵盖人的本质、社会功能与地位”。
“不论这个概念是不是人类本质的真实写照,都一定会真实反映出社会的本质,而社会也依此概念来辨识、鉴别自己。这个概念呈现出它所认为社会中具有决定性且最重要的人类活动范畴,并以之作为社会基本原则和基本信仰的象征。”一战前的欧洲大陆,正深陷资本主义的失败和无能,最后为纳粹主义这一乌托邦的炫奇概念出现,提供了虚无的思想土壤和真实的行为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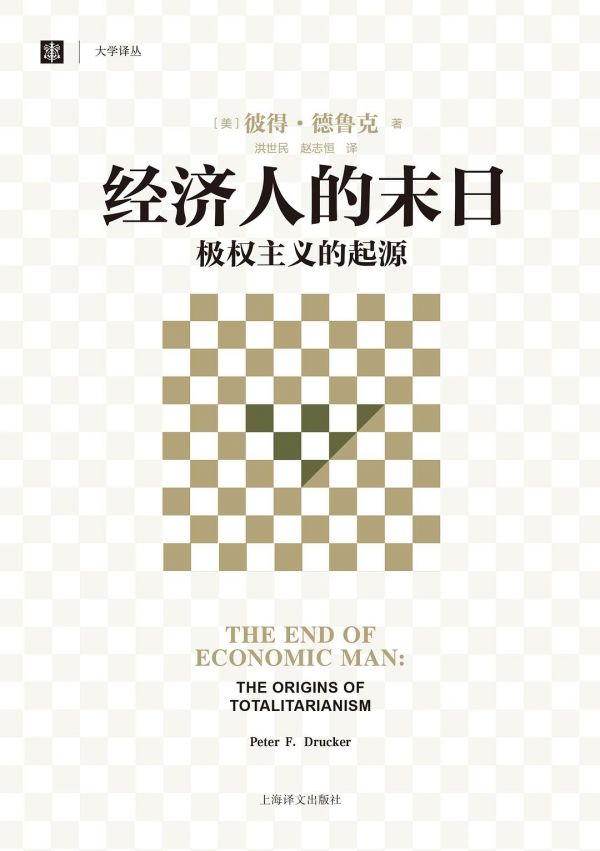
经济人的末日: 极权主义的起源
[美] 彼得·德鲁克 / 著
洪世民 赵志恒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8月
在德鲁克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西欧,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后,旧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崩塌,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权威又未及时建立,法西斯集权主义才找到了一条历史夹缝,迅速在欧洲蔓延开来。
按照德鲁克的观察分析,当时纳粹代表的集权主义除了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少数西欧国家受到欢迎之外,其实遭遇到了普遍性的敌意。在欧洲的大多数人看来,集权主义带来的残忍、激进以及充满仇恨的口号及信条,无疑是令人害怕、担忧和憎恶的。虽然纳粹法西斯是以一种所谓全新的“革命力量”出现,但和此前所有的欧洲革命不同,即便是置身“旧秩序国家”的少数族群,也无法接受集权主义的宗旨、精神和目标。然而,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并不能影响集权主义迅速取得社会优势地位,并且持续、稳定地向其他地区蔓延,直到最后称霸欧洲。
在德鲁克看来,欧洲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将自由平等的概念投射到社会存在和现实层面的历史。然而,法西斯主义区别于欧洲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进步革命,其典型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
法西斯主义不再包含任何正面积极的意识形态,而是一味地驳斥、打压和否定所有欧洲传统,包括自由平等这一最重要的传统基石。
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批判一切旧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与社会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以及依据该制度建立的管理机构正当性,更是罕见地将绝对权力视为唯一的正当性。
普通群众之所以笃信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西斯要成为一种积极信条,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类所谓的积极承诺。
除了这三个症候之外,纳粹法西斯主义还隐藏了一种奇特的症候,那就是投其所好——投群众所好的心理学。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德国,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纳粹的承诺,甚至连包括希特勒、戈培尔等最狂热的纳粹头目,也对纳粹信条漠不关心,就像戈培尔每次在群众集会时听到人们为某个精辟谎言欢呼时所说的那样:“当然啦!你们知道一切都是宣传。”
纳粹内部对自己的信条也讪笑不已,就像对待那份著名的描绘纳粹国家蓝图的内部文件“包斯罕”计划一样,非纳粹党的党外人士更是公开嘲笑它们,纳粹的这些想法如此荒谬,群众却依旧纷纷投入纳粹的怀抱。
这门群众心理学如此诡异、复杂,却又如此普通,是因为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斥,日用而不知——危机时刻,人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时时刻刻在祈祷、期盼并相信奇迹会出现,而自己可以逃过一劫。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陆几成废墟,旧秩序的坍塌,并没有换来人们在资本主义废墟中设计建立出任何新秩序。按照德鲁克的分析和观察,人们之所以投向法西斯主义的怀抱,恰恰是因为法西斯信条的荒谬、自相矛盾和不可能——“因为如果你被困在过去的洪流里,无法回溯来路,前方又是一堵显然爬不过去的白墙,你就只能期待魔法会奇迹来救你了。”
最终,思想大师德鲁克站在“瘫痪”的欧洲大陆之上,体会到了最深沉灰暗的痛苦之后,喊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我信,正因为荒谬!”
从“灵性人”到“经济人”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都市,就像德国电视剧《柏林巴比伦》中所呈现的万花筒一样,一度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试验场。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和纳粹极权主义在那里纷纷登场。作为资本主义废墟之上结出的虚无主义恶之花,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出现,正是利用了欧洲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思想真空。
为了宣称自己实现“真正的民主”,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允许社会留下一系列空洞的文化形式,同时又以暴力革命允诺了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社会,其代价则是整个欧洲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传统价值理念被全部抛弃,还有额外的一条严苛规定:投票反对纳粹独裁者,就是违法之举。
综观欧洲史,相信人人皆自由和平等,乃为欧洲思想之精髓。德鲁克认为,11-13世纪的基督教思想是一种“灵性人”(SpiritualMan)的概念,人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被看作是在灵性秩序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关于人们有权利从心灵层面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纪元。
灵性秩序崩溃之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开始转向了智识层面。路德教派鼓励人人可以用自己的理解来领悟《圣经》的教义,和上帝直接对话。在德鲁克看来,这是“智性人”(IntellectualMan)秩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刻——人们开始在社会层面追求更加真实的自由和平等,人先成为“政治人”,后来又演变成了“经济人”(EconomicMan)。“经济人”的概念,在经过亚当·斯密及其思想学派的加持之后,成为了20世纪最时尚的社会概念。作为一种虚构角色,经济人被鼓励可以奸诈狡猾、不择手段,并且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每个人行动的依据。这一学派深信,经济自由可以带来社会平等,且经济增长没有尽头。
在德鲁克看来,欧洲人想要通过资本主义来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已经幻灭。资本主义在经历了200年的发展之后,为欧洲带来了物质高峰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其所允诺的平等社会,甚至连“机会均等”这样的形式平等也消失了。经济自由的平等神话破产,不仅使得无产阶级信仰幻灭,连获得最多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中产阶级也未能幸免。
活跃在西欧的所有这些社会思想试验的溃败,为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出现提供了温床。一开始,法西斯主义还只是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到了30年代中期,纳粹们开始在思想领域大举进攻,在否定欧洲传统的同时,宣称“权力本身就是它的正当性”,即所有的权力都不证自明,就像墨索里尼声称的那样:“行动先于思想”,革命理应先于新信条或者新的经济秩序的发展。
纵览欧洲史,过往所有的革命都发生于知识领域或社会领域中(或者两者同时),“伟大的历史人物”充其量只是导火线或工具。但在法西斯那里,对于权力独裁者的赞美变成了“墨索里尼创造历史”。在法西斯宣称的“行动”(革命)发生之时,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任何积极的社会信条或者是新的社会经济秩序。
结果势必是,极权主义者把否定一切作为其政治纲领,同时也否定了本质对立的思维或者趋势。就像德鲁克所说:“法西斯主义既反对自由,也反对保守;反宗教,也反无神论;反资本主义,也反社会主义;反战争,也反和平;反大企业,也反对被认为是多余的技术工人和店主。”
这样一来,纳粹主义开始精心允诺了一个相互矛盾、根本就不存在的乌托邦社会。1932年,戈培尔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声称,:农民种谷物的收入会更高,工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面包,而面包店和杂货店会有更高的批发和零售盈余。这一时期,希特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向非常具有阶级意识的金属制造者业主承诺,只要纳粹主义存在,他们就一定可以夺回自己的经营权。
最终,几乎所有的工厂业主和许多劳工都成了纳粹的信徒。德鲁克曾经亲眼目睹了一个纳粹煽动者在一次农民疯狂欢呼的集会上的公开演讲,这位演讲者宣称:“我们不需要面包太便宜,我们不需要面包太贵,我们不需要面包的价格一成不变——我们只要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
当一个社会只留下空洞的文化形式、同时又被允诺一种不存在的纯粹乌托邦时,极权主义便开始潜滋暗长。这正是法西斯时代的基本体验:旧秩序不再具有正当性及真实性,新信条和新秩序又尚未建立,极权主义者建构的世界就只能变得毫无理性,如恶魔般邪恶。
此时,经济人的末日已经来临,但欧洲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在上世纪初新旧世界交替的特殊时刻,世界尚未出现建构新秩序,包括传统基督教教会在内的传统精神权威已经开始式微,人们还不能依循、发展出新形式与新机制来组织社会实体,达到新社会建设的目标。
身处两个社会变迁中的人们,自然承受着加倍的痛苦和迷惘。就像丹麦作家克尔恺郭尔所形容的那样,每一个个体感觉自己只不过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孤立原子。一方面,人们已经无法维持旧秩序的内涵,因为它带来令大众无法忍耐的精神混乱;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能立即抛弃旧形式与旧机制,因为这样做同样会造成社会和经济的混乱——那会让人难以忍受。
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迫切需要发现一个能赋予新内涵、传达新理性,同时又能尽量维持旧的外在形式的方法,这不仅是绝望大众的渴慕,也是当时的法西斯主义要实现的任务。
轮到极权主义粉墨登场的时候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任何一场革命之所以荣耀,在于它必定要打破旧外观并创造新形式、新机制及新口号。法西斯主义者在反对一切自由、敌视一切理性原则的精神之下,注定只能等待奇迹发生,才有可能完成其任务——一方面它要维持会唤来恶魔的外在形式(如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提出一种能将同一批恶魔加以驱逐或者将之重新理性化的新内涵。
在这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面前,法西斯主义发现,在他们最深沉的绝望里,理性是不可信的,真理是虚妄的,谎言也变成了真实的,于是,“贵的面包”、“便宜的面包”和“价格不变的面包”,都已经无法令绝望的群众信服,他们只能创造一种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价格的“面包”,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没有人见过且理性证明是虚假的“面包”上,换言之,寄希望于一种奇迹之上。
最后,德鲁克总结说,当年的欧洲大众之所以纷纷投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怀抱,是因为“魔术师之所以是魔术师,是因为他会凌驾于所有的理性惯例之上,颠覆一切逻辑法则,以超自然的手法做出超自然的事情。而当时欧洲大众迫切需要一位魔术师来创造社会奇迹,以平息他们难耐的恐惧。”
德鲁克在他在传记作品《旁观者》中,回望那个27岁的年轻人刚刚登陆美洲大陆那一刻,用了“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来形容这一新旧世界的切换。在文中,他动情地写道:“我想,在社会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年代(二战前实施‘罗斯福新政’最后几年的美国),混合着希望与失望、对知识狂热、不妥协与各种多元化的表现,这种种对于1937年从‘瘫痪’的欧洲登陆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震撼。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战前’(亦即1914年之前)的陈腔滥调是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只有恐怖、集权主义与失落。”
真不知道,如果德鲁克如果能再活一个世纪,见到今天的历史变局他该如何解释:一个被疫情和意识形态弄得七零八落的国际体系、种种全球化和国家保护主义并行的民族主义觉醒、还有那个摇摇欲坠且同样充满陈词滥调的“瘫痪”北美,当然还有多元化渐行渐远的这个世界……。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