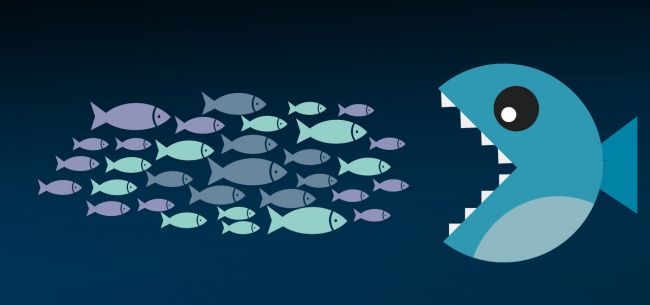
王陈/文 美国彭博社的一项最新研究让公众更忧心忡忡。研究者基于全球公司历年的大数据发现,全球巨无霸科技公司变得更大,中国的科技公司也挤入全球50强的行列。1990年代的时候,有3家科技公司在榜上——IBM、日本电气(NEC)和法国阿尔卡特;而到了2020年,全球50强中有21家是科技公司,全球10强公司中,有8个都是科技公司。
这些巨无霸公司与30年前相比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利润率高了很多,但交的税少了,投资相对少了,创造的就业职位相对也少了很多、创造的多是低端职位。
其实,在2019年年末,美国曾兴起一股对硅谷和数字技术的反思热潮:数字化技术不仅没有制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让社会更平等,反而加剧了族群分裂,让少数人私吞了绝大部分的成果。
对此,《大西洋月刊》在2020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写到,随着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吞噬了网络世界,它们颠覆了传统媒体,赋能鼓吹者,并扩大了美国的政治分歧。这本具有国际声誉的杂志还认为,科技行业的创新只是使得少数人变得很富有,但未能创造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以抵消该国制造业基础的沦陷,也不能帮助解决美国最紧迫的问题: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气候变化、低增长和不平等。
而过去30年,这些大公司的财富积累速度更为惊人,全球50强公司的净收入在全球GDP的占比数据显示,1990年,这50家公司的净收入总值68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0.3%;但到2020年,全球50强公司的净收入达到了8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全球50强公司市值与全球GDP的比较则显示,在1990年代的时候,这些公司市值占全球GDP还不到5%,但2020年已经接近30%,已到达28%。
无论如何,新的权力转移和财富分配正在发生。在未来的一段时期,新兴大公司们将更为深刻地影响全球产业布局、贸易以及竞争格局,也会深刻影响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政策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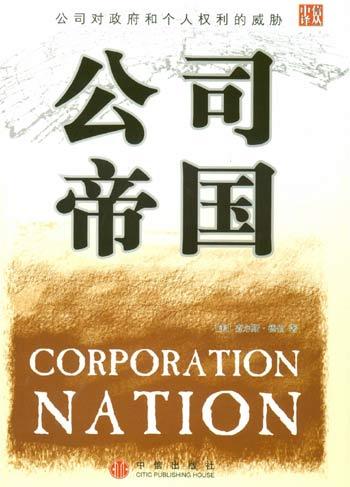
公司帝国
[美]查尔斯・德伯/著
闫正茂/译
中信出版社
2004年1月
公司帝国的历史
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虽然股份制是东印度公司的制度创新,也是西方国家在亚洲海域获得成功的关键,但是,依靠殖民帝国所颁发的特许经营状而横行世界的东印度公司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它们最多是帝国殖民的旗手。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公司会拥有司法权、货币铸造权、保护贸易活动的军事权、乃至非法贸易船只的检举权等。
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起源于18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不但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工业技术的创新高峰,而且也实现了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全新革命。手工工场时代结束,人类发展进入到现代工厂制的时代,公司正式成为主导经济发展和影响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
长期以来,虽然工业革命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为熊彼特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理论提供了诸多典型案例。但是,围绕这场革命的长久影响,也有其他反思性的评价。比如,阿诺德·汤因比就曾评价说,工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的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阿尔文·托夫勒也注意到了这种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的变革,他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说,此前用来耕作的土地上突然立起了无数的烟囱,这些“黑暗的撒旦工厂”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权力体系。同时,君权和旧贵族们逐渐没落,新的精英如企业负责人、官员和媒体大亨开始崛起。批量生产、全民教育和大众传播出现并影响了政治社会。
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公司的组织和规模基本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以电力、铁路网和通信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真正催生了一批制造标准化工业产品的公司,也催生出大型工厂,进而U型组织逐渐取代工厂制,成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原子能、航天技术等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让M型组织横空出世,这得益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相分离为主要特征的M型组织(即事业部制组织)开始在跨国公司中成为主流,并被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D.Chandler,Jr)称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组织与管理创新(详见其《战略与结构》一书)。
于是,公司进一步大型化和跨国化,并与全球化互相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格局被重新塑造,跨国巨头们富可敌国,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际贸易乃至世界政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多领域的科技创新逐渐引发新一轮革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使人类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更加灵活、有机的组织架构变得可行,包括战略联盟、虚拟企业和服务外包等在内的网络型组织纷纷涌现。而居于这些网络核心的和产业链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更多的权力向这些大公司转移。
今天,硅谷巨头们已经不是“富可敌国、灵魂永生的组织”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它们的能量大到可以影响民意、左右美国大选的地步。更令人深刻的是,现代监管制度对他们似乎无能为力。
“信息时代的强盗贵族们”,这本来是美国新闻记者埃莉斯·奥肖内西对微软、威亚康姆和迪斯尼这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公司商业精英们的讥讽,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把这句话作为了自己的著作《公司帝国:公司对政府和个人权利的威胁》里的一个小标题。
帝国反抗者
新世纪初,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德伯在其著作《公司帝国:公司对政府和个人权利的威胁》一书中引用亚伯拉罕·林肯上述言论的时候,全球正义运动(GlobalJusticeMove-ment)的支持者们已经发明了一个新词——公司王国 (corporatocracy或corporocracy),用来形容屈从于组织实业压力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公司王国是富人政治的同义词,这个词语也形象反映出跨国公司施加于现代社会的强大控制力。
众多大型跨国公司从二战后至今逐步控制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关键的生产和消费资料部门、中高端消费市场,使各个国家的经济、金融、贸易、政治决策越来越多地由跨国公司的全球需要决定,国家权力的一部分逐渐让渡于跨国公司。
查尔斯·德伯注意到,从本质上讲,企业的魔力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功掩护下,企业的力量在数十年间不断地增长着。在《公司帝国》一书中,查尔斯·德伯试图通过对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进行深刻剖析,让人们警惕大公司的特权。他认为,跨国公司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与个别国家的贸易往来,或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微笑着让一些政府债台高筑。
长久以来,美国的大公司们似乎一直面临公共关系危机,不在乎公众利益的印象一直在流行文化中被强化,其实这不奇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以及增加社会福祉的同时,它的腐败、贪婪、对环境的破坏和对政策的左右总是相伴而生。
在美国国内,针对大公司的抗议也屡屡发生。比如早期的“劳动骑士团”,轰轰烈烈的运动催生了8小时工作制,终结了童工雇佣,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些成就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商业世界。而这一过程中,流血冲突也层出不穷。
当然,美国早期的工业巨头们虽然可以镇压工人罢工,但随后发生的反垄断运动却“给美国的商业和公众生活留下了长久的印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枪口对准了洛克菲勒等工业垄断巨头,继任者塔夫脱分拆了美国烟草托拉斯。
无疑,反对大公司垄断不但维护了自由竞争原则,也为政府管制商业奠定了基础,西方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市场机制有时也会失灵,政府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出手校正那双“看不见的手”。
尽管这种博弈在持续,公司的巨型化却始终是一个主要趋势。在二战后,公司巨型化更成为美国商业世界的主要特征。
在新的时代,查尔斯·德伯等人充当了反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先锋。他尖锐地批评说:大型跨国公司已经侵占了普通公民和政府的权力,对社会的民主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当然并非新发现,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一种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会削弱权力体系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人们的家庭生活、企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世界权力本身的结构。
托夫勒当时说:“我们正站在历史上最深刻的权力大转移的边缘。”他还断言,未来几十年内,原始的权力在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层面将发生变化。现在回头看,这位预测学大师的预言非常准确,今天,这些趋势变得更为明显,速度更快。托夫勒活到了2016年,部分见证了新兴科技巨头们崛起和影响世界的鲜活史。
在托夫勒的警告之后,查尔斯·德伯试图寻找一种“有建设性的应对途径和出路”,比如发动和组织包括雇员、消费者、小企业、社区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从内部和外部对巨型跨国公司进行制约,从而有效地遏制那些巨型公司对社会生活的操控。
监管难题
最近这些年,美国参众两院举行过多次针对科技巨头们的听证会,试图打击他们的垄断行为,公众也经常看到科技巨头们在电视镜头下宣誓,承诺要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很多时候,在大公司监管的问题上,政府都很无奈。“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仅仅成功攻击了价格卡特尔机制,却并未从总体上限制巨头们的市场支配地位,这或许是资本的天然属性使然。查尔斯·德伯说,在所有的领域中,唯一不变的趋势就是资本的聚集,“无论是通过业务拓展、收购或者合并,这种资本的聚集推动着企业极权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美国,今天针对科技巨头们的监管变得更加复杂和难行,除了党派分歧的原因,还有立法者和监管者的认识跟不上科技发展速度,导致他们面对大数据、区块链、加密货币以及NFT时一头雾水,无所适从。
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TedStevens)因为将“互联网”错误地描述为“一系列的管子”(aseriesoftubes),而遭到众多业内人士的嘲笑——监管者居然如此外行。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Facebook创建14年后的2018年4月。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首次出现在国会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议员们指责Facebook商业模式贪婪,并把用户数据与CambridgeAnalytica公司共享,CambridgeAnalytica是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常利用社交媒体用户数据来左右大选投票。2013年时,Facebook的用户数量已经突破10亿。
非常有意思的是,随着听证会的开展,公众的愤怒情绪逐渐从Facebook转向了提问的议员们。因为在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表现出了对科技知识的不专业性,他们很多人并不清楚Facebook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对其广告业务模式也感到困惑。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在如何保护消费者和鼓励企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数十项旨在加强隐私保护、促进竞争和消除错误信息的法案由此停滞不前。所以从整体上看,过去10多年里,美国监管部门对于科技巨头们的无边界式的扩张仍旧力不从心、无可奈何。
造成这种尴尬结果的不仅仅是政治分歧。长久以来,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始终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才是推动美国“镀金时代”长盛不衰的支柱,私人企业的神圣独立性不可动摇,对于企业扩张和市场竞争,政府不应该伸手。
1970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商界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其自身的利润水平。对此,查尔斯·德伯认为,弗里德曼预言了美国“契约派”的崛起,并预示了一种新的美国神话的诞生,即企业是一种私人性质的“契约关系”,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当归类于个体公民的自身事务。此后,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经济学家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力军,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反对市场监管,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商业政策。
在大公司的发展史上,不断壮大并与监管层博弈,同样也是一个脉络清晰的过程。随着他们变得更大、更多元,特别是二战后,其游说能力也变得更加强大。本杰明·沃特豪斯注意到,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公司都设有“华盛顿代表”,即在华盛顿居住的永久性雇员,代表公司公开游说政府和国会,以影响政策走向。
推而广之,这种博弈并非仅限于美国。公司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成为商业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政府、公司、公众三者之间的博弈,也将是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