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扬/文 清代衙门里的爪牙们,在清代精英表达中常常是以“无赖”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是一群只为谋取私利的恶棍、二流子,是地方秩序的扰乱者,更有甚者,这些“爪牙”被认定为是腐蚀清代帝国统治根基的元凶。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清代行政领域运行的实际情况,总是与理想追求存在张力。清代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在清中前期皆呈现爆发式增长,资本主义萌芽导致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这些皆表明,清代地方社会的治理难度在不断增加,州县官员在正式制度中难以获得提高其治理积极性的经济刺激。同时,因国家财政经费掣肘,州县仅知县享有薪资,其他诸如书吏、差役等协助政府工作人员也明显不足。
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在研究清代民法表达与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清代官方话语的表达结构,是一种道德理想与道德化反理想的对应关系。这种背离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协调并存。清代地方档案记录的行政司法运作实际,在黄宗智看来,总是呈现出背离又统一的状况。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白德瑞(Bradly W. Reed)2000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Talons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2021年被译成中文,在这本书中,清代巴县的基层治理逻辑得以清晰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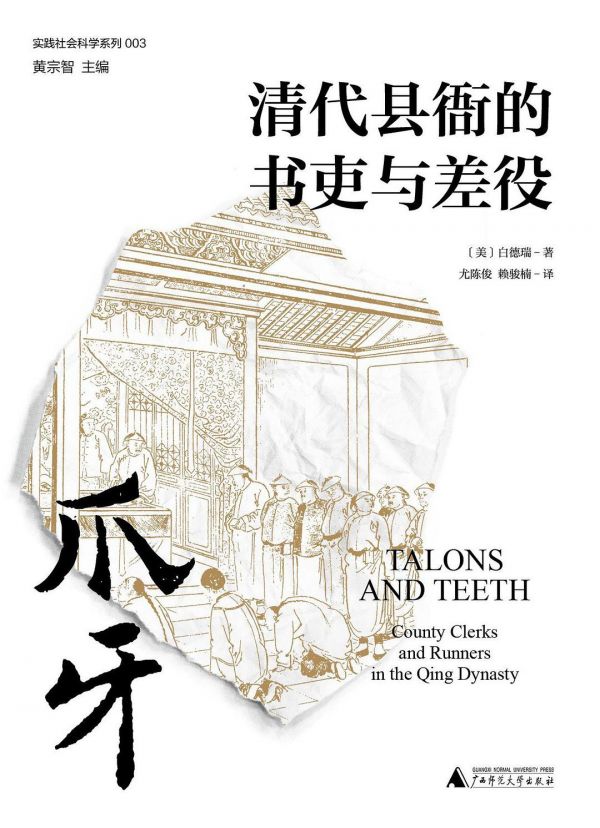
爪牙: 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美]白德瑞 /著
尤陈俊 赖骏楠 /译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一
《爪牙》第一章提出本书讨论的问题。这里关注的并非应然性,而是实然性的实践问题,是清代地方行政事务实际上如何运作的问题。不仅如此,白德瑞通过对学术梳理,阐明本书使用的理论资源、研究进路及其使用材料——巴县档案的社会历史背景。这里要强调的是,本书作者提出关于“非法”概念的区分问题,即严格意义的非法与非正式规范意义下的“非法”。这两种“非法”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晰,有时模糊不清,甚至是故意为之。只有理解不同维度下的“非法”概念属性,才能对本书讨论的“腐败”问题,形成符合清代地方行政运作实际的认识。因此,两种不同维度认知的“非法”与“腐败”是理解本书作者表达意图的关键。
《爪牙》第二章至第六章是以作为部分个体的行动者与作为整体的诉讼案费收取两个视角,对清代行政实际运作的状况进行审视,以此论证“非正式制度在清代地方实际运作中的不可或缺性”与“非正式制度的正当性与腐败作为话语资源”问题。《爪牙》第七章从巴县档案记录县衙书吏与差役的具体案例事实中抽离出来,回归本书开篇关注的问题:清代地方行政实际运作的真实场景。黄宗智提出道德理想与道德化反理想的巴县实践,在白德瑞对清代巴县县衙书吏与差役的研究中得到注解。
本书将巴县衙门的实践作为游离在正式法律制度外的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之体现进行检视,发现这种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中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也有各类非正式制度,包括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各种资源与利益,这种资源与利益作为各方争夺的话语,清代衙门只是作为话语的资源与利益进行交换的空间场域。本书想要讨论的,依旧是非正式制度的正当性存在与“腐败”的合理性问题,其中因地方行政需要产生的非正式惯例性费用与正式制度存在固有缺陷导致形成的“腐败”以维系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应是清代地方行政司法实践的实际样态。
二
长期以来,绝大部分官方文献与清代社会治理的研究著述都会描绘如下场景:书吏与差役利用各种借口骚扰管辖之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一群贪腐成性、只顾个人私利的群体。这些“非法”的爪牙们在清代官方精英群体的话语表达中是一群“无赖”,是只为谋取私利的恶棍、二流子与地方秩序的扰乱者,更有甚者将这些“爪牙”认定是腐蚀清代帝国统治根基的元凶。在这种认识的引导下,几乎所有的官方文献,都会把书吏和差役记录为上下其手、利欲熏心之人,刻板模式化的形象摹写,对当今学者看来清代地方治理问题影响颇深。
但是,这些吏役群体是否就是描述的那样?若答案是否定的,那又是一套怎样的话语模式在发挥建构作用?这种话语资源的运用又是为何实现怎样的动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丰富的案例故事,提出了同上述官方展现的话语不同的另一幅图景。
上述针对“爪牙”刻板形象的话语表达,背后是清代官方已经无法通过国家制度资源有效应对社会实际变化,转而利用“污名化”的话语资源以弥补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的关键是规范性的政治价值观,更多表现出儒家意识形态下的话语模式。
因此,当那些为满足生存需要的书吏与差役,通过利用知县赋予某种权力获得金钱、收取惯例性费用而施行的行为,在诉讼儒家的话语中,并不符合子民“无讼”的社会理想,是清代精英群体不愿目睹的境况。因此,通过对书差群体进行某种程度的“污名化”,是维持道德话语表现的必然结果。
清代地方书吏与差役人员数量的定额化要求,以及发展并不匹配或同步的人口增长、地域扩展的现状,导致清代国家财政来源已不能满足地方行政的实际需求,这些远超出定额要求的书吏,是维持清代地方行政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础。
这类并不“在编”的吏役群体为了讨生活,在承办民间讼案的过程中收取惯例性费用的做法,也成为清代地方社会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不仅满足了吏役个人生存所需的各种酬劳,对清代巴县地区的行政运转也提供了必要经费支持。
具体而论,占大多数的非经制吏役在清代县衙的存在本身,即已构成“非法”。换言之,这种“非法”的不稳定性在官方表达中,是县衙的行动者不受儒家意识形态与规范性政治价值的约束,这些群体的行为常处在国家正式制度的直接控制以外;若是要寻求这些“非正式”群体长期稳定存在的原因,就要从清代地方行政实践的视角开始观察。
在本书中通过两个层面进行了解析。第一,当清代国家正式制度已无法满足县衙日常行政运作的实际需求时,已经离不开这些非经制吏役。第二,作为清代地方官员的政绩与升迁要求,维持地方治安与征收赋税是考核的主要标准。因此,清代知县与这些“非法”的爪牙之间存在一种妥协,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的正向结果。
因此,这种行政实践模式,是以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达为标准,使得衙门内外的人可以用来界定自身行为,并以此话语来捍卫自身生存利益。
三
清代地方行政实践中产生的“惯例性费用”,即通常所称之“陋规”或“规费”,是理解清代非正式制度“正当性”的极佳例证。在国家律例构建的国家正式制度外,地方社会存在相应的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多是依循惯例或“陋规”存在。这些基于“非正式”体系形成的县衙内部的各行规矩,规范着书差的日常工作、利益分配与内部秩序,塑造了清代地方行政司法正常运转的场景。
倘若将这种惯例性费用作为一种资源,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势必会引起竞争。争端发生时,有三个维度的解决途径:一,纠纷双方自行协商、二,提交衙神祠的议事会议、三,上告知县定夺。这种非正式的规则,维持着知县与吏役之间的和谐共存。但是,这类纠纷上告至知县,知县已然知晓这种非正式的惯例性程序的存在,对纠纷处理本身即已构成知县对这种“惯例性程序”的默示。这种非正式程序的强制力,同时也为县衙内部的这种做法赋予正当性的认可。
最后,白德瑞在本书希望做到的是厘清并确立一种标准,即认为讼费高不可攀的讼费标准与界定腐败与滥权的标准。讼费数额多少对民众而言才是“高不可攀”,究竟地方吏役收取陋规费用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在非正式制度中被认定为“腐败”?无论是对案费收取数额标准的确立,还是三费局的设立,都是努力让民众进入县衙打官司的经济成本被标准化、规范化和可预期化。
随着地方档案的不断开放以及数位库的不断开发,学界相关主题研究的细化不程度断加深。举例而言,那些经常与清代地方衙门打交道的讼师也曾经历过如本书所描述的那种被“污名化”的实践。这种话语模式的运用不仅是官方,乃至讼师本人、参与诉讼的当事人都会在衙门这个特殊的场域,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标,展开话语资源的争夺。
本书英文版问世二十年后译出的必要性贡献,诚如译文后记所言,虽然相关主题在史料利用方面已有不少拓展与丰富,但依旧是一本具有“重要理论含义”、具有“研究方法启发性”的经验研究著作。这种学术贡献的价值地位使得本书的受众阅读群体已不限于历史学界,法律史学界,而是扩展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能从中获取关于清代中国行政司法历史实践的信息。本文也并未想过将衙门里的书吏与差役作为重要的对象进行观察,更多是将这些群体作为一种符号进行看待。清代地方司法行政实践中的参与者,有民众百姓、知县、书吏、差役,还有讼师、歇家,甚至还包括牙行。这些若是统归视为一种在清代衙门场域运作的符号,清代地方行政运作的真实也许就会跃然于纸上。
最后还可以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本书集中使用的地方司法档案。法国历史学者阿莱特·法尔热认为,司法档案所呈现的是一个被分割的世界。人们知道,大部分审讯记录通常都是一些不完整或者不准确的回答、只言片语、大多数是毫无线索可言的生活碎片。这在利用各类(包括中央与地方档案)档案以解决实际问题时,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地方。诚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档案资料,作为人类书写的历史,背后永远会有一套体现某种价值判断的话语模式作为支撑。作为方法的法律社会史,不应拘泥于判断这种话语是否真实的问题,而是应花费更多精力去思考不同类型话语模式的生成机制问题,这应是未来法律社会史研究可为的重要契机。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