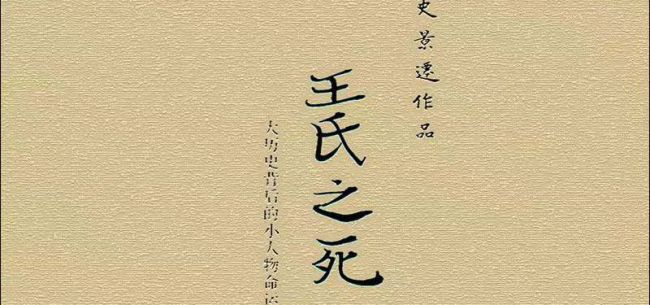
庄秋水/文
一
2005年冬,我逛到香港铜锣湾一家狭小的二楼书店,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了《妇人王氏之死》,读完译者序和作者前言,就决定买下来。261页的书,定价260元(港币),打折后也要87元。那时内地同样厚薄的书,只要十几块。后来我才知道,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一年,他还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但在翻开那本书的时刻,我确实对作者一无所知,完全是被这个奇妙的故事迷住了。
伴随着首次到香港的新奇感,我很快读完了这本书。
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住一份鲜活的颜色。
故事的结尾犹如一部电影画面的定格,深深拓印在我的脑子里。穿着软底红棉睡鞋的妇人王氏,我并不陌生。哪怕三百多年过去了,北方的乡下,一个女性所面临的根本性的境遇,似乎改变也极小。
《王氏之死》是史景迁最知名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部。他曾经说过自己写这部作品的缘由。在1960年代末,他正在写关于康熙的著作。17世纪下半叶,康熙作为中国皇帝,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很想知道,相对于那位高居龙椅之上的万民之主,那些生活在底层、在贫困和灾难面前不堪一击的普通农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景迁在英国剑桥图书馆中看到复印本《郯城县志》。在翻阅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女性故事,她被无情杀害,但没有更多的细节。最终,他依靠一部县志、一份官僚回忆录和作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构建了一个充斥着灾难、盗匪、刑案的底层社会,即便如此,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民众,也不乏自己卑微的梦想。
多年来,人们执着于评判史景迁如何在历史与文学的边界移动。这自然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不过在《王氏之死》这个案例中,最终吸引我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变换的视角。在后来阅读他的其他作品时,这也是他显著的特色。
他想知道同一时代,一位皇帝和一个乡下妇女的内心,如何与他们的生活互相塑造;他也关心在皇权游戏里,原本处于对立立场的两方,怎样“合谋”创造一段历史。在他的写作中,最核心的问题永远是人如何生存,他视之为“历史的本质”。故而他的问题意识指向的是立体化的过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具挑战性的是如何保持故事的平衡性”。20世纪后半叶以来盛行的主义、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各种文化批判都消隐不见。
比如他在《王氏之死》里使用了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的作品。蒲的故事里,是流浪汉、街头小贩、变戏法的、学道者这些在社会上处于底层的民众,他为他们编织奇异的梦幻经历。史景迁认为,蒲松龄是那个时代一些中国人的声音,他的小说里也充斥着暴力,他把这些嵌入到自己的故事里,使用近似蒙太奇的手法,为缺乏细节的的谋杀故事,增添了一个重要的内部视角。王氏女由此获得了“金身”,从一位沉默的自然的人,成为了被记住的“历史的人”。
史景迁相信他的故事自有其力量:“四十年后,人们仍在阅读我的书,这不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时兴,而是因为我触碰了这些故事的本质。”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必须承认,他建立了一种历史写作的新范式。那就是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生命存在感受,诸如好奇、焦虑、困惑,喜悦等,刻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再以繁密的细节编织精巧的场景,辅之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在遗存下来的历史材料之间织成故事,偶尔有一些跳跃,两端也是史实的基柱;故事的前景和背景,裁剪得当,都融化于叙述之中;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而非观点,存在于脚注里,或者干脆隐藏不见。毕竟,说《王氏之死》是一部女性主义历史著作,也未尝不可,但他并没有在书中提到一句当时正盛行的观念。
二
史景迁的英国前辈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800-1859)在《论历史》里说:“近代最好的历史学家都偏离了真理,不是由于想象的诱惑,而是由于理智的诱惑。”他批评历史学家们热衷于归纳总结历史规律,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以适应理论。出于这种理智的狂热,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们,豪情万丈,要穷尽历史材料,总结出类似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一类的历史公理。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讽刺:坚持寻找目的把历史学家变成了先知。这真是对科学史学的嘲笑。
也因此,人在历史中变得不再重要。时代是有意义的单位,人只是被动的浮萍般的存在。历史学家王汎森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整个历史像一部往前驶的火车,驾驶员、乘客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车厢、铁轨。我由此想到,那么沿着所谓历史规律运行的火车里的人,岂非就成了“火车里的囚徒”?单个的人,当然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复数的人,成了量化性的历史分析里的数据。
19世纪兰克学派认为,只要掌握了完全的史料,就可以客观而真实地重建过去,可以有科学般的精准。早于兰克的麦考莱早就批评此种想法纯属天方夜谭:因为绝对的真实,必须记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且不说历史记录永远只是一角,就是真的全部记录下来,一则浩瀚无垠,一则每一个记录者已经带着自己文化背景和意识偏见,那么记录已不绝对客观。如此说来,客观永远只是个程度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史景迁似乎接续的是麦考莱以来的叙事传统。他接受的是系统的英式教育,小时候上的是寄宿学校,13岁进入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温彻斯特学院,随后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攻英国史。他的校友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认为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他曾说过一段话,可以直接用来描述史景迁的历史写作:
就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来说,它乃是“一个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就像血肉围绕骨骼一样,应该贯穿许多不同的事物——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于社会的和文化的运动的研究,对于可能的原因和结果的探讨,以及历史家能够用以说明过去的任何东西。但是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史景迁在耶鲁大学深造期间,兴趣才转向中国历史。他跟随中国专家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1917-1970)研究清朝历史。芮玛丽又把他推荐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史学专家房兆楹。房以中国式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带他进入规范的学术世界,并送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中文名字——史景迁。“史”,取自他的姓氏首字母,又是他当行本色,而这个名字的寓意更是意味深长:向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致敬,成为同样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正是司马迁建立了中国历史写作的范式:以纪传体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为中心。”当然,由此衍生的问题,是泛道德化趋势,把历史的盛衰归因于人的言行和道德品质。晚清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反感传统历史,称之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关注点只在政治制度和朝代兴替。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痛斥此种历史书写传统。从此,人的比重在下降,社会分量在上升,到1920年代,傅斯年等人提出“新史学”,要建立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的科学史学。到后来的唯物史学,则相信历史规律决定论,人不过是时代的产物,单个的人,是犹如牵线木偶般的存在。
我认为,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正是中国传统纪传和英国叙事的一个结合体。他重新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人,在结构中的人,他不是孤立无援的存在,也非决定乾坤的神,也不是被抽掉血肉的名词,是生活在社会文化中的人。由此,他的写作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特质,是一种方法论。用史景迁自己的话说:“我们可以用任何现存的方法来讲故事。没有任何理由能表明你不能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治人物的动机。你可以假设这个政治人物受到某种理论和事件的影响,或者他在年轻时经历了某些重要事件,比如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被杀害。这恰恰正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也是数千年来人生活的方式。”
三
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这样才能在非线性因果的历史材料之间建立联系,也才能在叙述中细致动人。但他必须掌控自己的想象,将其限制在发现的材料上。史景迁写张岱的那本书中,灯笼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而且灵感来源于张岱的回忆。《陶庵梦忆》中,张岱说,他小时候被家里的仆人扛在肩膀上看灯笼;在他的记忆中,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灯笼的光芒。史景迁被诟病的地方,在于他有时会不受自己的控制,任凭想象力狼奔,构筑另一时空下的场景。这也不难理解,一个人掌握了一项精妙的技能,要忍住不用,绝对是对人性的考验。
我认为,没有比《王氏之死》这部奇妙的作品更能体现出史景迁在历史写作上的天赋,那是一种纯粹理性分析不能企及的高度。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直觉力”或者“悟性”。当他看着平凡无奇的材料时,脑子里已经有了画面,心灵上也与过去有了连接,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元宇宙”。他描述自己寻找故事的经验:“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隐藏在阅读的历史中的故事,就好像是那些历史都在等待着被发掘出来的感觉。”在《王氏之死》前言中,他使用的词是“召唤”,就好像用魔法召唤神龙。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是《王氏之死》前言的最后一段。那段话里,他带着一丝怅惘,描绘了发现这个故事带给他心灵上的撞击。
我感受到了这种撞击。在读过《王氏之死》一年后,我在一家报纸的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的,应该属于较早在公众媒体上推荐他著作的文章之一。我说他“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正是被他对历史的这种连接感深深打动。进入角色内部的写作,让这个情境自己生出对问题要害的理解和表达,用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环境。我认为,这正是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写作为何能在海外风靡的深层原因。毕竟他笔下的大部分历史人物,对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读者而言,可以说毫无意义。
在另一位历史学家卢汉超和他的访谈中,史景迁无比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目标:
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
他很清醒地看待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与冲击力,反而中文世界关于他的许多争论显得意义甚小。
魏斐德认为史景迁作品中最精彩的是写洪秀全一书的最后一幕:兵营内外,忙碌的西方商船以及凝视夜光与聆听信号的士兵,作者将自己的视角融入了条约口岸和战场的广角镜头之中,那是一种介于虚构和事实之间的多重性张力。在我眼中,最精彩之处,除了《王氏之死》的结尾,是几百年后,写《皇帝与秀才》的作者回到历史现场,最真切地抵达曾经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我觉得,那是理解力的源头,历史的本质由此浮现。
(作者为作家、制作人)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