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濯/文
乾隆吃好,嘉庆不饱:如何分好一块无法变大的蛋糕?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农历三月初八,本是皇储不二之选但患骨结核多月的皇五子永琪离世,谥号和他皇父三十三年后一样被定为“纯”。就在不久前,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英格兰出生,还很可能在满月时被前来祝贺的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亲吻祝福过。
在《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中,按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岩井茂树教授的估测,这一年清廷财政收支大致平衡。财政岁入约为4547万两白银,其中“地丁”“耗羡”“漕米”等三项组成的土地税占了法定正税的七成以上,余下的大项包括盐税(574万两)、关税(540万两)等稳定财源,而附加税、追加税等正额以外的财政“陋规”“规费”总额难以把握,“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尚不在内”(《清史稿·食货志》)。
在3460万两的正额支出中,满汉兵饷1700余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余下是文职和武职官员的养廉银各347万两和80万两,王公百官俸和外藩王公约100万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用银56万两,等等,“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尚不在其中”。总的来说,当年正额收支相抵后结余超过1000万两,而这也是清前中期财政收支的常态。
清朝法定正额部分的财政收入每一项都有“定额”的限制,灵活性极小。尤其是自入关后顺治朝的“蠲免除正额外一切加派”、康熙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政策已成为强化本朝合法性的“祖宗之法”。但由于对课税土地的严格把关和关税收入的增多,财政收入在在清初的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始终呈现增长趋势。如顺治九年(1653年)收入2438万两,结余638万两,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收入4359万两,结余1182万两,这也大致是清朝岁入和结余的最高值。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世纪前期的嘉庆、道光年间,财政岁入持续低于1791年最高值4359万两约300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岁入4013万两,但结余只有479万两;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岁入和结余更是跌到3701万两和57万两。
岩井茂树认为,虽然自己匡算的岁出是加总奏销册上的国库支出项目,而不是全国财政支出的实际总和,但两者反映的进入19世纪后的事实并不相悖:“收入减少,支出却增大”。再考虑到清代中期的物价上涨现象,“从18世纪前半期开始大约100年间,银的购买力贬值了2/3左右”,这意味着法定的、正规的、额度内的国家财政规模实际上大幅萎缩。而国库支付给官僚的俸给、津贴、兵晌、物资采购经费、马匹饲养费、衙役补贴等均采用固定价格,完全不根据物价变化相应调整。同一时期,人口增长超过了两倍,即使官僚和兵员数量的正规扩编幅度极小,但从人口比例来推算的业务增加,必然导致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吏差役数量和经费需求相应增加。
可以说,物价的长期大幅上涨和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各种摩擦,并倒逼正额外财政的扩大,以附加性、追加性课税来弥补国家财政的实质性缩小,“进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担负起了财政的自然膨胀的功效”。相应地,岩井茂树发现,州县的财政支出——“存留银”遭到大幅削减,“摊捐”和“摊款”却越来越多,地方财政的吃紧引起了附加性、追加性课税增多,带来社会各阶层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均衡,还衍生出“馈送”“规礼”等官僚间的私人送礼的俗规。岩井茂树断言,缺乏弹性的财政体制是造成吏治废弛的深层原因,“其结果是激化了社会利害冲突,扩大了不安定因素,放松了吏治管理,最终破坏了王朝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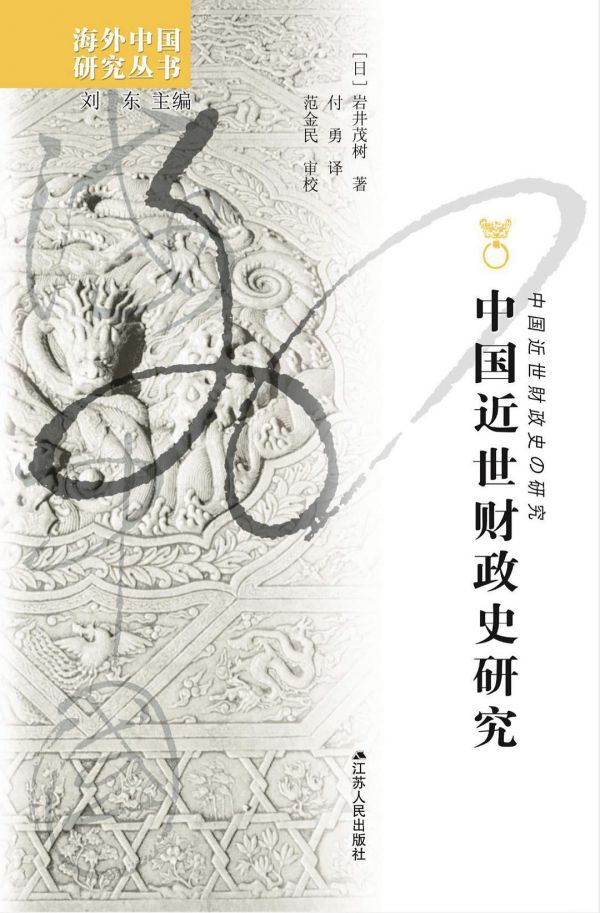
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作者:[日]岩井茂树著
译者:付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1
非正式、不完全、潜规则与制度外:“原额主义”与治乱循环
在帝国堂皇的财政体系中,存在两种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事实制度和收支逻辑:法定的国家财政(正额财政),以及法定之外“地方上巧立名目的公开或私下筹得的不明收入”(正额外财政)。正规的国家财政分配给基层机构的经费,往往不足以支付地方各项开支,不得不由附加性、追加性课税来解决,“‘中饱’‘规礼’陋规‘等形式的私下捐赠,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财源”。如果加上这部分法定的国家财政之外的收入,“那么支撑整个国家机构的财政循环规模,很可能远远地超出朝廷(中央政府)所掌控的财政的数倍”。
明代一条鞭法将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归入正额之内,之后编订的《赋役全书》甚至对地方最下级官府的胥吏衙役的“工食银”(即工资)、购买纸张蜡烛的经费等都有详细规定,目的在于固定和削减源自各种徭役的地方经费,“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人”,但是到了16世纪末,随着军事负担的加重,财政极度紧张,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再一次扩大。
后来,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清朝正额财政制度,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酌拨制度崩溃瓦解,以京饷与协饷为特征的摊派制逐渐呈现分权化倾向。“在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正额外财政与正额财政的关系若即若离,时而融合时而又有对抗”,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到了19世纪后半期,外销经费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核心和中央地方矛盾的主要议题之一,但外销款项在当时仍未成为正式的、具有“名分”的财政制度,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等“无名”(无正当名目的、非法性的)的形式,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可以说,虽然明清两代分别实行现物财政和银钱财政,但从财政结构和原则上说存在着共同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柔软的非正额部分的互补性”。甚至民国时期中央财政被架空、厘金制被废除、附加税成为县财政原资、苛捐杂税泛滥等等问题,也可以视为明清以来旧财政体系的延续。
“明代的徭役问题,清代的差徭、浮收问题以及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兵差问题……别无二致,归根到底是由财政结构引起的。”随着开支不断增加、财政日渐窘迫,各种曾被归入正额之内的非正式、不完全、制度外和潜规则下的附加性负担和追加性课税,往往会以新的名目和形式借尸还魂,再次扩大,概莫能外。
那么,为何国家财政体系和收支制度存在如此的一体两面?岩井茂树为此引入了“原额主义”的概念,来描摹与经济扩大不相对应的僵化的正额收入、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机构活动的扩大而增大的财政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为了弥补这种矛盾而派生出的正额外财政体系的特性。
岩井茂树认为,原额主义是在以两税法为主轴的财政体系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财政原则,并成为中国古代专制国家的财政和政治问题的特征之一。这种正额财政与正额外财政的复合式结构,并不意味着租税收入和财政支出的一成不变,而是经常性财政收支被尽可能地控制在固定的范围之内,这导致靠正规财政维持的政府活动受限,正规财政之外非法但灵活的财政措施却得以施展,正额外财政的滋长最终也损害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
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耗羡提解”使得附加税“准正额化”,抑或是国民政府对厘金的废除,集权管理、定额化预算化的政策与“财政结构的动态性格”之间的张力,使“地方经费的困窘”成为一种周期性反复出现的现象和“恪守核心部分的原额主义的必然结果”,并引起了附加性、追加性课税的增大,引起了与税役负担相关联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岩井茂树由此慨叹,历朝历代不断地重复着“建立制度——兴盛(墨守祖法)——矛盾显露(改革)——动乱出现——王朝覆亡”的循环,“在历史舞台背后的社会经济的因果关系中,原额主义的财政体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财政、仁政与善政:官僚体制的事与愿违
岩井茂树将原额主义的形成归因于两点:一是古代中国人严重缺乏对人口增长的正确认识,仅仅关注其会带来的物资紧张、物价上涨等负面结果,“却认识不到它背后带来的社会经济增长、纳税能力的增大”,因此将维持原额视为“善政”,将增大原额视为“恶政”;二是原额主义能够在当时的行政管理技术水平下满足财政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管理要求,以便中央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即“额”),从“考成”“奏销”“报销”等角度监督和检查税收的完成情况。
但岩井茂树发现,这种主观上的“善政”和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却事与愿违地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趋势下,越是想维护‘善政’,‘恶政’(即正额外财政)就越是横行;越是想坚持集权管理,集权体制下的正规财政就越发萎缩,就不得不默许正额外财政的泛滥”。在岩井茂树看来,“恶政”横行必然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带来国家机构内部的法制力衰弱,“这两者一定是相伴而生、同步发展,共同摧毁着专制国家的基础”。清代在太平天国以后呈现的财政极端分权化(中央政府和户部的财政管理失控)和吏治颓废,便是绝佳例证。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从长远来看,生产的增长和供养能力的增长难以与人口增长潜力保持同步,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鸿沟。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他也曾强调的,“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人口压力可以反过来刺激生产增长。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会束缚社会生产力和人口供养极限的提升?
人口在传统农业经济体系中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康乾盛世”带来了空前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和巨大的人口压力。然而,在封闭自足的体制和死守传统的祖法下,小农经济难以自然生发出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模式,只能让裱糊匠剜肉补疮,疲于应对人地矛盾激化、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危机加剧、生存环境恶化等诸多危机和隐患。善政和仁政,似乎愈发艰难和遥远。
宋濂等人在《元史》中继承和总结了中国古代“量入为出”的平衡财政政策作为治国之要,提出“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岩井茂树指出,“均”“平”“公”等理念对国家而言,也许是很有局限性、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的愿景,但是其背后“极大程度上是由官僚的良知、官场上的规则,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习惯、传统秩序等在左右着”,这是近代前期专制国家的类型和中国传统国家坚固不变的结构。
遗憾的是,正额外财政以及附加性、追加性的征税,在法律依据上是暖昧的。国家“力图法制化、权威化的努力”,在财政上原额主义的矛盾面前不得不后退。官僚身份的有无和社会势力的强弱,在实际的租税征收和负担分配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半公半私性质的钱财馈送“使得私人利益和人际关系侵蚀着行政上的‘公’与‘法’的行为原则”,并直接带来官僚机构制衡机制的失灵和内部监督的缺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古代中国何时形成较为完善的地方财政,学者之间是有争议的。梁方仲、周伯棣、宫泽知之等人从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角度出发、或者借用现代地方财政的概念和标准,认为除了军阀割据等极个别时期以外,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独立的地方财政存在。岩井茂树的观点事实上也与此类似,即认为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始终不具备独立自主支配地方财赋的权力,对地方经费施行制度化管理,会留下地方经费随时为中央掌控的风险。
“研究财政体系,是研究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性和结构的最好领域”。财政与社会诸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研究财政史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无论完善的古代地方财政是否存在,高度集权的制度设计与地方政府的额外加征、经费授受被默许,这二者长期共存形成的自发秩序,在其他论者的著述中早有提及。王业键强调法定税收与法外税费的分野,周雪光提出的“不完全财政”概念,吴思的“潜规则”话语体系,曾小萍将雍正朝的“耗羡归公”评价为“中华帝国最后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倪玉平认为“即便没有发生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代的财政体制也到了必须做全新调整的时候”,周健援引了梁启超的“包征包解”来概括清代各级财政关系兼有“集中”和“分散”的管理模式,刘增合分析各种“行走在制度内外”的财政供饷模式嬗递,和文凯强调在定额基础上展开的财政运作功能失调,在此不再赘述。
相比之下,我更为认同周雪光的观点,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其实只是帝国大背景下“放权——收权——放权”周期性波动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空间跨度大、文化多元、发展不平衡等帝国的特有规模和制度路径依赖,催生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和困难,以及“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的共生并存、互为依赖、微妙平衡。
奥地利社会学家鲁道夫·戈德沙伊德曾说过:“预算是一个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剥去所有意识形态宣扬后的骨架。”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财政和预算外资源的自利追逐,以及基层为国家治理注入的种种富有多样性、地方性、灵活性的努力,数百年上千年来都在野蛮而倔强地生长。日光之下,域内海外,并无新事。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