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木/文 直到朋友们整理胡晶晶遗物才发现,原来她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的药。
在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中,朋友的疑惑也是许多观众的疑惑,为什么平日里看着乐乐呵呵且十分开朗的胡晶晶,会患上抑郁症?
黑狗
前些年,曾经在《死亡诗社》中扮演老师的罗宾·威廉姆斯身患抑郁症(他于2014年自杀身亡);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金·凯瑞也曾在接受采访时坦露自己身患抑郁症……而无论是威廉姆斯还是金·凯瑞,他们的主要工作都是喜剧。为什么?看起来快乐活泼的人会患上抑郁症。
这一疑惑,反映了关于抑郁症的普遍迷思,即抑郁症在许多人的理解中就是暂时心情不好,过了这一阶段心情好些了,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抑郁症并未被普罗大众接受为一种疾病,当许多人得知它属于精神障碍时,又会随之产生新的污名。正是这一两难的状况,导致许多患上抑郁症的人,不愿意对身边人透露自己的状况,就如胡晶晶一样,还会装出一副开心活泼的模样,以掩盖自己被抑郁折磨的痛苦。
根据临床观察,抑郁症的典型表现之一,便是持久的心情低落和兴趣减退。因此它并不像其他疾病,有着明显的生理或精神“反常”表现。遭受抑郁困扰多年的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把抑郁症比喻成一只和自己形影不离的“黑狗”。随着人们对抑郁症了解的增加,我们才发现这只黑狗已经入侵了许多人的生活。
根据权威医学杂志《自然》收集的数据,全球有3.5亿多抑郁症患者,每天有3000多人因为重度抑郁症而自杀,这种病症已经成为全球疾病负担之首;可是,由于社会大众对抑郁症缺乏认知,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非常低,大约只有25%的人能获得有效治疗……更多的患者,会独自待在那座黑狗相伴的岛上,其中许多人选择自杀来摆脱这一漫无边际的痛苦。
抑郁症在现代社会的频发,一方面与医学和精神病学对它的诊断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抑郁症是一种与外部因素联系最密切的疾病。在英国两位精神病学教授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合作的《抑郁症》中,便梳理了西方历史中对抑郁症的认知和正名过程。
在希波克拉底时代,他认为这症状是“黑胆汁”,即体液失衡所致;而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过类似的体液观点;直到托马斯·威利斯才第一次以化学理论来解释这种情绪低落和忧郁。在这些医生寻找着抑郁症的生理性病因同时,许多研究者也发现这一疾病和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
暴力转向自身
弗洛伊德在1917年所写的其一篇名为《哀悼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的文章,讨论了哀悼和忧郁的差异,为我们理解现代抑郁症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弗氏指出:哀悼是通过对丧失对象一系列行为或仪式而完成的接受过程,即对于失去的或死去的人(可能只是象征性的),我们通过哀悼这一形式来纪念和追忆,由此使得失去的对象不再困扰我们;而忧郁,则是这一过程的失败,即未能通过合适的哀悼过程摆脱困扰,结果导致我们无法接受对象的失去,或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最终,这一原本投向他者的怨愤转入自身,导致自我的丧失。
“在哀悼中,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虚;在忧郁症中,变得贫困和空虚的则是自我本身”。
弗洛伊德关于忧郁在个体与外部互动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抑郁症的重要角度。当下,城市生活中的许多年轻人,正渐渐成为抑郁症的高发群体,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化。
这种结构性变化是指什么呢?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其《暴力拓扑学》中,给出了这样的论断:现代社会已经从规训社会变成了绩效社会。在规训社会中,外部他者是影响和塑造我们的主要力量,与其的斗争塑造了现代政治与精神的基本结构;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以及消费娱乐的兴盛,边界和差异性被抹平,来自外部他者的规训和挑战随之消失,我们开始面对自我。
在韩炳哲看来,这两种社会中的暴力形式已经有所变化:规训社会存在着排斥性暴力,即建立在我与他者的差异性之上;而在绩效社会,排斥性暴力渐渐隐匿,取而代之的是扩张性的暴力——迁徙过度频繁、消费过度、交流过度、信息过剩和生产过剩——一种强势的同化力量。在没有他者规训的世界里,暴力变得内在化和心理化,只能指向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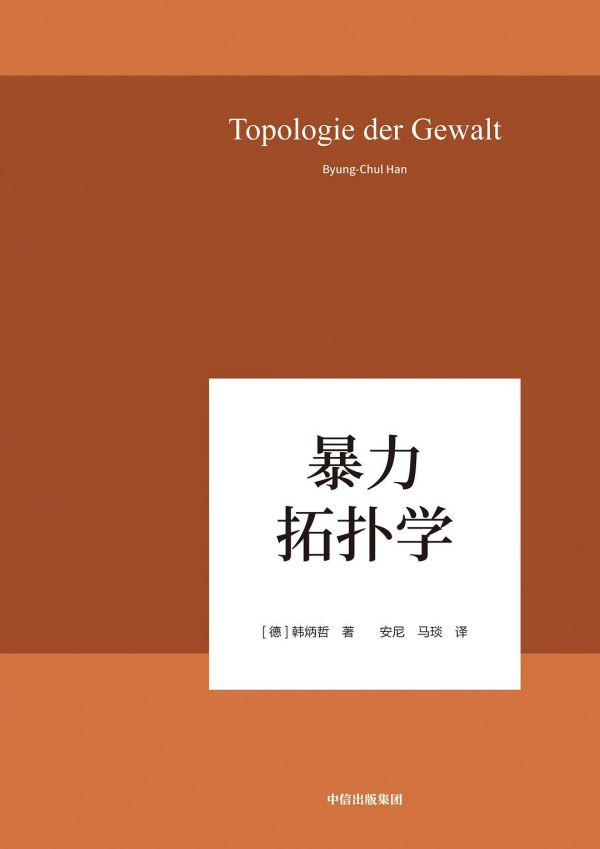
完美自我
显然,韩炳哲对绩效社会中个体心理结构的讨论,受到弗洛伊德关于忧郁症的影响。在韩炳哲看来,现代绩效社会所导致的典型症状便是抑郁症。在现代社会的“自由”中,个体被追求“完美自我”的绩效催促着,压迫不是来自外部、来自他人的命令,而是更多来自于自身的追求,从而导致自身筋疲力尽。
这不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主流样式吗?所谓的“996”和“内卷”,关于工作、关于教育、关于住房……甚至感情的焦虑,处处展现出我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加码绩效,无休止地奔波。
《我在他乡挺好的》勾勒的绩效社会中,几个女主人公为了能够留在北京、且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拼了命地努力——这当然无可厚非——恰恰在这里韩炳哲提醒我们,这一“自由选择”所隐藏的危机:追求这些目标所带来的压力,不像规训社会中来自他人的要求,而是我们的心甘情愿。在绩效的扩张性暴力中,我们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在这自我剥削中,个体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奴隶。正是这种强烈自我剥削和暴力压迫,常常导致抑郁。
弗洛伊德观察到,抑郁患者往往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且大都会出现强烈的自卑倾向。对于自我不完美的焦虑和痛苦,来源于绩效社会对“完美自我”的推崇和建构,当心灵从“对象丧失”转向“自我丧失”,抑郁症这只黑狗,会威胁每一个个体。
在2011年由堺雅人和宫崎葵主演的日剧《丈夫得了抑郁症》中,堺雅人扮演的男主角干夫,便在平静且规律的生活中患上了抑郁症。妻子对辞职在家休养的丈夫说:“如果痛苦,就不要努力了,保持平常心就好”。
实际上,干夫在工作上的努力,尽管能够带来每月的工资以供家庭和生活开销,但工作本身却给他带不来任何快乐和自我满足,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是压迫。
通过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看起来天经地义,当个体将其内化为信念和理想时,“暴力”的种子也就种下了,当我们十分努力却无法实现美好生活时,挫败和痛苦便会猛烈袭来。现代绩效社会中个体的心理模式,即自我压迫。
在《丈夫得了抑郁症》中,干夫失去的就是对于自我的接受,他觉的自己一旦不工作就没有价值。如果不是妻子以离婚相威胁,他依旧不愿意辞职在家养病。而在这“无所事事”的居家阶段,干夫渐渐获得了快乐和安慰,开始寻找到自我的意义。
这部剧是对当下绩效社会的强烈反叛,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构成个体和人生意义的,并不是各种“完美自我”,看似美好的目标中,包藏着对自己过分的要求和伤害。 “做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人不努力也是可以的”,这些看似消极的话,也是对抗绩效社会压迫的重要手段,对于正遭受抑郁症折磨的人来说,摆脱对“完美自我”和追求,或许是离开那只黑狗的第一步。

笑脸面具
《丈夫得了抑郁症》之所以感人或被称作治愈,也与故事中妻子对丈夫的耐心与呵护有关。抑郁症让干夫不想起床,只想一直睡觉,感觉一切都无意义和无趣,充满了强烈的自杀念头……这是一个非常灰色且阴郁的状态,如果不是妻子的坚持,干夫很难自己从其中走出来。
在为《抑郁症》所写的序言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提醒道:抑郁症患者需要正视自己的疾病,积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全程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不是把自己困在只有自己和黑狗的孤岛上”……可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诸多抑郁症患者的自白,他们自己往往很难坚持治疗,有人陪伴十分重要。
为什么看起来活泼开朗的人会患上抑郁症?或许我们该反思对“快乐”的过分推崇。在众多情绪谱系中,快乐往往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与之相反的一些情绪:如心情低落、忧郁与悲伤,常常被忽视其积极意义。某种程度上,相比于“快乐”,悲伤与忧郁提供了心灵状态更复杂的样貌。
绩效社会的人际关系情态,也潜移默化地加剧了一种现象,我们常常评价某个人“想太多”、“太脆弱”、“玻璃心”,使得他们被贴上标签和污名化,导致抑郁症患者或潜在患者,有了更深一步的恐惧,害怕被认为“意志力软弱”或“生活能力差”,从而使得抑郁被深深地隐藏起来。
绩效社会要求人们多呈现笑脸,对同事、对客户、对路人、也对朋友……这些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里被赋予了太多积极意义的“笑脸”,也让许多抑郁症患者戴上笑脸面具,深深隐藏心灵的重压,最终导致悲剧。胡晶晶虽然一直在微笑,我们却很难从这张面具脸上察觉到她的心灵。
所谓“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2012年,一位微博名叫“走饭”的南京女孩因抑郁症自杀后,她最后一条遗书微博下的评论区,便成了许多网友的树洞,人们在其下坦露自己遭遇的困难、痛苦和无奈,由此相濡以沫获得些许安慰。
抑郁症,像一面镜子般照射着绩效社会、照射着处于其中的每个人。当一切都变的相似且不断重复的时候,琐碎、肤浅、无聊和无趣成为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群时代”,个体该如何自处,如何消解“完美自我”的迷惘与缺失。
那只黑狗虎视眈眈,我们却往往视而不见,依旧无知无觉地耗尽自身。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