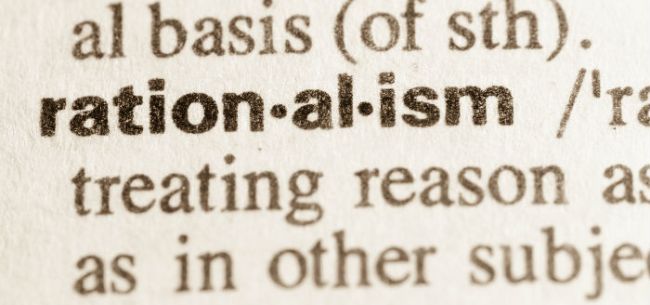
陶力行/文
齐格蒙特·鲍曼于1925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家庭,二战爆发之后,全家逃往苏联。1943年,鲍曼加入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后来升任上校,在军队任职期间,学习了社会学。1953年,鲍曼在反犹清洗中遭到迫害,被撤销了军职,于是转道学术,次年加入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从此走上社会学家之路。他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阶级和社会分层、英国劳工运动等问题,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1968年,鲍曼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不仅被迫离职,还被驱逐出波兰,但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就在英国利兹大学获得了教职,得以重启新的职业生涯。初到英国时,西欧思想界正处在反思近代理性主义的浪潮之中,“入乡随俗”的他改变了研究方向。19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几部有关理性主义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为一名经历过二战和冷战的思想家,鲍曼的主要学术经历都在反思现代理性主义及其产物。虽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但是他自198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作品都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号,即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一种现象的发生或问题的产生都牵涉到多重社会关系的组合,在理解这些现象和解决相关问题时,若采取现代理性主义者的机械论立场,那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如果说《现代性与大屠杀》是对“理性主义会导致巨大灾难”这一命题的例证,那《社会学之思》就是在告诉我们,除了机械论立场以外,思考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社会学的有机论立场。只要仔细阅读,就会发现《社会学之思》一直在和《现代性与大屠杀》对话。
现代理性主义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起步于1517年,以宗教改革运动为标志。1517年以前,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罗马教会所把持的基督教主义(Christian-ism)。在当时,《圣经》被教会确立为最高真理,所有知识(knowledge)的正确性都依赖于《圣经》的背书,因为罗马教会对于《圣经》的解释享有垄断权,所以他们也就垄断了人们的认知方式(epistemology)。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向罗马教会宣战。从组织管理上而言,当时的教会积弊已久,人们对此早就积怨很深,但由于担心教会的报复,所以一直敢怒不敢言。直到马丁·路德把教会的腐败问题摆上桌面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倒逼教会改革。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马丁·路德的阵营,既有普通百姓,也有各路精英贵族。“广泛的民意基础”削弱了罗马教会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在解释《圣经》这件事上,罗马教会不再享有垄断权。带来的结果是,不少新型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出现。
新型教派反对罗马教会,但他们并不希望人们抛弃基督教信仰,毕竟其意识形态底色依然是基督教主义。为了有一天能够团结信仰,新兴教派需要引入新的理论弹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笛卡尔(1596-1650)、斯宾诺莎(1632-1677)、牛顿(1643-1727)、莱布尼茨(1646-1716)就是那些输送理论弹药的人,他们生产了大量被后世历史学家归为科学范畴的知识。虽然他们生产的知识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普遍坚持两点:第一,这个世界的运行是确定的以及服从特定规律的。所谓规律,即能引发重复性现象的原因;第二,人们可以通过发明与引入分析工具而非借助《圣经》的表述来掌握这些规律。
因为分析工具的发明与引入依赖于人的推理能力,即理性,以及分析工具主要是指数学这样的形式语言,所以这些人被称为“形式理性主义者”。当代有不少思想史著作会从形态学角度将理性主义视为基督教主义的对立范畴,但这样的处理方式是错的,因为它忽视了历史的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牛顿、莱布尼茨等都是信教者,他们相信世界是一台精密有序的机械,如果不是上帝的创造,世界就不会这么有序,更别提用形式语言表述这种有序了。
18世纪之后,欧洲诸国之间加剧的竞争促进了生产设备的迭代,大量机械被发明出来。因为机械的发展依赖于各种形式理论的转化,这让不少思想家意识到,基于形式理性主义发展出来的知识不仅有解释性的功能,还有工具性的价值,于是他们在谈论理性时,更愿意从“产出”的角度展开,这点在英国人那里尤其明显。例如边沁(1748-1832)就认为,说A行动比B行动更理性,是因为A行动能比B行动产生更多的幸福/好处。以计算为基础、讲究知识效用的观念,就是“工具理性主义”。根据社会学家赵鼎新的解释,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是能够直接比出胜负的竞争方式,它们会导致工具理性主义的发展,因为胜负的确定依赖于计算和对比。
工具理性主义的发展让人意识到“能够创造事物的不仅有上帝,还有人本身”,但它只是稍稍撬动而非颠覆基督教主义的基本盘。对基督教主义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是价值理性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卢梭(1712-1778)、百科全书派、欧文(1771-1858)、圣西门(1760-1825)、夏尔·傅立叶(1772-1837)以及最著名的是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并不是因为人的能力不足,而在于传统宗教意识形态束缚……
价值理性主义者对人性以及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转折点,主张用新价值代替旧的基督教主义价值来改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从而实现一个“完美世界”……有意思的是,虽然价值理性主义是内生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但到了20世纪,它的主张却成为了大量后发国家寻求发展的实验性纲领,而在西方世界内部,它在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下遭遇了“污名化”。
反理性主义和鲍曼的反思
反理性主义其实一直伴随在理性主义的左右,从19世纪末的尼采、卡夫卡到20世纪初的海德格尔以及各种文学流派,都有反理性主义的影子。二战以前,反理性主义的趋势并不是太显现,但是二战之后,它吸纳了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精英,既有反殖民主义者和反国家主义者,还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形成了思潮。这些来自不同阵营的人非常灵活地将自己的经验与反理性主义话语相结合,分化出了三种形态的反理性主义,即反形式理性主义、反工具理性主义以及反价值理性主义。
虽然反理性主义的思潮起源于知识群体内部,但使得思潮得以形成的条件并非知识群体的自发意识,而是二战结束时所奠定的左倾化政治生态。二战结束之后,世界被划分成由美苏两国分别主导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两大集团都视对方为死敌,但鉴于两只领头羊都是核武器大国,所以各方都保持着行动上的克制,转入以意识形态之争为主的冷战模式……从国家层面看,两方保持着势均力敌的状态,直到冷战结束都如此,然而在社会的公共舆论层面,由于知识分子左倾化,西方世界一边倒地支持苏联集团。
以法国为例。二战刚结束时,法国知识界的意识形态光谱分布比较均匀,但战时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知识界主力是反纳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战争期间积累下了道德资本,在战后,利用话语权借“反纳粹思想余孽”之势把一些持民族主义态度的知识分子赶出了主流,导致左右失衡。这种左右失衡状态在冷战时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后都会加剧,比如1954年11月爆发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当时,法国政府无视战前承诺,派军队镇压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结果给主张反殖民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送了子弹”。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权力者,可以塑造公共舆论,当他们集体左倾时,社会也就左倾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那些理应保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界也不断走上“自我否定”之路,为了批判自己所处的阵营,他们从西方传统内部寻找精神的“劣根性”,将现代思想的出现——即现代理性主义——视为一切不良行为的原罪。鲍曼进入英国时,美国阵营正经历声势浩大的左派运动,反理性主义思潮如日中天,耳濡目染之下,他顺利地承接了反理性主义的话语,并将其应用在了大屠杀的分析之上。
在解释“为什么德国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屠杀这么多犹太人”,他提供的原因是:纳粹的大屠杀过程是一个高度流程化的操作,它将杀人事件分解成若干连续性步骤,当每一个步骤都变得非常容易操作时,整体的杀人效率就提高了。在解释“为什么反犹主义能够升级为大屠杀”,他的说法是:追求纯粹性的德国人相信,犹太人是一种畸形、不纯洁的化身,一种癌症,通过组织一个宏大的官僚机器、采取控制性的手段就可以将这种癌症根除掉。在解释“为什么德国人能够免于良心的谴责去执行大屠杀”时,他认为:在高度流程化的操作过程中,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个执行者都只是在完成局部性的任务,虽然总流程是杀人,但对于深嵌在组织链条中的一员而言,这却是一个盲点,以至于在参与杀人的时候免于责任感。
在鲍曼的笔下,大屠杀不是一个待解释的对象,而是一个用来注解现代社会的案例。虽然这个案例是一个经验性事件,但鲍曼只是在不遗余力地将执行大屠杀的官僚机构描绘成一个超大的机械体,丝毫没有通过比较的视野去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以至于得出了“大屠杀是一个现代社会内生性产物”这样一个既没办法证实也没办法证伪的结论。如果有读者愿意,完全可以找出某个古代社会屠村的例子,通过将纳粹大屠杀与之作类比,然后将纳粹大屠杀说成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返祖现象”。但这样的做法只是徒增了一个漂亮的隐喻而没有给读者增加任何信息含量,更别提知识含量了。
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到《社会学之思》
当一系列诸如大屠杀这样的恶性事件都被归为理性主义的后果时,理性主义式微,反理性主义崛起并成为了主导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在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在本体论层面,理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台精确的机械,其运作符合规律,而反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是高度不确定且复杂的有机体;在认识论层面,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因果关系,且这种因果关系必须通过一个稳定的形式系统来表征,而反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知识是默会的、碎片式的,要获得这些知识只能依赖于人的感受而非形式系统的构建。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学之思》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延续,前者是一部基于反理性主义立场的批判性作品,后者则是从反理性主义立场出发的建构性作品。
从《社会学之思》一书的内容上来看,鲍曼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将当代社会的各个面向都纳入了自己的考察范围,主题涵盖个人行为、物质交换、时空流动、技术嵌入、社会风险等多个领域。他在论述每一个主题时,都会从个体感受出发,然后回归至个体所在的社会网络,通过不断呈现出各种关系的交错与对抗,以提醒读者,看似独立与自由的个体总是受制于各种可见或不可见的条件,从来无法独善其身地行动。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的行动会被我们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都是在这些关系中构成的。行动、自我,以及社会认同和理解,都是密切关联的。”因此,即便是健身这样貌似纯粹以健康为目的的私人行动,在鲍曼看来,也无法回避满足他人期望、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表演的迎合式动机。鲍曼的核心论点是: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感受,而人的感受决定他的行为。
不过,在鲍曼的文本中,“决定”是一个很暧昧的语词,它并不被表征为一种清晰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社会关系类型多样,以及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同时背负多重社会关系,所以在鲍曼笔下,这些关系总是以混杂的方式“共同存在”,并以集体的方式“共同决定”每一个具体行动的发生。但这样的认识是错的,因为虽然任何一个行动者都同时背负多重社会关系,但不同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权重并不一样。在具体语境中,只有权重大的社会关系才会起主导性作用(dominant)……
鲍曼没有办法理清不同关系间的层级性以及特定语境下的权重分布,这是因为他采取的方法论是“解读”而非“解释”,即一种“重意义、轻因果”的知识构建方式。至于解释,则是对于因果关系的陈述构建这样一种知识的方式是归纳和比较:先明确观测范围,然后对被纳入观测范围的所有事件或行动进行考察和比较,接着明确其中的差异性,最后对这种差异性归因。因为基于差异性的比较依赖于量的考察,所以在解释特定事件时,在量上不显著(insignificant)的说法都可以被抛弃,留下的说法,则可以按照量的分布确定权重。
通过比较两种知识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出,解释性生产总是具较强的决定论色彩,而解读性知识总是语境依赖……
解读性知识的生产高度依赖于私人感受、联想和类比,所以解读性知识的生产总是千差万别……一千个读者纵然可以生产一千个莎士比亚,但不是每一个莎士比亚都重要,读者也没必要穷尽地去了解那一千个莎士比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一些不重要的莎士比亚给剔除出去。然而,无论是《现代性与大屠杀》,还是《社会学之思》,鲍曼生产的大部分知识都只是解读而非解释。
鲍曼之所以后来会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因为他走马观花式的思考让他把握不住社会的形态,看一切都不稳定,以至于肤浅地反对机械论。理性主义有缺陷,不代表反理性主义没有缺陷。虽然理性主义将社会假定为一台精确的机械是错的,但这不代表在我们的复杂社会中不存在广泛的非常固定的(fixed)机械式现象。社会学的目的纵然不是为了生产显白的命题,但是将如此固定的因果关系从复杂的社会表现中剥离出来却是社会学得以存在的理由。就这点而言,鲍曼并不是一个很有反思能力的学者,他对于反理性主义立场的全盘接受阻碍了他在智识上做出突破的可能。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