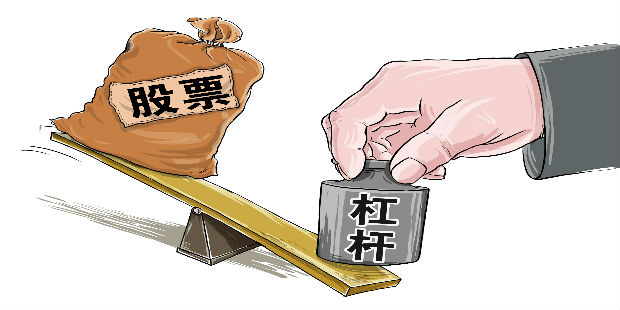
实习记者 宋建禹 万科股权之争从去年7月份持续至今已历时1年多,经历了大股东之争,资产重组的停牌期,到如今斗文斗法“逼宫”监管,犹如给市场上演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宫斗剧”。而“万宝之争”中出现的资管计划杠杆资金也让“观众”眼前一亮,原来收购还可以这么玩;当然有些“观众”对此也颇有微词。
首先说一下“杠杆收购”。杠杆收购指公司或个体利用收购目标的资产作为债务抵押,收购目标公司的策略。举个例子:A以准备以十元的价格向B购买一个苹果,A先投入两元买了该苹果的五分之一,然后用苹果的五分之一向银行或者路人C抵押借款继续购买该苹果,直到买完该苹果的一半以上拿到其控制权或者干脆买断。控制权到手以后A通对苹果合理的控制,持续产出利润或者部分出售来还本付息。当然也可以“咬”该苹果一口,让该苹果身价大增然后高价出售给路人甲。不过如果处理不好A的两元钱也可能血本无归。
事实上,杠杆收购在国外早有先例并且司空见惯,它最早大概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一、60年代:萌芽
这里要提到一个美国老派传统的金融投资家杰尔姆•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他在贝尔斯登(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全球500强之一,2008年破产)任职期间经常通过杠杆收购购买一些家族企业模式并且稳定盈利的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业主希望套现和继续经营,科尔伯格便以小企业为担保向债权人融资进行收购并以被收购企业的利润偿还债务。对债权人而言即使债务无法偿还也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盈利的小企业。科尔伯格第一次标准的杠杆收购是1965年收购了一家牙科产品制造厂,72岁的制造厂老板斯特恩由于子女对家族事业不感兴趣,希望把股权变现并且保持公司稳定运营,最终科尔伯格和一些小投资人以950万美元完成收购。他们投入自有资金150万美元,其余来自抵押借款。8个月后,这家被收购的公司公开募股,发行价为11.75美元,而公司原始股价只有2.5美元。4年之后,科尔伯格以8倍的价格出售手中所有的股权。这个阶段,杠杆收购以科尔伯格的理念为主,即以双赢为目的尽量保留小企业管理层,与小企业一同发展。而科尔伯格与其后辈克拉维斯(Henry Kravis)和罗伯茨(George Roberts)于1976年创建了KKR集团,该集团是全球最早、经验最为丰富、最成功的产业投资机构。
二、80年代:狂潮
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杠杆收购的利益回报过高使其迅猛发展并导致竞争加剧,直接拉高了这些小型企业的收购价格,而小型企业收购价格的提升使得债务仅靠利润无法偿还,因此,收购成功后通常利用将被收购企业重组、变卖资产等财务手段提升公司价值。1982年威利斯(Wesray)资本管理公司(下称“威利斯”)对吉本斯贺卡(Gibson)的收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威利斯于1981年成立,为前任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和他的合伙人——投资银行家雷蒙德·钱伯斯所属,其从事的第一宗交易就是杠杆收购RCA(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分支企业吉本斯贺卡公司。RCA于1919年由美国联邦政府创建,1985年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并购,1988年转至汤姆逊麾下,历史上曾生产电视机、显像管、录放影机、音响及通讯产品,因为受到70年代通胀影响,股票不景气,偿债成本加大,开始剥离收购的资产。这个时候由于大量资金从股票市场抽走,即使是收益不错的名牌企业也以从没有过的低价出售股票,资产的出售价格远低于其实际价值。1982年1月威利斯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买断吉本斯贺卡,西蒙和钱伯斯提供了33万美元的现金,以资本金形式提供的其他资产加起来也仅仅提供了100万美元。其余资产全部通过抵押贷款,以及回租形式的资产出售。这笔收购交易中,回租形式是在杠杆收购中首次使用。他们首先将吉本斯的固定资产和一家工厂以3100万美元出售,然后设法将这些资产进行了长达20年的回租。13个月后公司上市,资产评估近3亿美元,这可能是得益于1982年开始的牛市,实际上公司本身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而西蒙和钱伯斯持有资产估值为1.3亿美元,从1983年到1986年仅仅从一系列的资产销售中便赚取了7500万美元。4年中超过200倍的收益引发了80年代的并购狂潮。
80年代中期由于更多的竞争对手出现,甚至于1987年出现了“行业拥堵”现象。这也催生了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私募股权公司,它们通过筹集大量资金撬动一些大公司来获利。像黑石、KKR、凯雷等私募股权公司从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成立基金,并用基金中的资金购买上市或者非上市公司的股权,然后通过将被收购公司推出上市、二次收购、拆分出售资产等形式退出被收购公司并以此收回成本及获得利润。私募股权公司按照所管理的基金数额的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在盈利率超过一定标准时也能够分享投资收益)并将所获收益返还投资者,不过在这个阶段,收购方即私募股权公司并不注重公司经营。
比如1986年KKR收购贝亚特里斯(大型食品联合企业),经过长达4年资产的一连串销售,KKR最终将4亿美元的投入变成了20亿美元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拆分出售资产的典范案例。而1989年的“世纪大收购”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作为美国当时最大的食品与烟草公司,雷诺兹-纳贝斯克是美国老牌的食品公司纳贝斯克(奥利奥的主人)与当时烟草业两大巨头之一雷诺兹(RJR)与在1985年完成合并。1986年罗斯·约翰逊任职CEO。此人履历虽然可称传奇,但是在管理能力上颇有瑕疵。上任以后,罗斯·约翰逊无力解决两家公司合并后在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上遗留的很多问题,在1987年股市崩盘公司股价低迷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于1988年提出方案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对公司进行收购,而当时每股市值为53美元。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最终闻讯赶来的KKR以每股109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这次竞价收购的胜利。此次收购中KKR使用的现金不到20亿美元,而收购资金的规模超过250亿美元。整体交易的费用达320亿美元,KKR仅各项佣金就收取了约10亿美元。而其后公司新管理层引入的不当和高负债经营公司无力扩大规模等原因让雷诺兹-纳贝斯克元气大伤。1995年初KKR不得不剥离了公司的剩余股权,雷诺兹与纳贝斯克分道扬镳各自独立重回起点。这次收购不仅收益平平更让KKR赢得了如潮骂名。不得不说一向注重管理层作用的KKR在连企业资产情况都不明了的情况下贸然参与竞价收购,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投资的巨额收益使杠杆收购成为80年代获利性最高的投资理念,它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华尔街的公司、养老基金和财力雄厚的个人,1983年杠杆收购的交易额为45亿美元,而1988年是杠杆收购的发展巅峰时期,交易额已经达到了766亿美元。这次杠杆收购热潮的产生有诸多原因,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使企业的新购资产可以加速折旧,这就相当于使企业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一定程度上缓解杠杆收购后的债务压力;而美国的收入法使高负债经营可以合理避税,因为债务利息是在税前扣除的;通货膨胀也能给负债经营带来部分收益,因为债务利息率是固定的,并不随物价指数上涨而升高,从而通过举债可以获得通货膨胀带来的部分收益,进而转移债务负担;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利率市场化为“垃圾债”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等。而作为当时杠杆收购主力并提供了大约30%夹层资本的垃圾债,其违约率还不到4%。而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KKR的创始人之一、克拉维斯和罗伯茨的入行引领着科尔伯格于1987年离开了KKR。主要原因是与克拉维斯和罗伯茨两兄弟在公司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不得不说科尔伯格作为美国老派金融投资家,是有其坚持的。如同墨西哥老派黑帮分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与警察合作一样。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垃圾债”,因为垃圾债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杠杆收购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支持。当时杠杆收购的资本结构主要分三层,首先是有担保的优先债作为顶层资本(50%-70%),主要由银行提供;其次是没有担保的低评级债务作为夹层资本(20%-40%),主要由垃圾债提供;最后也是最核心的底层资本就是由收购方提供的资本金却只占了10%左右。那么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提供夹层资本的垃圾债。垃圾债即垃圾债券,是指主要由信用等级较低或盈利记录较差的公司发行的债券。由于信用等级差,发行利率高,此类债券具有风险较高同时收益也高的特征。在这里仅仅提一下杠杆收购中发行的垃圾债。杠杆收购中的垃圾债很多是无担保的,而即便是以目标公司为担保的,由于其极度的“劣后性”在公司破产清算时也很难被偿还。20世纪80年代垃圾债兴起,有着“垃圾债大王”之称的迈克尔·米尔肯功不可没。20世纪70年代米尔肯在德雷克斯投资公司成立了专门经营低等级债券的部门并四处游说他人购买,到了70年代末期,由于米尔肯的引领和市场需求,这种高回报的债券已经成为非常抢手的投资产品。1982年,德雷克斯投资公司开始通过“垃圾债券”形式发放较大比例的贷款来进行杠杆收购。1977年到1987年的10年间,米尔肯筹集到了930亿美元,德雷克斯公司在“垃圾债券”市场上的份额增长到了2000亿美元,让米尔肯成为了全美“垃圾债券大王”。巨额的垃圾债券像被吹胀的大气泡,终有破灭的一天。由于债券质量日趋下降,以及1987年股灾后潜在熊市的压力,全美发行垃圾债的违约率从1978—1988年间的2.2%激增到了1989年的4.3%,而到了1991年更是达到了11%。从1988年开始,发行公司无法偿付高额利息的情况屡有发生,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就不断有人状告米尔肯违法经营。法庭于1990年确认米尔肯有6项罪名,这些罪名都是没有先例的:掩盖股票头寸、帮助委托人逃税、隐藏会计记录,但均与内部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受贿无关。垃圾债券难以克服“高风险—>高利率—>高负担—>高拖欠—>更高风险……”的恶性循环圈,逐步走向衰退。而储蓄和贷款从高息市场指令性的撤出(《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执行法》)也给了高息市场沉重一击。垃圾债危机和米尔肯的入狱伴随着80年代的并购热潮走向终结。
三、90年代:注重“价值建立”
90年代中期,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杠杆收购也开始复苏。1994年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电信产业膨胀,杠杆收购资金大部流入电信产业。90年代中期另一个导致杠杆收购复苏的因素是史无前例的巨额资本由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和富有投资者流入收购基金。这个时期私募股权更注重被收购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价值建立”)和长期发展,因此收购杠杆率有所降低(自有资金一般达到30%),并且重视被收购公司管理层的作用。KKR收购安费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安费诺公司是世界著名的接插件制造商,产品主要用于通讯、有线电视、商业和军事航空电子。其最初是美国联合信号公司(AlliedSignal)的一个部门,于1987年分拆出来,以4.39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LawrenceJ.DeGeorge。DeGeorge在收购后一直担任公司主席,并于1991年将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DeGeorge家族合计拥有安费诺约30%的有投票权股份,为第一大股东。1996年DeGeorge打算退休并将股份变现。年末与一些潜在买家沟通并最终选中KKR。其后KKR筹措资金通过成立新的壳公司NXS收购公司以“杠杆资本重组”的方法完成对安费诺的收购。在1997年1月宣布并购计划前,安费诺公司各项收入、利润指标始终保持稳健增长,经营性现金流充裕。此次收购中KKR(KKR与其合伙人1996基金)投入股本资金3.41亿美元,杠杆资金9.9亿美元(抵押贷款7.5亿美元,垃圾债券2.4亿美元)于1997年收购安费诺,收购完成后持股约75%。收购后KKR对安费诺管理层主要通过认股权方式进行激励,与整合后的新安费诺管理层一起通过削减经营成本,改变经营战略以增加利润和现金流量。经营与管理的改善极大提高了公司市值。在公司度过债务支付难关后,随着股票价格上涨,KKR开始逐步出售股份,而公司管理层通过股票期权计划不断增加持股,并扩大员工持股范围。KKR的合伙附属企业于2004年售出所有股份。通过售出方式完全退出。随着KKR的完全退出,安费诺公司已经成为公众控股股东,公司实际处于管理层控制之下。
四、2003年之后:大型上市公司成为“猎物”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引发了并购低谷。到了2003年并购业触底反弹。此次杠杆收购热潮中,私募股权收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收购价格大幅增长,并且股息资本重组和二次收购成为主要的获利方式。经济复苏使巨额资金涌入杠杆收入业,优秀的大型收购公司不再满足于几亿或者十几亿美元的交易,上市公司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收购目标,比如2006年HCA。彼时,美林证券、贝恩资本以及KKR三方共投入股本资金约45亿美元,杠杆资金约185亿美元(128亿贷款57亿债券)于2006年收购HCA。收购完成后持股约99%。HCA公司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美国田纳西州,公司主要经营医院、康复理疗中心等美国各种不同的保健设施,截至2005年10月,公司已在英国、瑞士等23个国家拥有187家医院,94个独立的诊疗中心。2006年HCA公司业绩持续下滑,2006年第二财季净利比上年同期下降27%。公司在经营不振的情况下考虑第二次私有化。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在老龄化,医疗需求增加,加上公司现金流稳定,因而吸引了私募股权的兴趣。美林证券、贝恩资本以及KKR三方于2006年通过要约收购方式完成对HCA的收购,其中公司管理层和原公司创始人也参与了收购。收购后通过成本管控及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提升收入增长率。2007到2010年4年内收入增长38.25亿美元。2011年再次上市,估值约为2006年的两倍;同年,在《财富》世界500强中排313名。KKR等收购方至今仍未完全退出。这次交易算上HCA的自有债务,收购规模超过了330亿美元,刷新了1989年的雷诺兹-纳贝斯克收购规模的记录。这也是一次典型的友善收购,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仅仅以18%的对价溢价完成收购,不得不说管理层的参与和配合起到了巨大作用,与1989年的世纪大收购形成鲜明对比。
收购启示
纵观美国的杠杆收购史,也是一部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博弈史。收购方、管理层和股东三方博弈谋求均衡。而在博弈中三方均有着强烈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收购方和管理层。
首先收购方与股东,这是最直接的买卖双方利益冲突,冲突点是在价值判定上;其次收购方与管理层,公司完成收购时由于控制权变更,通常会进行管理层重组。双方的冲突点一目了然,就是权(控制权)利(薪水);最后是管理层和股东,理论上来讲管理层的义务之一就是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事实上在收购中股东受益是必然的,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最确定的事情就是死亡、税收和股东受益(公司被并购时),因此股东有足够的动机支持收购完成,但是管理层在收购中有可能权益受损,因此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利益冲突的。而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最了解其价值的往往是负责管理公司的管理层,这也可以解释CEO为什么是股东权益代言人,在收购中,管理层承担着股东和自身的双重利益,必然与收购方有着剧烈的矛盾冲突。
在公司并购中,管理层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在杠杆收购中更是被放大了。在与管理层有充分沟通的友善收购中,通过谈判达成共识以化解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层对股东的说服也对收购有着促进作用。而在恶意收购(未经董事会允许进行的收购行为)中,双方的利益冲突就极为剧烈。这也催生了许多防御手段的产生,比如“毒丸计划”、“白骑士”等等。“毒丸计划”是美国著名的并购律师马丁·利普顿1982年发明的,正式名称为“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当一个公司一旦遇到恶意收购,尤其是当收购方占有的股份已经达到10%到20%的时候,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控股权,就会大量低价增发新股。目的就是让收购方手中的股票占比下降,也就是摊薄股权,同时也增大了收购成本,目的就是让收购方无法达到控股的目标。它有着部分自残性质在内。而“白骑士”就是公司在被恶意收购时引入善意的第三方参与竞买,抬高收购成本。而在杠杆收购中,收购方一旦被认定为恶意收购,这些防御手段很容易达到启用条件,效果也更强。防御手段启用条件简单来说就是三条:一、管理层经过善意调查认定恶意收购对有效经营产生威胁。二、采用的防御手段与威胁相适。三、管理层的目的不是为了保住在目标公司中的位置。第三个就比较有喜感了,一个道德感十足的条例。杠杆收购中目标公司未来可预见的高负债经营让第一条很容易成立,二三条基本毫无难度。而收购方由于举债收购所负担的债务成本也让这些防御手段效果更强。因此在杠杆收购中,作用被放大了的管理层不容忽视。
而美国80年代恶意收购案件频发,直接引发了《公司法》的变革。1989年,为了抗御“恶意收购”,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它包括四条新条款:
l 第一,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这一条款就是为专门对付杠杆收购的,也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一股一票”的原则。
l 第二,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计划宣告后18个月之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收购者所获的利润。
l 第三,成功了的收购者必须保证26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
l 第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利,而不像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 即便其后争议如潮,宾州的新公司法仍显示出生命力,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采用了类似宾州的新公司法。仅从杠杆收购中来看,该法案第一条严重阻碍了恶意收购方计划和方案的实施。第二条让恶意收购者的收购对股东吸引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也就间接抬升了收购成本。第三条更是加重了收购方的偿债难度。而第四条的核心思想是:将股东视为公司的“所有者”是一个错误,公司管理层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者”直接扩大了管理层的权责范围,而对处于对立面的恶意收购者而言,收购难度无疑加大了许多。有意思的是该法案第一条早在1960年德国《关于大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为私有法》的联邦法律中就已出现,可见法律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被拿来借鉴。
因此在杠杆收购过程中很注重首先与管理层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友善收购。确立双方都认可的价格和融资方案,同时对收购以后的企业管理和资产重组也做出安排,尽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当然也避免了管理层执行“毒丸计划”等防卫手段。“黑石”(著名的PE投资机构)一贯坚持“友善收购”以及KKR坚定采用“管理层收购”的原则是数十年经验沉积下来的,当然KKR因为目标管理层出资参与收购就标榜自己是“管理层收购”也不能说它的不是。“雷诺兹-纳贝斯克”收购案中去除机会成本和名誉影响,很难说它赚到了什么,此案中超过100%的对价溢价和HCA收购案中18%的对价溢价形成鲜明对比,管理层的作用在此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收购方、股东与管理层三方博弈的情况下。最优选择只能是三方受益的合作性均衡。因与管理层没有协商而导致的强烈对抗最终会使结果得不偿失。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