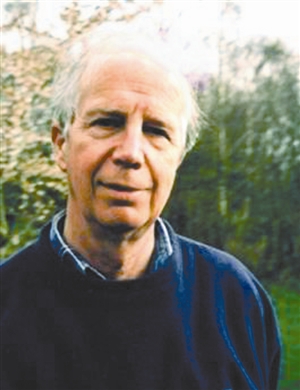
张耐冬/文
对麦克法兰教授的采访结束之后,负责翻译的April从书包里取出几本他的著作请他签名。她解释说,自己在2006年读到《给莉莉的信》,当时并未注意作者是谁,后来为准备论文,读了他关于茶叶贸易与生产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才发现自己在16岁时就已是他的读者。借着这次机会,她想让作者给自己的这段阅读经历做一个见证。
April的麦克法兰阅读史,也正是麦教授的著作进入中国的历程。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之外,作品的中译本又先后分由几家出版社推出,让他在大众阅读领域不似中国研究者如史景迁般知名。不过,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他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从细微之处入手去解析宏观问题的方法绝对值得称道。他能够从玻璃和茶叶这些看似日常的物件着眼,去探究它们在现代化历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进而对现代化进程提出自己的解释,正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的功力。更为难得的是,他能把学术著作写得令读者轻松,没有大段的拗口词汇,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新潮理论,甚至没有大多数学术作品看似严肃的枯燥文风,阅读体验极佳。
尽管如此,于我而言,准备和他的访谈并不轻松。这次的采访主题是关于他的新作《现代世界的诞生》(TheInventionoftheModernWorld),这本书是他对此前研究的一个总结,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历史会走到现代社会?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麦教授反对一切历史决定论,并不认为“现代”必将降临,这一立场是我所认同的;他强调现代化的过程是一条偶然出现的道路,如果离开这一偶然情况发生时各种错综复杂的条件,就根本不会出现“现代化”,这一说法我也同意。而他过于强调英国在各方面能够催生现代化并符合现代化精神的论断,我却并不赞同。这一论断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他认可“英国是第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这一常识,又强调英国得以走向现代的原因在于其内在特性,大大削弱了“现代”的普适性,间接瓦解了“英国率先实现现代化”这一常识,使其论证逻辑不能首尾相衔。
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思路何以形成?特别是对麦教授这样一位多年思考现代化进程的学者而言,有点难以想象。如果将原因简单化,我觉得可能是他内心对本国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很多网络与平面媒体的者都对他过分强调英国(他自己专门强调用“英格兰”一词更为合适)因素的倾向进行激烈的批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他的缺陷,而是所有研究本国史或与本国有关论题者共有的矛盾,或者说困境。一方面,我们无法割裂自己与传统的联系,也无法真正挣脱国家认同语境下的种种神话,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学术的立场上理性地发论,从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开始,我们就陷入无法自拔的矛盾,思考愈深,困境愈明显。20世纪那一批最伟大的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身上,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又何必对麦教授过分苛责呢?
我们所熟知的学者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晚年讲学时甚至讲到西方优秀的文化与制度,就要在本国传统中寻出与其匹敌者,儒者情怀展露无遗,以致有论者含蓄地批评他这种比较“是一场完全没有悬念的比赛”。与他相比,麦教授已经显得理性多了。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麦教授考察英格兰因素与现代国家所具有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时,都尽可能地在学术范围内寻找理论依据,因此他的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与钱穆那种做中西比较时一招制胜的做法相比,论证方式已经严谨得多了,其研究态度比较接近陈寅恪所提出的“了解之同情”。
正因如此,在访谈时应该如何向麦教授发问就成了一个问题。做准备功课时,余婉卉女士对麦教授讲座的侧记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她在《麦氏讲座的诞生》中,将麦教授的“认真”充分展现出来。无论是出行惯例、著作中文版的译者选择,还是对课堂的要求、时间的把握、录像效果的追求,甚至讲稿摆放的位置,麦教授都有一种近乎执着的认真,这是我经验中典型的英国绅士性格,谦和有礼又一丝不苟,原则越强,外在表现就越温和。方麟先生认为麦教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学术上都有种牛仔风格,在我看来,也许牛仔的外在之下,仍是矜持的绅士——当然,麦教授可能会按照他书中的观点告诉我们,牛仔的探险精神与中古欧洲的骑士精神和英格兰的绅士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猜想在采访中得到了印证。在April把我的问题翻译成英文时,他都严肃地听着,偶有沉思,开始回答时,他的脸上大多时间带着温和的微笑,所做的回答条理清晰,对自己的观点也如我意料中那般坚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英格兰历史与传统的热爱,但在表达这种情感时并不张狂,和时下某些大张儒学的国人截然不同。当我们的问题对他在书中的某些说法提出质疑时,他耐心地做出解释,并表示我们指出的问题和他的思考并不矛盾,而当我们提到他特别看重的观念和前贤的观点时则会心一笑。当问到他为何在书中多次使用“旧制度”一词时,他表现出对托克维尔的赞佩,明确回答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直接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而并无个人的修正。整场的气氛非常轻松,April和他的英文对话也非常连贯,若闭上双眼,甚至会觉得他们是在剑桥大学的课堂上交流。
能够如此谦和地把自己所坚持的观点表达出来,在面对不赞同的声音时也并不急躁,并不仅仅是所谓绅士风度就能概括的。十几年前读到马彪先生的《狷介书生谷川道雄》,对谷川氏的文章中敢于发出与前辈截然不同声音的勇气颇为心仪,后来聆听他的现场报告,感受到的只有他对学术、学者和听众的谦恭,毫无狷介之气。麦教授也是如此,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他继续了年轻时勇于挑战权威理论的风格,对几种在现代性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的研究范式进行质疑,但在人前谈起自己的观点时并无以此自矜之意。
谷川氏和麦氏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少数派,他们的观点都受到很多批评,基本结论都和某些前辈学者的假说有明显的承继关系,研究的出发点也都和其领域内最时新的潮流相异,又都能在自己处于“非主流”的境遇下坚持己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共性,应该就是学者的自信,也就是《论语》中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麦教授认为,英格兰的现代性与其历史密不可分,从11或12世纪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形成的传统在走向现代之后并无本质变化,不存在一个从中世纪向现代的飞越。这种对英格兰传统的强调,并不是来自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是他在研究欧洲的同时,对东亚世界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审视。从“他者”的身上,麦教授看到了本国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又以此反观其他文化,在比较中寻找英格兰特质的历史位置。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在体认不同文明的基础上,寻求现代性中所具有的本国文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对这些文化的他者也有充分的感受和考察,颇为严谨。不过,对于本国文明的审视,是建立在英国已经充分现代化基础上的,作为历史存在的文明特性,如何保证他的考察是可信的,正是评论者质疑的焦点。麦氏选择的一些论据在可信性上确实存在问题,而且有将英格兰存在的某些现象归结为英格兰特质之嫌。
从进程而言,英格兰的现代化本身存在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具备复杂性,麦教授所概括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几个方面的现代性并非一日完成,在现代化过程中,它们各自的特征也非始终不变。对这种复杂的过程性,麦教授没有做过多的论述,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所提出的只是现代性的理想模型。所以,我本打算就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提问,切入点是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的推理小说,想听听麦教授对这两位小说家笔下的各类案件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各自所反映的现代化情况做出解析。在April的建议下,我舍弃了这个问题,而对现代化复杂的过程性的思考,仍应是我们对麦教授作品细思的一个方向。
很多评论者认为,以探讨英国现代化为主的这部著作,题名《现代世界的诞生》名不副实,应该改名“现代英国的诞生”。如果按照我们近年来博士论文的拟题方式,可能“现代世界的诞生——以英国为例”是最容易被采纳的,但在麦教授看来,现代性最初的呈现就是英国的现代化,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现代”降临人世的事情。如果要对书名深究的话,“诞生”也许并非最好,从麦教授的原文来看,“Invention”并非必然应有之物,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他的论述,就是在探讨现代的成立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或者“现代世界的成立”更能体现他所强调的特质内容。
